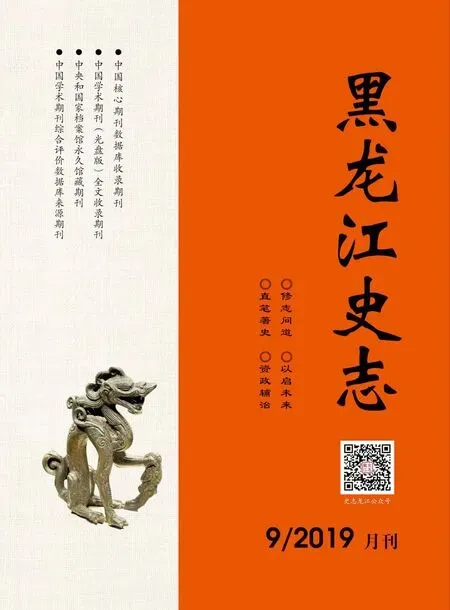論修志責任和人才思想發展
韓章訓
修志責任屬于修志者的意識問題,修志人才屬于修志者素質問題。此兩問題既是修志中的兩個具體問題,也都是事關修志大局的兩個重要問題。對于某一官修志書來說,若編修責任得不到落實,那該志編修便無從談起。若未能選用合格人才,那該志就不可成為一部合格志書。自上一輪修志開展以來,雖然已有一些書文論及修志責任和人才問題,為促進對此兩問題的研究,這里擬從歷時角度作一梳理和評述。
一、修志責任思想發展
在隋前,由于修志多屬個人行為,修志全憑個人興趣所驅動,故不存在具有社會性質的修志責任問題。自隋始,我國修志同修史一樣,皆被納入行政軌道,于是便出現了具有社會性質的集體或個人的修志責任問題。“修志責任”作為一種思想意識,就是指修志者把修志視為自己應作的一件分內事。對于官修志書來說,官員的修志責任意識是官修志書得以產生的動力源所在。倘若修志者對修志意義毫無認識,那么其修志責任思想便不可能產生。就某一具體地方而言,其修志者的責任意識能否產生和產生遲早,完全取決于該地方人士尤其是該地行政長官對修志意義的認識程度。
(一)宋元修志責任思想
在宋前,未見有人對修志責任問題進行理性探索。自宋始,隨著修志的不斷發展和修志理論研究的不斷進步,才有人對修志責任問題進行研究。南宋梁克家率先把修志視為守土者之責。他述《三山志》編纂緣由曰:“夫追惟往昔之事,不可復記,世常以為恨至。耳目所接,謂未遽泯沒,則又不急于紀錄。歲月因循,忽莫省憶,使來者復恨之,斯亦守土者之責也。”[1]梁氏此說對后世影響深遠。南宋胡太初首先談及志書主修者的責任。他總結自己主修《臨汀志》經驗曰:“太初為定科條,訂事實,劑雅俗,正訛謬,而編成矣。”[2]由此可見,在胡氏看來,“定科條,訂事實,劑雅俗,正訛謬”,這就是志書主修者所應承擔的責任。
元人承宋人余緒,繼續探究修志責任問題。有的繼承宋人觀點,認為修志是守土者之責。如贍思曰:“易代制度之變當紀矣,而國朝因革之宜未書,紀錄不備,為郡之典良有闕焉。斯責固守土者之所任”。[3]有的還把不及時修志視為地方長官的一種罪過。如馮福京說:“至宋,獨圖籍文書一事鑿空駕偽,顧不如秦之猶為務實。而且貽禍于來世蒼生也。昌國中海而處,由縣升州,而州志不作。此固仆廝吏不知稽古之務,而為上者亦有罪焉。”[4]馮氏作為封建時代的一個地方官吏,能持這種修志責任觀念是很難能可貴的。在元代,有些地方官很重視修志,有的甚至把修志視為居官首務。如馮福京論修志與做官關系曰:“夫輿地之間,所司之務,土壤之物,宜與夫革命以來所損所益之大政令,皆當刊入志書,以備天子史官之采錄,乃臣子職分之當然。而或者以為非期會簿書之所急,則不敬莫大乎是。余嘗佐州昌國,即以是為第一事,亦既編摩鋟梓,以補是邦之闕文矣。”[5]
(二)明代修志責任思想
至明代,隨著修志的迅速普及和撰寫志書序跋人的驟然增多,學界對修志責任問題的研究有明顯深化,且提出一系列新見。其主要見解有四:其一,有的認為修志為地方政府之責。如張嘉謨論隰州志編修曰:“國無史則不可以為國,郡無乘又奚以為郡。隰乘之無,隰之闕典也,實有司責哉。”[6]這里所言“有司”即指地方政府。比較而言,“有司”說比“守土者”說更為科學。“守土者”說是強調地方官的個人作用,“有司”說是強調地方政府的集體作用。地方長官會不斷更換,這樣就往往會導致修志責任的不落實。地方政府總是存在的,這就可避免因首官更易而影響修志責任的落實。其二,有的認為,地方官當以宋程顥、朱熹為榜樣,把修志視為“居官第一義”。如梅思說:“粵昔明道尹上元,嘗修縣乘,曰此居官第一義也。晦翁軍南康,下車之初,即加修集,彼大儒也。豈區區文字者,昭政紀言,垂憲示戒,志實急焉。”[7]梅氏此說雖對促進地方修志有一定積極意義,但此說本身有偏頗之嫌。因為對于“居官者”來說,他們應該永遠把國計民生視為“居官第一義”。其三,有的認為,修一統志為天子之責,修地方志為地方官之責。如寧良說:“一統之志,天子之事也。郡邑之志,守令之事也。”[8]其四,有的繼承和發展前人思想,認為續修志書為后人之責。如李維楨述《新安文獻續志》編修緣由曰:新安繼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后,“相望缺而不載,責在后人,乃謀于同志,旁求大家故族,鴻生巨儒續葺之。”[9]其五,有的繼承和發展前人思想,認為修志首先是地方官的責任,其次也是鄉賢的責任。如馮孜曾對鄉賢寧堅說:“天下之志久成,而吾鄉之志缺焉不修,固我守土者之責,抑亦鄉賢之責也。愿與吾子修之。”[10]
(三)清代修志責任思想
清代是修志責任研究的持續深化時期。彼時許多學者在繼承和發展前人思想基礎上,又提出許多新見。其主要新見解有四:其一,有的認為,修志是地方官民的共同責任。如黃宅中述《大定府志》編纂體會曰:本志“第成書太遲,捐俸無多,心雖勤而力有限,采訪不無遺漏,校讎仍有錯訛。簿領匆匆,草創為此。所望后之君子,因而討論之,修飾之,更加潤色,完善克臻,則官斯土與居斯土者均有責焉。”[11]其二,有的認為,在修志上,地方政府當負行政責任,地方士紳當負筆事責任。如丁振鐸說:“一國文獻具于史,一郡一邑文獻具于志。文獻者,彼都人士之專責也。然非官紳共任之,則其書不能成。”[12]其三,有的認為,修志責任心是落實修志責任的關鍵所在。如李紱曰:“吾觀天下郡國之志,或迫于功令,勉強而為之。若州與縣則往往有開辟數千百年而未嘗有成書者,雖通都大邑猶然,其小者則闕略尤甚。豈皆一無足志耶?毋乃司是土者,有其才而無其志,有其志而無其才,故玩廢至于此歟!”[13]這里所謂修志之“志”即指修志者的責任心。其四,有的認為,邑志長期不修是一邑人士之恥。如李兆洛說:“志書為一縣文獻所寄,猶家之有譜牒也。為子孫而不知先代譜牒世系,無不羞之。為邑中人士之望,而于一邑文獻不能數述,獨非恥乎?”[14]在清代,也有一些地方官總是把修志責任推諉給后人。如寧夏知府張金城曾評說曰:“夫后人惜前人之不為,而復望后人,曰‘有待在官之事輾。’轉因仍,以至廢墮而不可復理,大率以此。金城既守此土,既任此責,是以不揣鄙陋,偕我同志,勒成此書,亦聊以供蒞事者之考稽,備太史軒之采擇。后之覽者誠鑒其不敢 謝之由,而寬其不學自擅之咎,則厚幸矣!”[15]張氏這種敢于批評時弊的勇氣和勇于承擔修志責任的精神是值得點贊的。
(四)民國修志責任思想
民國時期,各級政府對于修志問題既有重視的一面,也有不夠重視的另一面。其總體情形恰如李泰 所云:“五稔以還,國府通令各省,省府通令各縣,催促續志,急如星火。既為公令,勢必奉行,故省無間南北,縣不分大小,莫不各續志書,待梓報命。然省縣數千,未聞有某志之作,可以表現當時史潮者,甚至求如清代章學誠、戴震、洪亮吉、楊篤諸家之作,亦復不可多得。間嘗推原厥故,遺誤多由疆圻。蓋清代康、乾諸帝既已稽古右文,各省督撫科道亦多出身翰苑,故所延聘類皆通儒,所成方志義例謹嚴。資料淹博者各地多有,即其下者亦復文通句雅,蔚然成章。若在今日,省吏多非士林。上焉者以志館屬之僚紳,下焉者并設此以置親故。故立館而終無成者有之,成書而言無物者亦有之。以較清代,反多遠遜”。[16]民國學界對修志責任問題仍在繼續研究,且有不少新見。其主要新見解有三:其一,有的認為,修志為地方責任。如陸炳麟說:“修譜者,子孫之責也。譜久不修,木本水源茫無稽考,咎莫大焉。修志者,地方之事也。志久失修,疆域、戶口、田賦、學校諸要政,代遠年湮,見聞舛誤,恥莫大焉。”[17]其二,有的認為,修志是“為政者之責”。如吳鼎昌述《貴州通志》編修緣起曰:“民國二十六年,余奉命主黔,慮此邦文獻之年久失墜,即有意于修志之舉。時值抗戰軍興,百端紛集,迄無寧日。以言省志,難于即時措手,然方志與治道相表里,雖在艱危,使其裒然成帙,以收綱舉目張、明體達用之效,是亦為政者之責。”[18]其三,廣西省政府率先把編修縣志列為縣政工作之一。民國23年,廣西省政府頒發各縣施政準則,率先把編修縣志列為縣政工作之一。時人陳壽民追憶此事曰:“民國二十三年度,省頒各縣施政準則,將修志一項列為縣政工作之一。”[19]后國民政府頒布的《地方志書纂修辦法》也對地方政府提出要求:“各省市縣纂修事宜,應由各省市縣政府督促省市縣之文獻委員會負責辦理。”
(五)當代修志責任思想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從上一屆修志工作開展以來,各級政府都把修志視為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江澤民同志指出:“我們不能讓編纂方志的歷史中斷。為給后世保留這一精神財富,同時編纂好新方志,也是我們這一代的歷史責任。”[20]李鐵映同志認為修志是“政府主要領導同志的職責”。他指出:“修志工作絕不是可有可無的事,而是各級政府的職責,主要是省、市、縣三級政府主要領導同志的職責……對各級政府領導來說,修志可以說是‘官職’‘官責’。”[21]2014年 4月 19日,劉延東同志指出:“要繼續深入貫徹落實《地方志工作條例》,進一步明確地方各級政府管理和發展地方志事業的重要職責,切實做到認識到位、領導到位、機構到位、編制到位、經費到位、設施到位、規劃到位、工作到位,將地方志工作納入各地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之中。”[22]最近,謝伏瞻同志還向全國地方志機構主任提出守土“有責”、“負責”、“盡責”的新要求。他說:“新時代的地方志踏了新征程。讓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高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偉大旗幟,以對黨忠誠、為黨分憂、為黨盡職、為民造福的政治擔當,以時不我待、只爭朝夕、勇立潮頭的歷史擔當,以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的責任擔當,不斷改革創新、攻堅克難,銳意進取,努力做出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無愧于歷史的業績,全力推進地方志事業轉型升級,奮力開創新時代地方志事業高質量發展的新局面。”[23]
二、修志人才思想發展
欲做好修志工作,關鍵在于得人。唐劉知幾率先論及史志人才素養問題。他說:“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并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24]劉氏這段話含有三層意思:一是指明作為一個合格的史志人才,必須兼具“才、學、識”三長。二是強調兼具“才、學、識”三長。其三,必須具有“好是正直”和“善惡并書”的品德。劉氏此說對后世修志人才思想發展影響巨大而深遠。
(一)宋元修志人才思想
自宋始,許多學者都論及修志人才問題。南宋鄭樵認為,修志者須有豐富歷史知識。他說:“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于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為也。”[25]這里所言“老于典故”,即指豐富歷史知識。有的認為,充任主纂者,必須是大手筆。如方逢辰自謂曰:志書“纂修宜擇大手筆,淺陋非敢當也。”[26]有的認為,充任主纂必須有博物洽聞的素質。如趙不悔曰:“羅君以儒學早馳雋聲,惟其博物洽聞,故論載甚廣,而其敘事又自得立言之法,讀者必能辨之。”此中“羅君”即指《新安志》主纂羅愿。有的認為,修志必須選用合格人才,否則就會記載失當,無信今傳后可言。如傅兆敬曰:“今州縣之編,雖與并載寰宇者不類,條目纖悉,亦豈易為?茍非其人,則詳略勿當,是非雜糅,何以信后?”[27]
元代重視修志人才主要體現于兩方面:一方面是重視對主纂者的選擇。有的認為,主纂者當由博物洽聞、做事不茍者來充任。如索元岱譽《金陵新志》主纂張鉉曰:“予聞張君博物洽聞,而做事不茍。”[28]有的認為,主纂者當由學問老成、詞章典雅的大手筆來充任。如《金陵新志·修志文移》曰:“所有續纂新志,非仗大手筆未易成就。近聞陜西儒官張用鼎名鉉,學問老成,詞章典雅,必得其人,事能就緒。”[29]另一方面是重視對一般修志人員的選擇。有的認為,作為一個合格的修志者,必須具有“才、學、識”三長。如馮福京曰:“作史者必擅三者之長,曰學、曰識、曰才,而后能傳信于天下。蓋非學無以通古今之世變,非識無以明事理之精微,非才無以措褒貶之筆削。三者闕一,不敢登此職焉。”[30]揭 斯對修志人才問題最有見地。他認為,選用史志人才“當以心術為本”。他說:“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31]這里所言“心術”意同后世所言思想道德。
(二)明代修志人才思想
明代學界對于修志人才的研究,既有繼承前人思想的一面,更有創新和發展的另一面。綜其見解主要有四。其一,有的認為,修志者須做到修心與修志相統一。如鄭紹 說:“太上修心,其次修志。心敝而后志敝,心修而后志修。”[32]鄭氏此說對于發展修志人才素養觀念有創新意義。其二,有的還提出關于修志人才的職業道德標準。如王崇慶認為,作為一個合格修志者必須具有“明、公、勇”三品質。他說:“何以辨物?曰明。何以取舍?曰公。何以獨斷?曰勇。故物辨而后是非昭焉,取舍定而后君子小人別焉,勇斷而后讒者莫之間,力者莫之奪焉。是良史所以跨百代而先王之所必與也。”[33]后王道純加以發展,認為修志者應該具備“正、虛、公”三品質。他說:“嘗聞作史有三長,曰才、學、識。修志亦有三長,曰正、虛、公。何謂正?表端始可取影,繩直始可裁木,居恒有泰山北斗之望。甫受事,咸心傾焉,不待其帙之成也,然后可以惟吾揚抑而入不疑。何謂虛?裘必成于眾腋,冶必集于碎金,匹夫匹婦之口有確案焉。谷虛則響應,器虛則受多,自廣狹人先正戒之矣。何謂公?平衡不 軒輊,止水不作妍媸。惟物有分,惟人有質。墜淵加膝,使人眩于名實。罔知所守,則孰是間斥之不言怨,榮祿之不言德者,無忝厥任。有此三長,而又有才、學、識濟之,舉山川名物、星野 祥、建置因革、風俗移易,指掌了然。”[34]王氏此說對后世有較大影響。其三,有的認為,修志者必須有任勞任怨的工作作風。如劉元瀚曰:“古有良史才,未必有良史品。品與才俱良而不能身任怨勞,內私其好憎,外怵于威富,將傳穢傳冤,為禍等烈。”[35]其四,有的認為,作為一個合格修志者,不僅要學問豐富、史事熟悉,而且還得心術端正即要重視修志者的職業道德問題。
(三)清代修志人才思想
清代學界對修志人才思想研究有所深化。綜其見解主要有四。其一,有的認為,作為一個合格的修志人才,不僅要兼具才學識“三長”,而且還得有公正之心。如汪士璜曰:“古人論作史有三難,曰才,曰學,曰識。三者備,而后可以言史。予謂三者固難,而尤難者,一出之以至公之心。蓋史所以傳信也,一有顧忌而史偽矣,一有護惜而史偽矣,一有阿曲而史又偽矣。中懷顧忌護惜阿曲之私,則雖才學識之俱優,適所以長其浮夸,而反足為史累。”[36]其二,有的繼承和發展前人思想,認為修志者當有“識”“明”“公”三長。如章學誠說:修志當有 “ 識 ”“ 明 ”“ 公 ”“ 三 長 ”,“識足以斷凡例,明足以決去取,公足以絕請托。”[37]其三,往昔學界多注意修志人才的個體素質問題,而清代學者則開始注意修志班子的群體素質問題。阮元在編纂《廣東通志》時,首先論及修志人才班子的群體素質問題。他總結謝啟昆編纂《廣西通志》經驗說:“凡總纂、分纂、采訪、校錄,莫不肩任得人,富于學而肯勤其力。”[38]后王 也認為,欲編好一部志書,僅有一個合格總纂者是遠遠不夠的,還要“分修”“繕寫”“校讎”得人。他說:修志“亦自有道。第一,書籍宜足。第二,采訪宜詳。第三,分修得人。第四,繕寫得人。第五,讎校得人。……”[39]王氏此說頗具學術見地。其四,自古以來,學界在論及修志人才問題時,多著眼于以主纂者為代表的業務人才,而對于主持修志行政的主修者是否得人,幾乎無人論及。孫觀獨具慧眼,首先提出關于主修者素質問題。他說:“志例每六十年而一修,而主修者實難其人。役于簿書期會之煩,則不暇修。有意修志,不以事廢置矣,而又苦于文獻之不足征,政事之未及備舉。或甫議興修,又適以遷擢去。不恒久于其任,則時修時輟也。”[40]孫氏此言可謂植根于修志實踐的經驗之談。
(四)民國修志人才思想
民國時期,學界對于修志人才問題的研究有明顯進步,彼時學界主要見解有四。其一,有的認為,修志者必須兼具“德、才、學、識”四種良好素質。如梁啟超總結修志歷史經驗曰:“一志之成,殆等一史,非‘三長’兼備,未易慊然。然此尚非其至難,至難乃在纂修之得人,幾不可能。”[41]李 也說:“方志本為史乘之一。其記述之最要關鍵,據劉子元、章實齋之見解,謂為無論何人何志,非具左列之四長,自不能勝其所職。”又說:“德者何?即著述者之心術也。”“學者何?即著述者之心法也。”“識者何?即著述者之心靈也。”“才者何?即著述者之心技也。”[42]其二,有的認為,修志者須有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兩方面知識。如吳宗慈曰:“從作方志之人選言,其最低限度,非有三十年以上之舊學根柢即掌故學,不足以應付過去之事物。非有現代各種科學之充分常識,不足以融通現在之事物地質、生物、語言、氣候、統計、測繪等等,雖應屬之專家,然主編者非有此各種之常識不可。而為未來事物植其基,非有專門史學之研究與素養,不足以提綱挈領、擷要刪繁,以成專門不朽而切合時代之創作。”[43]其三,有的還論及志書主纂、主修的素質問題。如周順循認為,主纂者當“通才博識,品學兼長”,主修者當“聰明睿智”,待人“寬容”。他說:“古之長史莫若董狐,秉筆直書,大道是賴。故雖一縣志也,而主撰者固須得一通才博識、品學兼長之士任之。即長吏大府尤須聰明睿智,諒予寬容,以全其用。”[44]瞿宣穎認為,作為修志總裁須有“學識超卓、精力彌滿”之素質。他說:“眾手修書自古難之。古人官修之書所以能佳者,全在一學識超卓、精力彌滿之人一手鑒裁。”[45]其四,有的還論及修志人才的培訓問題。如吳宗慈說:在修志中“訓練人才當分兩種步驟。一暫時的,一永久的。”所謂“暫時”者就是通過各類培訓班授以“新知”。又說:“前文所述修志人選,一須有舊學根柢,二須有科學常識,三須有史學修養。如此全才,夫豈易得。然際此新舊學術遞嬗之時,舊者固未盡荒落,所缺乏者新知耳。新者方逐次延續,所不足者根柢耳。若合新舊而冶之,各用其偏,自臻其全矣。其訓練之法則討論可以立會,講習亦可成班。”所謂“永久”者就是指通過高等學校授以系統方志學知識。吳氏此說很有學術見地,迄今仍有借鑒意義。
(五)當代修志人才思想
自上一輪開展以來,學界對于志書主編素質問題多有討論。1981年,梁寒冰說:“專業修志人員應具備必要的條件:一是應具備高等學校畢業的文化程度。二是要懂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方法。三是要有一定的歷史和地理的專業知識。四是應有一般的自然科學基礎知識。五是要有一些方志學和編纂學的基本知識。如果說,一個人不可能具備全部條件,至少一個小集體是應該具備的。”[46]1985年,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頒發的《新編地方志工作暫行規定》指出:應“重視提高方志工作隊伍的素質。應在修志實踐中,采取多層次、多渠道、多種形式的短期培訓,逐步培養一支具有一定政治思想和理論水平,具有一定專業知識和寫作能力的新修地方志的專業隊伍。還應注意經過較長學習期限,培養具有較高水平的骨干力量,以利于新方志學的理論建沒。”自上一輪修志開展以來,學界對于志書主編素質問題也有所研究。有的認為,“作為一個合格的主編必須具有這樣幾方面的素質:一要有高尚的道德品格,要有不畏艱難、埋頭苦干和連續作戰的精神。二要有廣博的學識,包括哲學、社會科學知識、自然科學知識、地方歷史知識和方志學知識等。三要有較強的宏觀把握和調控能力,包括綜合分析能力、研討能力、決斷能力、協調能力等。四要有嚴謹和勤勉的工作作風。”[47]當代學界不僅論及修志人才的個體素質問題,而且還論及修志人才的群體結構問題。有的認為,修志專業班子群體結構必須符合四個原則,即“年齡結構上的橄欖型原則”“知識結構上的全面性原則”“智能結構上的多樣性原則”“個性結構上的協調性原則”。[48]有的認為,修志專業班子的群體結構必須符合三個要求,即“老、中、青三結合,以中青年為主體”“以高學歷、高學位和高職稱為主,以中等學歷和中級職稱為輔”“社會科學人才為主,以自然科學人才為輔”。[49]2015年8月25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全國地方志事業發展規劃綱要(2015—2020年)》指出:要“重視人才選拔、培養和使用,加強專兼職結合、結構合理的人才隊伍建設,培養和引進一批高端人才,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地方志編修、研究工作隊伍,弘揚修志問道、直筆著史的方志人精神。”
由上所述可知,修志責任和人才思想都已經歷從簡單到復雜的演變過程。隨著修志事業的不斷發展,人們對修志責任和人才問題的認識也必然隨之發生變化。近期,謝伏瞻同志指出:“方志人應樹立‘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即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際,實現省省、市市、縣縣有志有鑒,一個都不能少的‘兩全目標’,實現世界文化偉大創舉,在21世紀中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年即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之際,編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志,實現省市縣三級志書,鄉鎮志、村志、社區志、小區志和地方綜合年鑒全覆蓋等。”[50]可想而知,欲完成這樣一個偉大歷史任務,新一代修志者所承擔的責任將更加重大,新的修志事業對于修志人才的要求也將會有所變化。本文所以要對古往今來的修志責任和人才思想發展兩問題作初步梳理和總結,其目的就是要通過總結歷史經驗,從而為新時代修志事業發展提供某種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