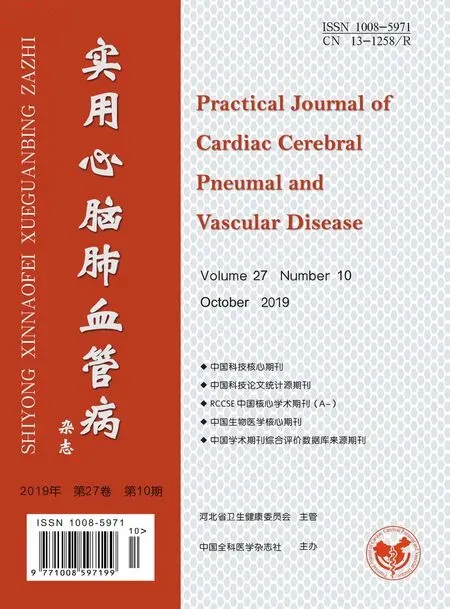心房顫動患者疾病接受度的影響因素及其與生活質量的關系研究
韓晴,蘆霜
心房顫動與心力衰竭、卒中、出血性疾病及血栓栓塞性疾病的發病率和病死率升高有關[1]。研究表明,心房顫動發病率隨年齡而變化,多數心房顫動患者年齡為65~85歲[2-3];60~70歲患者受心房顫動影響達3.7%~4.2%,≥80歲患者受心房顫動影響達10%~17%[4]。歐洲心臟病學會指出,心房顫動患者最常見的臨床癥狀包括虛弱、心悸、呼吸短促、胸痛、睡眠困難和社會心理困擾[5]。DUDINK等[6]研究表明,與心血管疾病不伴有心房顫動患者相比,心血管疾病伴有心房顫動患者日常活動更受限,健康狀況更差,因此臨床醫護人員更應該重視心房顫動患者的生活質量。CIPORA等[7]研究表明,有較高疾病接受度患者更能保持積極的身心調適能力,并對自身疾病康復和促進健康生活具有較大益處。本研究旨在探討心房顫動患者疾病接受度的影響因素及其與生活質量的關系,以提高患者對自身疾病的接受度,從而獲得更高的健康生活質量。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連續選取2017年6月—2018年6月在遼寧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住院的心房顫動患者160例,均經心電圖檢查確診。納入標準:(1)年齡50~85歲;(2)至少接受抗凝治療3個月;(3)受教育程度為小學以上水平并具備基本的識字閱讀能力。排除標準:(1)瓣膜性心房顫動;(2)急性冠脈綜合征等其他嚴重心血管疾病或紐約心臟病協會(NYHA)分級>Ⅲ級;(3)調查問卷填寫不正確或不完整;(4)癡呆、認知障礙或精神障礙。本研究經遼寧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所有患者及其家屬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方法
1.2.1 一般資料 采用調查問卷方式收集所有患者一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居住地、是否獨居、職業、吸煙史(連續或累積吸煙6個月或以上者)、飲酒史〔飲酒量的判定標準:將1杯標準飲酒量定為12 ml酒精(乙醇),即360 ml(12盎司)啤酒或180 ml(6盎司)葡萄酒或酒精濃度為9的飲品45 ml(1.5盎司),其中中度飲酒:男性≤2杯/d,女性或男性65歲以上≤1杯/d;危險飲酒:男性>14杯/周或1次性飲酒>4杯,女性>7杯/周或1次性飲酒>3杯,≥3次/周,連續4周中度飲酒以上即為有飲酒史〕、患病時間、合并癥、治療藥物〔包括維生素K拮抗劑(vitamin K antagonist,VKA)、新型口服抗凝藥(new oral anticoagulant,NOAC)〕及歐洲心律協會(European Heart Rhythm Association,ERHA)分級[8],其中ERHA分級為主治醫師根據患者癥狀嚴重程度及病史進行分級,Ⅰ級:無任何癥狀;Ⅱ級:癥狀輕微,日常活動不受影響;Ⅲ級:癥狀嚴重,日常活動受影響;Ⅳ級:致殘性癥狀,無法從事日常活動。
1.2.2 中文版疾病接受度量表(Acceptance of Illness,AIS)[9]中文版AIS包括8個條目,主要描述疾病給患者帶來的困難和限制,包括:(1)我很難適應疾病帶來的限制;(2)因為健康問題,我不能去做自己最喜歡的事情 ;(3) 疾病有時候讓我感到自己很無用;(4) 疾病使我比想象中更依賴他人;(5)疾病使我成了家人和朋友的負擔 ;(6)我的健康狀況讓我感到自己信心不足 ;(7)我將不可能因足夠自給而讓自己開心了;(8)因為我的疾病,我想我周圍的人會經常感到不舒服 。量表每個條目采用Likert 5級計分,“完全同意=5”“部分同意=4”“同意與不同意相等(沒有意見)=3”“部分不同意=2”“完全不同意=1”,總分8~40分,其中8~18分為低接受度,19~29分為中接受度,30~40分為高接受度。
1.2.3 世界衛生組織生活質量測定量表簡表(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Quality of Life-BREF,WHOQoLBREF)[10]WHOQoL-BREF共29個條目,其中包含2個獨立分析的問題條目,旨在了解患者個體的主觀感受;包含3個特有的條目,即家庭摩擦情況、食欲和自我評分;其余24個條目分為四個領域,即生理領域(7個)、心理領域(6個)、社會關系領域(3個)和環境領域(8個),各領域得分按正向記(即得分越高,生活質量越好)。WHOQoL-BREF得分根據公式轉換成百分制,即轉換后得分(百分制)=(原來得分-4)×(100/16),保留整數部分。
1.3 質量控制 調查問卷由研究人員在患者入院后3 d內發放,向患者說明本研究的目的和意義,研究人員運用統一的指導語向患者說明問卷的填寫方法與注意事項,由患者本人回答所有問題,如有疑惑,在場發放問卷的研究人員會予以解釋。調查問卷不記名,問卷完成后當場收回并檢查,如發現錯填或漏填及時向患者說明并更正。回收問卷后根據填寫內容進行數據錄入。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1.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分析采用χ2檢驗;心房顫動患者疾病接受度的影響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M(QR)表示,組間比較采用Kruskal Wallis H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共發放160份問卷,有效收回152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95.0%。152例患者中男68例,女84例;平均年齡(68.7±9.1)歲;婚姻狀況:未婚12例(7.9%)、已婚86例(56.6%)、離婚21例(13.8%)、喪偶33例(21.7%);受教育程度:小學45例(29.6%)、初中61例(40.1%)、高中/中專30例(19.8%)、大專及以上16例(10.5%);居住地:農村50例(32.9%)、城市102例(67.1%);獨居:是33例(21.7%)、否119例(78.3%);職業:有40例(26.3%)、無112例(73.7%);患病時間:<3年73例(48.0%)、≥3年79例(52.0%);合并癥:無16例(10.5%)、1~2種32例(21.1%)、3種及以上104例(68.4%);治療藥物:VKA治療21例(13.8%)、NOAC治療131例(86.2%);ERHA分級:Ⅰ級19例(12.5%)、Ⅱ級48例(31.6%)、Ⅲ級74例(48.7%)、Ⅳ級11例(7.2%)。
2.2 疾病接受度 152例患者中低接受度53例(34.9%)、中接受度83例(54.6%)、高接受度16例(10.5%)。
2.3 單因素分析 不同性別、居住地、合并癥及有無職業、吸煙史、飲酒史的心房顫動患者疾病接受度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年齡、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患病時間、治療藥物、ERHA分級及是否獨居的心房顫動患者疾病接受度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4 多因素分析 以表1中有統計學差異的指標作為自變量,患者對疾病接受度作為因變量(賦值變量見表2)進行多因素Logistics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受教育程度、獨居、患病時間、治療藥物、ERHA分級是心房顫動患者疾病接受度的影響因素(P<0.05,見表3)。
2.5 WHOQoL-BREF評分 不同疾病接受度患者的社會關系領域總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疾病接受度患者的生活領域、心理領域、環境領域總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1 心房顫動患者疾病接受度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n(%)〕Table 1 Univariate analysi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cceptance of illness in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表2 變量賦值Table 2 Variable assignment

表3 心房顫動患者疾病接受度影響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Table 3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cceptance of illness in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表4 不同疾病接受度心房顫動患者WHOQoL-BREF評分比較〔M(QR),分〕Table 4 Comparison of WHOQoL-BREF score in atrial fibrillatio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acceptance of illness
3 討論
患者接受疾病程度受疾病的癥狀強度、對治療滿意度、個人性格和治療方式、家庭支持和社會經濟狀況影響。患者接受自身疾病會產生安全感并能夠緩解相關負面情緒[11]。慢性疾病的高接受度不僅可以降低患者心理壓力,也可促進患者積極參與治療過程,進而提高患者治療成功率[12]。據統計,12%的心房顫動患者治療無效,50%~60%心律失常的患者在恢復竇性心律1年內復發,嚴重者導致住院,影響患者日常活動和社會活動[13]。
近年來,眾多研究人員開始關注患者對自身疾病的認知程度,并且通過相關護理措施使患者更加了解自身疾病,進而改善患者生活質量[14-15]。OBIEGLO[16]等對100例患者進行諾丁漢健康狀況問卷(NHP)和AIS的調查結果顯示,疾病接受度是患者生活質量的獨立預測指標,且患者受教育程度與疾病接受度呈正相關。但目前國內鮮有研究了解患者是否接納自己的患病狀態,因此本研究探討心房顫動患者疾病接受度的影響因素,并進一步分析疾病接受度與患者生活質量的關系,從而可更科學的進行護理指導與宣傳教育。
本研究結果顯示,受教育程度、獨居、患病時間、治療藥物、ERHA分級是心房顫動患者疾病接受度的影響因素;分析其原因可能是:(1)受教育程度高者能夠迅速和多元化地獲取醫療知識和醫療途徑,進而提高對自身疾病的認識及疾病的接受度。(2)非獨居患者擁有更緊密的社會人際關系,其能夠從伴侶或子女身上得到依靠和歸屬感,并且良好的家庭氛圍有助于緩解壓力,因此非獨居患者更易于接受自身疾病。(3)心房顫動患者在經過系統治療出院后逐漸適應自身心房顫動節律,且癥狀不會對生活造成特別嚴重影響,而患者心絞痛或心力衰竭發作會伴心房顫動加重,但通過休息或口服急救藥物而自行緩解,因此患病時間長的患者會越來越不重視心房顫動,導致疾病的接受度較低。但CYBULSKI等[17]研究表明患病時長與患者疾病接受度無相關性,本研究結果與之不一致的原因可能與該研究納入的研究對象年齡差異較大有關。(4)口服VKA對飲食要求較嚴格,且還需定期監測凝血功能,患者依從性和自律性均較好,因此其疾病接受度也較高。(5)有研究表明,ERHA分級越高表明患者癥狀越嚴重,疾病接受度越高[10],可能是ERHA Ⅳ級患者無法從事日常活動,需要專人看護,而ERHA Ⅰ~Ⅱ級患者日常活動均不受影響,因此癥狀越重患者的疾病接受度也越高。
世界衛生組織(WHO)對生活質量的定義為個人在生活文化和價值體系以及與個人目標、期望、標準和關注下對自身生活地位的感知[18]。生活質量是評價慢性疾病患者健康狀況的重要指標之一,可綜合反映人的身體機能、心理功能和社會功能。生活質量的評估和對疾病的接受度能夠識別心房顫動患者所產生的問題和需求,也能提供優化的以患者為中心的護理干預。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疾病接受度患者的生活領域、心理領域、環境領域總分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且疾病接受度高患者生理領域、心理領域和環境領域中的總分較高,因此疾病接受度高的心房顫動患者具有更好的生活質量。美國心臟病學會基金會/美國心臟協會/心臟節律協會/美國心血管造影和介入學會的指南強調,在標準臨床實踐中心房顫動患者的生活質量能夠作為評估治療成功的終點[19]。《2016年歐洲心臟病學會(ESC)心房顫動管理指南》[20]中明確指出,規劃心房顫動患者護理并向患者解釋管理心房顫動的預期益處能防止不良預后和優化患者生活質量。護理干預會對患者的生活質量產生積極作用,在臨床實踐中,護理人員可向患者進行健康教育,只有患者了解疾病、接受疾病才會引起其對自身疾病重視,進而理解預防方法及自護方法,最終提高自身生活質量。
綜上所述,受教育程度、獨居、患病時間、治療藥物、ERHA分級是心房顫動患者疾病接受度的影響因素,且疾病接受度與患者生活質量有關。因此在臨床實踐中護理人員不僅要提高心房顫動患者對自身疾病認識,還要了解心房顫動患者疾病接受度,能夠有針對性地對疾病接受度低患者進行更多護理干預,以提高患者疾病接受度,從而達到改善生活質量的目的。本研究納入樣本量較小,且為單中心,因此可能造成選擇性偏倚;另外,目前對心房顫動癥狀的嚴重程度尚無明確評價標準,有國外文獻表明,ERHA對評估心房顫動嚴重程度具有一定意義[21],但國內尚無文獻表明其對亞洲人同樣適用,因此直接引用作為本研究心房顫動癥狀嚴重程度的評價標準也稍顯不妥。
作者貢獻:韓晴、蘆霜進行試驗設計與實施、資料收集整理、撰寫論文并對文章負責;韓晴進行試驗實施、評估、資料收集;蘆霜進行質量控制及審校。
本文無利益沖突。
延伸閱讀
疾病接受度于1956年由DEMBO等學者提出,其最初被描述為接納失落感,旨在使患者了解認識疾病的積極意義,并通過整合疾病體驗及生活方式而使患者重新獲得控制感,是臨床衡量患者疾病適應程度的重要心理學指標。大量臨床研究表明,患者疾病接受度越高則其健康促進行為、治療依從性及生活質量越好,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