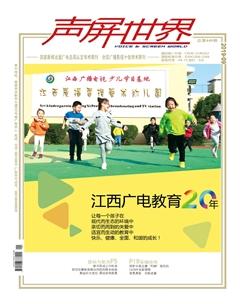中國慢綜藝的創新發展研究
王川川
摘要:近年來,在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的政策引領之下,電視節目導演以富有創新的審美感知力以及對市場極強的敏感度制作出慢綜藝這一新的節目樣態,但很快因不斷跟風模仿陷入了同質化的局面。湖南衛視《我家那小子》打破了模式化的僵局,昭示慢綜藝未來發展的趨勢。文章以《我家那小子》《幸福三重奏》為例,從去陌生化的制作理念、多元評論的環節設置以及獨居明星群像展示的話題性三個方面進行對比分析,以此來論述未來慢綜藝發展的成功之道。
關鍵詞:慢綜藝 《我家那小子》 《幸福三重奏》
我們正處于后現代化的文化語境中,快節奏是觀察與體驗世界的方式。多年來電視節目導演對于快節奏的“奔跑秀”“親子秀”進行著孜孜不倦的跟風制作,釋放觀眾的荷爾蒙,滿足他們的窺視欲、“八卦”心成為節目的定位。隨著“世界很大,我想出去走走”的生活理念生根發芽,“回歸生活,好好生活”成了普遍的心理需求,慢綜藝這一新的節目樣態應運而生。湖南衛視2014年推出的《花兒與少年》是慢綜藝的初次試水。索福瑞數據來源顯示,周五、周六、周日晚間省級衛視所有綜藝節目排名,《花兒與少年》穩居第一,收視率最高可達到1.918%,可見其歡迎程度。后來湖南衛視在2017年相繼推出《向往的生活》《中餐廳》《親愛的客棧》都取得了不錯的反響。但隨著“情感雞湯”的濫用,觀眾逐漸產生了審美疲勞,慢綜藝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發展的困境。2018年湖南衛視推出的《我家那小子》延續了慢綜藝的美學特征,將節目品質內涵進行了深度挖掘與提升,其開創性地以親人嘉賓,以及“旁觀者”明星嘉賓的主觀視角觀察獨居明星的真實生活狀態以及內心情感世界,并從多元的角度詮釋了慢文化之下“好好生活”的理念,最重要是深度挖掘了都市社會性話題,引發人們的思考和討論。筆者為了使讀者理解《我家那小子》的節目創新性,將網綜《幸福三重奏》與其進行對比研究。
去“陌生化”,貼近真實生活本身
俄國形式主義學者什克洛夫斯基認為“藝術的手法是事物的陌生化手法,是復雜化形成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難度和時延”。①這一觀點長期影響著藝術家的創作理念,新奇特、超越常規、感官的刺激成為其創作的宗旨。傳統慢綜藝就是將人物、環境、事件進行陌生化處理,使觀眾產生新奇的觀感、超越生活本真的擬態化體驗。比如網綜《幸福三重奏》將三對家庭置于北京郊區陌生的房子里面,讓其過一段無打擾的理想化生活,夫妻相處之道成為節目的重心,于是情感、情緒通過各種電視手段被無限擴大,觀眾從中得到窺視欲的滿足。因此,陌生化只是給觀眾提供了一個可被窺視的新奇敘事空間,缺少的是對生活本身的思索和人生意義的探討。《我家那小子》摒除了陌生化的手法應用,將節目主題定位為“好好生活”,呼喚人們回歸生活本真。因此,在節目進行過程中,不同年齡層次的明星嘉賓生活狀態被真實地記錄下來。生活環境是熟悉的,遇到的人是熟悉的,遇到的事是真實的,沒有被刻意放大,明星的軟弱、痛苦、無助、孤單被真實展現,第一次讓人們真正看到了明星真實的內心世界,更讓都市男女們感同身受。朱雨辰“怎么就沒有一個人愿意陪在我身邊”成為千千萬萬都市男女的心聲,睡在狗窩的影像記錄更讓觀眾深刻體會到一種孤獨感。因此,真實成為慢綜藝最有說服力的審美元素。
多元評論元素,增強節目內涵張力
在傳統的慢綜藝中,參演明星嘉賓按照導演預先設計的環節進行“真實”的擬生活展現,觀眾在觀看的過程中,基于個人的理念、生活閱歷等進行主觀、隨意、片面的評價,或多或少對節目產生負面的影響。《幸福三重奏》在節目最后通過對路人的采訪,將幸福的概念進行深化,提升了節目的親和力。但是未免有牽強附會之嫌,與前面節目環節的銜接性較弱。《我家那小子》評論元素的融入,增強了節目本身的廣度和深度,尤其在新媒體發展的大環境之下,評論引導了網絡輿論的導向性,形成延展性話題討論,最終擴大了節目的影響力。同時,《我家那小子》區別于傳統綜藝節目的單方評論,它體現出多元化的評論特征。在傳統的綜藝節目中,評論身份要么是專家,其評價機制融入到綜藝節目流程設計中,并成為提升節目品質、價值導向的一種重要因素;要么是主持人,其一方面點評事件或故事本身,起到四兩撥千斤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是節目流程順利進行的重要保證。在《我家那小子》節目中,觀察評論者由三個身份群體組成,一是主持人,二是情感觀察嘉賓,三是參演明星的親人。主持人穿針引線,情感觀察嘉賓根據自己的經驗進行點評,而主要點評人是明星親人。他們跟參演明星既親近又陌生,一方面可以對觀眾費解或感興趣的明星“八卦”進行闡述說明;另一方面,作為觀察者,以“獵奇”的心態去觀看孩子的生活狀態,從而真正達到溝通交流的目的。因此,在多重評論的話語交鋒中,一個意義空間被無形創造出來,觀眾會緊跟節目的主題進行話題討論,最終實現節目品質及內涵的提升,保證了價值觀的正確性。
獨居明星群像展示,話題熱點性高
慢綜藝明星嘉賓的選擇首先要符合節目的定位,選用流量明星、新晉演員等是慣用的手段。因為其自帶流量、自帶話題,對于節目收視率或者點擊率而言,至關重要。《我家那小子》參演明星陳學冬、錢楓、徐海喬(替代朱雨辰)、武藝,各自家庭背景復雜,但也是眾多中國家庭中的典型個案,比如武藝母親與父親因性格不合長期分居;陳學冬父母親離異,大姨撫養其長大等,每一位明星自帶話題熱度。其次在傳統的慢綜藝中,我們會看到明星與陌生人之間的對立沖突,外在的矛盾沖突被人為設計,長此以往,便容易被觀眾所詬病。《幸福三重奏》中嘉賓的選擇是處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三對家庭:一對是寵妻、愛女兒、“兒子是充話費送的”話題家庭汪小菲和大S,一對是正在懷孕、演技在線的陳建斌和蔣勤勤家庭,一對是象征中日友誼乒乓球的福原愛家庭。節目重點依然是外在的事件沖突展現,比如大S騎自行車與汪小菲產生矛盾,蔣勤勤出門前因陳建斌不耐煩而生氣等,真實但又有“蓄意”之嫌。而《我家那小子》重點是都市獨居男人面臨的普遍的精神困境,是一種群像展示,內在的戲劇沖突是重點,這樣做更容易拉近與觀眾之間的心理距離,從而提升話題的社會熱點性。在此,針對綜藝節目受眾群體的觸媒習慣,筆者將“新浪微指數”作為數據支撐來對比分析兩個節目。
筆者截取了2018年7月15日至9月10日的微指數數據,如圖1所示,播出當天以及后續時間內,《我家那小子》的話題熱點性比《幸福三重奏》高,話題熱度持續性強,并且衍生話題內容多樣,每一期幾乎都有一個熱點衍生話題供觀眾討論,比如陳學冬大姨、武藝弟弟、朱雨辰媽媽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陳學冬大姨”衍生話題隨著每期節目的進行,因其點評辛辣,被推上了新浪熱搜,更有網民表示“看節目就是為了看家屬評論的”。由此可見,一方面星素嘉賓組合的使用成為吸引觀眾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明星嘉賓的選擇要考慮其群像特征,《我家那小子》中明星嘉賓獨居、單身、苦悶、精神困頓,是都市男女普遍精神狀態的真實寫照,因此,話題參與度高,容易引起觀眾的認可。同時,需要說明的是,將“新浪微指數”作為數據支撐,有一定的偏頗性,因為《我家那小子》粉絲群體趨于年輕化,微博是其主要的話語載體,“微指數”相對較高。而《幸福三重奏》中夫妻檔的嘉賓選擇,受眾群體的年齡范圍有限,對微博的使用量有待商榷。
結語
慢是一種方式,也是一種態度,更是一種價值觀的體現。中國慢綜藝要尋求發展,取決于節目品質的提高。相比較傳統的綜藝節目,它更加需要文化內涵的提升,用小節目體現深內涵、大情懷。怎么做?首先,強化內在戲劇沖突的建構。新媒體環境下,如何能激起觀眾的興趣,產生共鳴感是關鍵。我們需要做的就是要創造話題,一方面制作方通過團隊進行話題炒作,通過官微進行話題引領,另一方面就是觀眾自發而成的觀感體驗,最終演變為熱點話題。因此,電視節目導演需要通過視聽元素深層次地打動觀眾,拉近和觀眾之間的心理距離,使其產生共鳴。傳統的慢綜藝顯然將人與環境、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對立作為重點,而未來慢綜藝需要將戲劇沖突由外在轉向內在,將觀眾普遍面臨的問題真實地展現出來,體現出更多的人生意義和人生價值。比如《我家那小子》節目中展現的精神困頓成為其成功的關鍵。內心獨白被影像真實記錄,自白成為自圓其說的堅強。最終,觀眾與明星之間建立了共同的話語體系,進行有效地意義互動。其次,文化內涵的融入,正能量的傳達。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藝術作品應該彰顯精神高度、文化內涵、藝術價值,注重作品自身的品格。一直以來,中國傳統的綜藝節目依然是以競技等娛樂環節取勝,文化內涵、正能力的融入相對較難,除了文化類電視節目之外,其他綜藝節目很難實現其普世價值。《我家那小子》雖做出了嘗試,但整體上節目正能量的傳達還比較弱,更多仍然是對觀眾窺視欲的滿足。總之,電視節目導演應該在慢綜藝中將“好好生活”的理念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弘揚新時代的精神,制作出更多的小成本、大情懷、正能量的慢綜藝節目。(項目課題:山西省藝術科學規劃課題“山西故事影視傳播歷史與發展趨勢研究”,項目編號:2016C07)
(作者單位:山西傳媒學院)本文責編:邵滿春
注釋:① [俄]什克洛夫斯基著,方? 珊譯:《俄國形式主義論文》,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