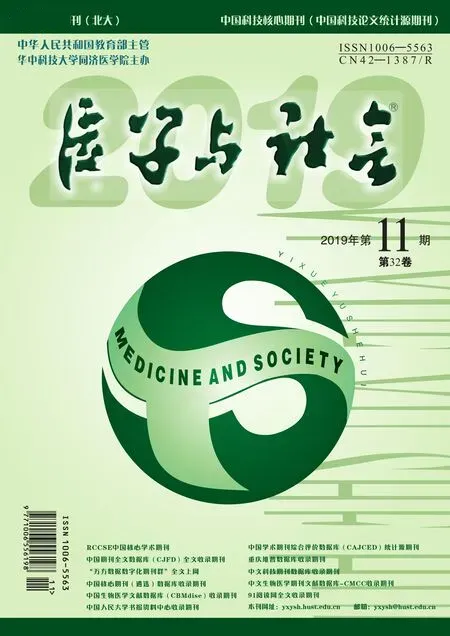我國神經內科醫師職業倦怠亞型分布狀況調查
田 露 蒲俊材 劉藝昀 鐘小鋼 桂思雯 徐韶華 宋學冕 王海洋 周 維 謝 鵬,3,5
1重慶醫科大學公共衛生與管理學院,重慶,400016;2重慶醫科大學神經科學研究中心,重慶,400016;3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神經內科,重慶,400016;4重慶醫科大學生命科學院,重慶,400016;5中國醫師協會神經內科醫師分會,北京,100010
職業倦怠反映的是個體在長時間工作和人際情感壓力下形成的一種身心疲憊、耗竭的狀態[1]。從事服務型工作的群體,特別是醫務工作者,更容易經歷倦怠[2]。醫師職業倦怠對醫生和患者都有危害,長期的工作壓力和緊張的醫患關系使得醫生情感衰竭、待人冷漠,使醫師的心理健康受損,進而影響醫師與患者、家人、同事之間的人際關系[3]。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患有神經退行性疾病和腦血管疾病的人群迅速增多,社會對神經內科醫師數量和服務質量的需求也不斷提高。已有研究表明神經內科是為數不多的高倦怠率、低滿意度的專業之一[4],因此有效地干預神經內科醫師倦怠,保證醫師身心健康,是應對當前腦疾病嚴峻挑戰的重要舉措。國內外研究者使用聚類分析對教師、律師等進行類型學的研究,發現職業倦怠可分成不同亞型[5-7],影響亞型分類的因素也不同,這對研究神經內科醫師倦怠具有參考價值。因此,本研究以全國神經內科醫師為例,科學地識別神經內科醫師的倦怠亞型,綜合探究職業倦怠亞型的影響因素,有助于醫院等相關部門合理地開展針對化和差異化的防御措施,實現“精準預防和干預”。
1 資料來源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中國醫師協會神經內科醫師分會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進行的第一次全國神經內科醫師執業現狀調研[4]。調研面向全國30個省份,共收集5590份問卷,其中221份由于Maslach職業倦怠量表數據缺失予以排除,最終納入5369份問卷。
1.2 研究方法
職業倦怠采用Maslach職業倦怠量表測量,評價體系包括情緒耗竭、去人性化、低成就感3個維度,共15題,每題0(完全不符合)-6(完全符合)級計分,當情緒耗竭維度≥27分或去人性化維度≥10分時,則認為被試者存在倦怠癥狀[8]。心理健康狀況采用一般健康問卷(GHQ-12)測量,主要評估神經內科醫師的心理健康水平,共12個條目,總分范圍為0-12分,累計得分≥4分則認為存在心理健康問題。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以等級結果表示,工作壓力分為:沒有壓力、壓力較小、壓力一般、壓力較大、壓力很大;工作滿意度分為:非常滿意、比較滿意、一般、比較不滿意、一點也不滿意。
1.3 統計學方法
運用SPSS21.0統計分析軟件進行描述性分析、聚類分析、Pearson相關性分析、秩和檢驗和卡方檢驗。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基本情況
5369名神經內科醫師的基本情況見表1。
2.2 神經內科醫師的職業倦怠現狀及分型
神經內科醫師倦怠率高達53.2%,相關性分析表示倦怠各維度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且符合正態分布,具備進行聚類分析的條件(表2)。本文使用兩步聚類方法對倦怠三個維度進行快速聚類(聚類前,先將各維度得分轉化為Z分數),系統將數據自動聚為兩種亞型(見表3)。非參數檢驗結果顯示,亞型1在低成就感維度中的得分最高,而情緒耗竭和去人性化維度得分較低,因此將其解釋為低成就感型;亞型2中情緒耗竭、去人性化維度的得分較高,低成就感維度的得分偏低,可理解為系統將情緒耗竭和去人性化維度中得分較高的自動聚為一類,因此將其解釋為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型。
2.3 神經內科醫師人口學特征在職業倦怠亞型上的分布
20-35歲的神經內科醫師在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型中比例最高(χ2=56.424,P<0.001),而35-50歲的神經內科醫師在低成就感型中比例最高;中級職稱在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型中的比例最高(χ2=61.135,P<0.001),高級職稱者在低成就感型中的比例最高;在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型中,月收入8000元以下的神經內科醫師(χ2=36.291,P<0.001)占比最高;工作時間>55h的神經內科醫師倦怠發生率高于工作時間短的醫師(χ2=18.195,P<0.001),且工作時間>55h的醫師占比最高,具體見表1。
2.4 神經內科醫師職業倦怠亞型分類的影響因素
表1的結果顯示:不同的年齡、職稱、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月收入、每月夜班次數、每周工作時間,以及是否有小孩這些因素在倦怠亞型分布上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 0.05)。另外心理健康狀況、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與職業倦怠亞型分布相關。其中,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型的倦怠發生率(χ2= 2035.347,P<0.001)高于低成就感型,以及心理問題發生率(χ2=591.825,P<0.001)也高于低成就感型(表4)。

表1 神經內科醫師的基本情況
注:a若總人數少于5369,則為缺失值所致;b亞型1,低成就感型;c亞型2,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型。

表2 倦怠與心理健康狀況、工作滿意度、工作壓力的相關性分析
注:*P<0.05,**P<0.01。

表3 神經內科醫師亞型的倦怠特征和心理健康狀況
注:a亞型1,低成就感型;b亞型2,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型;因數據呈非正態性分布,以中位數(四分位間距)表示。

表4 神經內科醫師職業倦怠亞型的單因素分析
注:a亞型1,低成就感型;b亞型2,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型;因數據呈非正態性分布,以中位數(四分位間距)表示。
在壓力度等級中,壓力非常大在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型中占比65.3%,壓力越大,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型的倦怠發生率越高(P<0.001);在滿意度等級中,一點也不滿意和比較不滿意都主要聚集在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型中,分別占比83.9%和59.7%,滿意度越低,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型的倦怠發生率越高(P<0.001)(表5)。

表5 神經內科醫師職業倦怠亞型的單因素分析
注:a亞型1,低成就感型;b亞型2,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型;因數據呈非正態性分布,以中位數(四分位間距)表示。
3 討論
3.1 神經內科醫師倦怠程度嚴重,科學分型以辨別倦怠群體異質性
結果顯示我國神經內科醫師的職業倦怠狀況較為嚴重,倦怠率達53.2%。聚類分析可辨別出職業倦怠者的群體異質性,是對既往現狀描述、因素分析和關聯研究的有效補充。已有研究根據職業倦怠嚴重程度劃分亞型[6],而本研究根據倦怠各維度的得分構成來劃分亞型,將我國神經內科醫師群體分為低成就感型和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型,側重于倦怠內在結構的差異,這與Bauernhofer[9]劃分標準是相同的,各亞型在職業倦怠維度得分的差異表明亞型之間有較高的異質性。本次研究沒有識別出情緒耗竭型和疲倦型,研究[8-9]顯示情緒耗竭型是倦怠特征最嚴重的,而疲倦型是倦怠特征較輕的,結果顯示兩種倦怠亞型屬于中等偏高水平,這也可以側面顯示出我國神經內科醫師職業倦怠程度整體處于中等偏高水平,必須引起醫師和管理者的重視。
3.2 人口學特征影響神經內科醫師倦怠分型
以往研究[10]發現男性醫師的倦怠發生率顯著高于女性醫師,而本研究發現性別因素在倦怠亞型中的分布無統計學差異,這表明男性和女性醫師在高強度的工作壓力之下,均存在發展為倦怠者的危險性。青年醫師在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型中比例高于低成就感型,而中年醫師在低成就感型中比例較高。原因可能是青年醫師初入職場,高期望值與現實之間存在差距,面對新角色和環境,以及工作、家庭生活帶來的系列壓力,青年醫師更易出現倦怠癥狀,這與楊平[11]的研究結果一致;而中年醫師在事業上已獲得一定成就,發展出對成就的鈍感力,且因為期待高、時間少、自我提升空間變小,所以個人成就感較低。此外工作時長是影響職業倦怠的重要因素,工作時間越長,醫師的倦怠發生率越高,且工作時間>55小時的醫師,在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型中所占比例高于低成就感型。相關研究[4]也表明工作時間延長會導致倦怠和抑郁,影響工作態度和工作效率。
3.3 心理健康狀況、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因素影響神經內科醫師倦怠分型
倦怠嚴重影響醫務人員的身心健康和工作效率,本研究發現神經內科醫師心理健康狀況與倦怠顯著相關,這與前期研究[4]的結果一致。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型的心理健康狀況得分≥4分,表明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型對醫師心理健康狀況的損害程度比低成就感型嚴重;以及工作壓力大、工作滿意度低的神經內科醫師在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型中的比例最高,因此可以認為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型的倦怠嚴重程度高于低成就感型,是職業倦怠預防和干預的重點。可以認為神經內科醫師的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一定程度上均能預測心理健康狀況。作為一種典型的壓力反映,職業倦怠最主要的誘因就是臨床工作壓力,醫務人員工作壓力越大,工作滿意度越低,職業倦怠水平就越高。聚類亞型對醫師進行職業倦怠及心理健康評估具有重要意義,表明對神經內科醫師職業倦怠和心理健康狀況干預,應關注倦怠亞型的分類,以減壓為基礎,提升其工作滿意度,從而針對性地解決職業倦怠和心理健康問題。
4 建議
結果影響顯示,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型的醫師倦怠嚴重程度高于低成就感型,因此管理者和醫師應當根據倦怠亞型的差異性,制定針對性的、具體的干預措施。首先,中年醫師和較高職稱的醫師主要屬于低成就感型,因此管理者應積極引導他們參與組織管理、充分發揮經驗與智慧,如開展學術交流、教學講座等,實現對其成就的認可;對于低成就感醫師本身而言,首先要對自己和工作有清晰的認知,明白自己擅長和需要改進的地方,隨時保持對工作的熱忱,積極參與外出進修學習的機會,努力突破工作的瓶頸。其次,對于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型的醫師,應減少其工作壓力、心理壓力,如重新規范神經內科醫師的工作流程,促進科室內部人力資源的合理流動,合理縮短值班時間和減少夜班次數等,減輕醫師的工作強度;對于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型的醫師本身而言,主要就是緩解倦怠感,保持良好的心態,學會緩解壓力,培養自己生活中的興趣愛好,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轉移注意力,從而達到舒緩工作壓力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