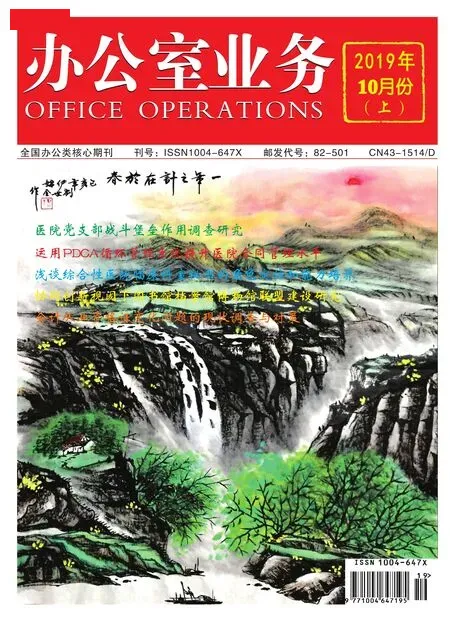關于檔案展覽的思考
文/諸城市檔案館 李培杰
檔案展覽是各類檔案機構舉辦的最重要的文化活動之一。傳統檔案展覽形態比較單一,伴隨社會的發展——尤其是計算機信息技術的普及——檔案展覽的形態越來越多樣化,在實體展覽之外,出現了互聯網展覽、手機端展覽等新型展覽。而虛擬影像、人工智能等現代科技引入檔案館的展廳,也使得展廳更加高端大氣。與此同時,學術界也將更多的關注投向了新型展覽和現代科技如何應用于展覽,而看似簡單、低端的傳統展覽則受到冷遇。
互聯網展覽和手機端展覽,我們可以統稱為線上展覽或者虛擬展覽。理論上,線上檔案展覽依托于強大的互聯網,可以實現快速傳播,覆蓋廣大的用戶。據統計,截至2018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已達8.29億。如此龐大的網民規模,都將是線上檔案展覽的潛在用戶。然而實際上,我國檔案館在社會公眾中的知曉度和認可程度是偏低的,各級檔案館所建立的網站、微博、微信公眾號、手機客戶端等平臺,其活躍用戶數量都是非常少的,成功案例鳳毛麟角。尤其是級別較低的市縣級檔案館,其影響主要局限于本地,所謂“粉絲”更多的是本地各個政府機關“互粉”,缺少真實的用戶。線上展覽,現在仍然只是“看上去很美”。
將現代科技引入檔案展廳,是非常有必要的。在現實中,也有不少檔案館在展廳中應用了最新的科技元素,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吸引了大量參觀者前來。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我國多數檔案館——尤其是低級別的地方檔案館,每年接待的查檔者數量都是比較少的,而參觀展廳的人數則更少,與博物館、文化館等文化機構的接待量相比,相去甚遠。建立一個配備了現代聲光電技術的展廳,需要花費幾十萬、幾百萬甚至更多的資金,而接待的參觀者則非常有限,“投入產出比”是非常低的。
筆者工作于縣級檔案館。檔案館有自己的網站,在網站上設有線上展覽,在館內也設有展廳。工作人員在籌備展覽之時,不可謂不用心,然而參觀者卻寥寥,線上展覽無人問津,展廳每年接待來客不過百余人。參觀展廳的來客,絕大多數是因公來館內交流學習的外地檔案館工作人員,再就是國際檔案日等特殊時間來參觀檔案館的機關干部。每見偌大的展廳無人參觀,筆者倍感痛心。
聽館內的老同志說,前些年檔案館新館還未建成的時候,老館辦公條件很差,沒有專門的展廳,工作人員就制作可移動的展板搬到城市的中心廣場去展出,路過的人無不駐足觀看,人們有疑問,工作人員現場解答。這種展覽,非常質樸,沒有最新的科技設備,只需花費很少的錢,然而取得的效果卻是極佳的。
筆者在查看國外檔案館的網站時發現,國外檔案館雖然也在網站上設有線上展覽,部分檔案館也將新科技應用到展廳中,但傳統的展覽并未因此而削弱。檔案館在開設新型展覽的同時,仍然會不斷推出可移動展覽,送展覽到社區、學校、博物館等處。
新型展覽的產生,并不意味著傳統展覽的消亡。雖然新型展覽更加“高大上”,但傳統的可移動展覽更加親民。無論線上展覽,還是建立現代化的展廳,都是“坐等參觀者上門”。因為受眾數量少、檔案館假期閉館等因素的存在,檔案館能“等來”的參觀者必然是極為有限的。要想改變這種狀況,絕非一日之功。我國檔案館,尤其是地方檔案館,在建立線上展覽和現代化展廳時,不應盲目立項,而應該充分考慮到地方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和潛在的用戶數量。檔案館應重拾曾經的好傳統,更多地推出可移動展覽,由“坐等參觀者上門”改為“送展覽上門”,將展覽送到農村、學校、醫院、社區、廣場、路邊等,讓檔案展覽真正實現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