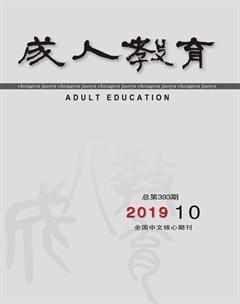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國農民職業化培育的變遷與展望
樊夢瑤 張亮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改革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而解決好農民問題始終是改革工作的核心。回顧四十年農民職業化培育的發展與演變歷程,大體分為新時期、新世紀、新階段。農民概念由傳統農民向新型農民、新型職業農民發展,農民職業化培育由農民素質教育向新型農民培訓、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發展。我國已進入新時代,要全面促使農民回歸到職業屬性,未來的職業農民培育將向著制度化、組織化與小農戶和新型經營主體雙向耦合趨勢發展。
【關鍵詞】農民;職業化培育;改革開放四十年
【中圖分類號】F3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8794(2019)10-0043-05
【收稿日期】2019-01-08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新型職業農民‘兩新融合機制研究”,項目編號為15BJY104
【作者簡介】樊夢瑤(1994—),女,河北保定人,在讀博士生,研究方向為農林經濟管理;張亮(1971—),男,河北東光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職業農民培育。改革開放歷經四十年,我國進入社會主義新時代,農村改革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即將完成,但仍存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并且在鄉村尤為突出。解決“三農”問題始終是改革的重中之重,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使農民成為鄉村振興的主體力量。[1]伴隨著社會發展及制度變遷,農民的內涵和針對農民的培育也發生了深刻變化。改革開放初期,農民的發展主要伴隨著戶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市場經濟的實施發生轉變。新世紀以來,由于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及農業轉型升級要求,新型農民向新型職業農民發展邁進。進入新時代,農業現代化的目標賦予了農民更重要的責任與使命。[2]農民始終是動態發展的群體,農民職業化培育也經歷了農民素質教育、新型農民培訓、新型職業農民培育三個階段的發展,由培訓工作轉變為培育工作。十九大以來,職業農民更具勞動、報酬、發展、保障等顯著的職業屬性,[3]同時也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主體力量。通過梳理和分析我國農民職業化培育不同階段的發展規律,展望其發展趨勢,對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實現鄉村振興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農民內涵的發展
農民這一稱呼已延續了幾千年,其內涵一直是社會學和經濟學界爭論的焦點。《辭海》中,農民是指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社會主義初期,農民具有很強的身份屬性,呈現出結構性特征。[4]1958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第一次明確將城鄉居民區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種不同戶籍。凡是具有農業戶口的居民(不管他從事何種職業)劃定為農民。農民的職業屬性逐步被身份屬性所覆蓋,成為區別于城市人口的社會學概念。[5]這是中國目前法律上確認農民的唯一標準。戶籍制度圈定了農民身份,把農民演變成為“農業戶口”的代名詞。當時我國對于農村集體產權制度發展處于探索的初級階段,常常將農民跟生產資料所有制聯系起來,即擁有生產資料(如土地等),我們稱之為“農民”。改革開放后,我國的一些學者開始從職業的角度來給農民下定義,主要指集體農民。農民的內涵發展可劃分為新時期傳統農民的演變、新世紀“新型農民”的萌芽、新階段“新型職業農民”的發展三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1978—1999年):新時期農民的演變
改革開放初期,全國大多數地方仍以戶籍作為依據對農民進行界定。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鄉鎮企業及第三產業快速發展,戶籍制度進行了初級改革,城鄉勞動力開始半開放式的自由流動。1984年10月國務院發布《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集鎮落戶,農民呈現出“亦工亦農”的雙重身份,“農民工”成為這一時代特殊農民群體的代名詞。[6]農民工指在城市從事非農業生產活動但具備農村戶口的農民,他們從原本的農業生產中脫離出來,投入到非農產業。同時期鄉鎮企業的崛起,也為農民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會,他們開始了“離土不離鄉”的生活。上世紀90年代,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逐漸飽和,部分農民看準改革開放浪潮中城市存在的新機遇,開始“離土又離鄉”的生活。[7]至二十世紀末期,農民工處于快速發展時期,農民的分化程度逐步擴大。十一屆三中全會農村率先改革不適應當時發展的生產力關系,從人民公社體制轉為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家庭成為農業生產經營的組織者和管理者,這一農村突破性變革標志著以農戶為基本生產單位的農村經營制度正式確立,農民變成農業生產的主導者。通過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人才自由流動、就業自由選擇、行業分工日趨交叉整合。“農民”一詞的理解也開始容納許多變化性的、發展性的因素。總的來看,在此時期的農民是傳統農民,逐步指向在農村居住并且長期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人。
(二)第二階段(2000—2011年):新世紀“新型農民”的萌芽
進入新世紀以來,伴隨著土地流轉政策的實施與城市化進程的推進,農民又有了新的內涵。2003年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依法流轉,部分農民自愿把土地的承包經營權流轉出去,這部分農民雖具有“農民”身份但卻不進行農業生產活動,即發展為“無地農民”,而流轉到土地的農民逐漸轉向規模化農業生產,變成種植大戶、家庭農場主及合作社負責人。在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新型農民”的概念,基于提高農民整體素質,明確了“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能力素質要求。在城鎮化發展背景下,大量青壯年勞動力轉移,農村實用人才向“非農化”發展,農村“能人”外流。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弱質化嚴重,帶來的是農村的空心化和農村社會的活力退化,農村勞動力素質呈結構性下降,同時新生代農民工存在新的就業問題。在此期間,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懸殊,農民教育發展滯后嚴重,農村亟須農業人才。而現代化農業具備現代產業組織特征,對從業者的文化素質和技術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會經營、善管理、具備市場經濟意識的“新型農民”愈發重要,該群體的培育和壯大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培育“新型農民”,發揮其在建設新農村中的主體作用,明確培養新型農民不僅需要教育培訓來培養專業技能,提升自身素質,也需要通過扶持和環境建設去保障其自身發展及其與產業部門的有效結合。新型農民是與時俱進且具有一定的經濟基礎、生產規模和創業需求的農民。此階段新型農民不再局限于農業生產,同時涵蓋經營、管理與服務工作,具有身份多重性的特征,主要指具備“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能力素質要求,從事農業規模化生產的創新型農民。[8]
(三)第三階段(2012—2018年):新階段“新型職業農民”的發展
2012年,中央一號文件立足我國農村勞動力結構和職業教育的新變化,著眼現代農業發展的新需求,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職業農民,新型職業農民概念由此產生。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農民和農村實用人才,準確把握新型職業農民主要類型及內涵特征,指明了轉變農業經營方式,發展現代農業的人才隊伍建設方向。2014年,在《關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中,黨中央提出加大對新型職業農民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領辦人的教育培訓力度,并建立培育制度。2015年,中央財政安排農民培訓補助資金11億元,農業部正式啟動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程,集中力量、突出重點、迅速及時有針對性地培育一批新型職業農民,支持新型經營主體發展。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立足農業供給側改革重點,以實現全面小康為目標,以農業提效為重點,提出“加快培育新型職業農民”。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以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為目標優化農業從業者結構,深入推進現代青年農場主、林場主培養計劃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頭人輪訓計劃,探索培育農業職業經理人,培養適應現代農業發展需要的新農民。[9]在“十三五”全國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發展規劃中提出,到2020年,新型職業農民總量超過2 000萬,并建立“一主多元”的新型職業農民教育培訓體系。十八大期間,中央一號文件持續關注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問題,不斷強調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迫切性,指出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是中央統籌城鄉、推進四化同步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標志著我國農民素質的革新和身份向職業的轉變。在此期間,我國在經濟、社會等方面獲得了飛速發展,農業現代化腳步加快,科技型農業發展需求強烈,現有勞動力很難適應農業的發展。發展現代農業,保障糧食安全,促進農業農村發展的可持續,都需要“愛農業、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
二、農民職業化培育的變遷路徑
農民職業化培育在改革實踐中逐步發展,前期以科教興農為基本要求,以提高農民素質,促進勞動力轉移為目標開展教育培訓;后期在實現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業現代化的要求下,經過不斷的探索,向職業化的培育轉變。改革開放后,農民職業化培育可以劃分為農民素質教育、新型農民培訓、新型職業農民培育三個發展階段。
(一)第一階段(1978—1999年):農民素質教育
改革開放后,農民整體素質較低難以適應農業生產的要求,國家開始重視以提高農民素質為目標的教育培訓。農業部從 1990 年開始組織實施綠色證書制度試點工作,綠色證書是農民從事某項農業技術工作所必須具備的知識、技能及其他條件的資格證明。1994年開始在全國2 000個縣全面組織實施綠色證書工程,累計超過1 000多萬名農民參與。該項目是對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農業社會化服務人員、專業戶、科技示范戶等技術型農民進行的包括思想政治、職業道德、專業知識等崗位標準等內容的系統培訓,最終提供有效的資格證明。“綠色證書工程”的目標是通過培養千百萬農民技術骨干,全面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廣泛地推廣農業科技成果,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全面振興農村經濟的系統工程。1999年,農業部、財政部和團中央共同實施《青年農民科技培訓工程》,旨在為農業培養更多的青年農業勞動力,增加就業觀念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責任感,為農業專業化生產和產業化經營培養高素質的勞動者和帶頭人。
(二)第二階段(2000—2011年):新型農民培訓
進入新世紀以來,政府對于新型農民培訓的重視程度與投入力度加大,培訓種類也更加豐富。2003年,農業部、財政部實施《新型農民創業培植工程》,以升級經營模式為目的,著力提升新型農民的創業創新能力,培養一批規模化、產業化、專業化經營的農場主與農業企業家。2004年,農業部等6部門實施《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旨在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與就業能力,增強勞動力轉移能力。2005年,農業部實施《農業科技示范戶工程》,旨在提升農業科技能力,推廣農業新科技與新方法,提升部分領軍人物的示范水平和帶動能力。2006年,農業部、中國科協等19個部門實施《農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著力提高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就業能力,農村婦女與欠發達地區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2006年,農業部實施《百萬中專生計劃》,培養具有中專學歷的農業人才,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領軍人才隊伍建設,培養100萬名具有中專學歷的從事種植、養殖、加工等生產活動的人才,以及農村經營管理能人、能工巧匠、鄉村科技人員等實用型人才,使他們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帶頭人。
(三)第三階段(2012—2018年):新型職業農民培育
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更具長期性與宏觀戰略性,涵蓋了制度保障、政策支持,且需要政府與市場主體的多方參與,是實現農民從“兼業化”到“職業化”轉型的過程。[10]2012年8月,農業部印發《新型職業農民培育試點工作方案》,開始新型農民培訓向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轉變。首先,從國家層面通過土地流轉、生產補貼、保險金融等方面的政策傾斜,綜合提高新型職業農民的自我發展能力;其次,通過教育資源整合,大力開展農民職業培訓,將陽光培訓的基金與資源重點用于開展新型職業農民培訓,開展從種到收、從生產決策到產品營銷的全過程培訓,突出新型職業農民務農技能的全面提升;最后,要求各地方政府加大對新型職業農民的政策扶持力度,支持土地流轉、農業補貼、產業化項目建設等向新型職業農民傾斜,突破身份局限,解決職業農民轉型后顧之憂。
2014年,農業部、財政部共同實施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程,以培養造就具有科學文化素質、掌握現代農業生產技能、具備一定經營管理能力的新型職業農民隊伍為目標,科學解答“誰來種地”的問題。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是一項基礎性工程、創新性工作,重視突出新型職業農民成長的全過程,即教育培訓、認定管理和政策扶持,采取適應成人學習和農業生產規律的“分段式、重實訓、參與式”培育,將教育培訓過程、產業發展實際與培育對象的滿意度等作為衡量培育效果的綜合指標,同時與農技推廣信息化建設相結合,開發智慧農民云平臺,開通新型職業農民網絡課堂,實現在線教育培訓、移動互聯服務、在線技術信息咨詢、全程跟蹤管理與考核評價。《2017年全國新型職業農民發展報告》指出,2017年全國新型職業農民總量已突破1 500萬人,發展質量顯著提升。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作有效開展,“三位一體、三類協同、三級貫通”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制度基本建立,政府主導下的“一主多元”新型職業農民教育培訓體系得到鞏固,“一點兩線、全程分段、實訓服務”的培育模式全面推行。[11]
三、新時代“職業農民”培育發展趨勢展望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農民職業化特征顯著,“職業農民”發展成為現代農業的主力軍,參考《職業大典》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對職業農民的概念進行界定,賦予其勞動、報酬、發展、保障職業屬性。在準確定義職業農民概念后,對未來職業農民培育發展趨勢進行展望,認為其向著制度化、組織化,與小農戶和新型經營主體雙向耦合趨勢發展。
(一)“職業農民”概念與內涵
隨著農業內部的橫向分化和縱向發展,農民職業化性質逐步強化,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勞動者開始逐步恢復并體現出勞動、報酬、發展、保障四個職業化特征,成為不受地域和戶籍約束,以農業為職業的職業農民。
以往對職業農民的定義,除了以農業為職業,有的強調經營達到一定的規模,有的強調收入達到一定的水平,這些都偏離了職業的本質屬性。因此,職業農民的定義應回歸職業屬性,加入工作時間和年齡因素。考慮以下條件和因素:
第一,職業農民從事的必須是農業或農業相關聯的產業。
第二,職業農民可以是進行農業方面的生產,也可以作為管理者進行經營,還可以為農業或關聯產業提供服務。
第三,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和國家有關規定,不得招用16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因此職業農民的起始年齡為16周歲。考慮到職業農民將來要建立與其他職工相統一的退休制度,且目前農村居民領取養老金的年齡不分男女均為60周歲,因此作為職業農民年齡最高也不超過60周歲。
第四,考慮農業生產的特殊性,且有一定的農閑時間,按照國家規定扣除休息日和法定節假日,每年有250個工作日,再扣除職工帶薪休假天數(按10天計算)工作日為240天,同時考慮職業農民制度應涵蓋較多的農民,職業農民的條件不宜過高。綜合以上因素按50%計算工作時間,為120天。
第五,強調市場機制和規則來獲取收入,是為了排除從事農業生產主要用來滿足自給自足的勞動者。考慮不宜將職業農民的條件定得過高,收入來源于農業及關聯產業的比例應不少于50%。
結合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將職業農民定義為:在農業或農業關聯產業進行生產、經營或服務,年齡在16周歲至60周歲之間,每年工作時間不少于120天,利用市場機制和規則來獲取收入且主要來源于農業及相關聯產業(應占50%以上)的勞動者。
(二)“職業農民”培育發展趨勢展望
1.職業農民培育制度化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強化鄉村振興的人才保障,全面建立職業農民制度,完善配套政策體系。建立職業農民制度已經超越了原有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程的范疇,需要在深入研究、構建制度、創設政策、完善體系等多個方面進行系統研究和深入探索。職業農民制度是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補充與完善,是暢通城鄉間人才要素雙向流動的制度性安排,是一項指導性而非法規性制度設計。[12]未來“農民”是一種自由選擇的職業,制度是一種有效的保障,涵蓋職業農民發現、培養、發展全過程,貫穿職業農民培育始終,是系統性制度設計。充分體現國家重農強農惠農的政策導向,在明確職業屬性的基礎上,建立職業分類和認定體系,暢通職業能力提升渠道,完善創業就業支持政策,建立制度保障體系。未來將探索如何賦予職業農民與城鎮職工享受同等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待遇時如何給予一定的補貼,職業農民也有失業,如何建立失業救助及保險制度。
2.職業農民培育組織化
職業農民的組織化是以土地流轉、適度規模為前提的,且多是新型經營主體負責人。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顯示,截止到2016年末,在工商部門注冊的農民合作社總數達到179萬個,入社農戶近1億戶,農民組織化程度明顯提升。近年來新型職業農民組織在新型職業農民隊伍不斷壯大的同時逐漸發展起來,隨著現代農業的不斷發展,職業農民組織化程度加大,謀求、維護和改善其共同的經營活動,互相協作的發展目標逐漸趨同,組織功能由最初的成員之間信息交流轉變為同業合作、跨行業互補、抱團發展,提高了抗風險能力,更有利于推動農業要素的有效配置。[13]職業農民借助組織達到更高的層次、更大的平臺、更廣的范圍上的合作與聯合,實現與產業緊密的聯結度,既具穩定性又具靈活性。
3.職業農民與小農戶、新型經營主體雙向耦合發展
在鄉村振興戰略中,培育鄉村發展新動能,明確提出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要求。我國小農戶數量龐大且長期存在,但其并未很好地納入到現代農業發展軌道,處在農業發展的“邊緣地帶”,對實現農業現代化產生嚴重制約。職業農民是聯系小農戶與新型經營主體的重要紐帶,即職業農民通過新型經營主體與小農戶形成帶動扶持,從而形成三方“利益共同體”。[14]“利益共同體”奉行利益共享原則,在參與市場行為中,各方享受到應有的價值增值,實現利潤最大化,從而達到資源最優配置及市場良性運行。在未來大力培育職業農民的同時,會逐步建立起與小農戶、新型經營主體的雙向耦合發展機制,拓展小農戶轉變為職業農民或加入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渠道。新時代下職業農民培育新路徑是如何使職業農民、小農戶通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有效銜接現代農業。
【參考文獻】
[1]陳錫文.從農村改革四十年看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J].行政管理改革,2018(4):4—10.
[2]馮道軍,施遠濤.從新制度主義看中國農民身份的制度變遷:兼論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民問題[J].甘肅社會科學,2014(3):122—125.
[3]王守聰,趙幫宏,張亮,等.職業農民是如何成長的[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4.
[4]楊茹,宋國愷.從身份農民到職業農民[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10.
[5]吳鵬森.進城農民:中國社會特殊的身份集團[J].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2):6—13+152.
[6]錢文榮,朱嘉曄.農民工的發展與轉型:回顧、評述與前瞻:“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農民工的貢獻與發展學術研討會”綜述[J].中國農村經濟,2018(9):131—135.
[7]何強.對于傳統農民向新型農民轉變的思考[J].學習與探索,2007(4):134—136.
[8]呂莉敏.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政策變遷與趨勢:基于2012—2017年相關政策的分析[J].職教論壇,2017(16):26—31.
[9]朱啟臻,胡方萌.新型職業農民生成環境的幾個問題[J].中國農村經濟,2016(10):61—69.
[10]徐輝.新常態下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機理:一個理論分析框架[J].農業經濟問題,2016,37(8):9—15+110.
[11]農業農村部科技教育司,中央農業廣播電視學校.2017年全國新型職業農民發展報告[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8.
[12]范力軍.鄉村振興視角下農民職業化教育體系優化探討[J].安徽農學通報,2018,24(22):12—13+17.
[13]蔡榮,馬旺林,王舒娟.小農戶參與大市場的集體行動:合作社社員承諾及其影響因素[J].中國農村經濟,2015(4):44—58.
[14]洪仁彪,張忠明.農民職業化的國際經驗與啟示[J].農業經濟問題,2013,34(5):88—92+112.
The Changes and Prospects of the Cultivation of
Farmers Professionalization in China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FAN Meng-yao, ZHANG Liang
(School of Hebei Agriculture Un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as rural reform have been obvious to all, and solving the problem of farmers has always been the core of the reform work. Looking back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farmers professionalization in the past 40 years, it is roughly divided into new period, new century and new stage. The concept of peasants is developed from traditional peasants to new peasants and new professional peasants. The peasant professionalization is cultivated by peasant quality education, training for new farm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era, and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urge farmers to return to professional attributes. The futur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farmers will be oriented towards institutionalization, organization, and the bidirectional coupling of small farmers and new business entities.
【Key words】farmers; professional cultivation;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編輯/徐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