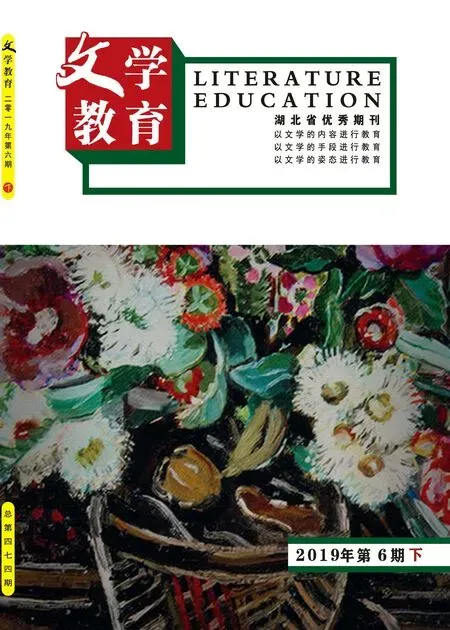《五卷書》框架結構在東西方民間文學中的發展
段孟潔
框架式結構,是一種文學敘事架構,多見于民間文學當中。其形成與口頭文學息息相關,擁有極大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框架式結構起源于印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古典梵語時期的《五卷書》,但這種結構并不是以《五卷書》為代表的印度民間文學所獨創的,追根溯源還是要回到印度文學當中,從吠陀文學時期的四大吠陀以及其相關的吠陀文獻,到史詩時期的印度兩大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諸多的文獻中都包含有許多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童話和寓言。《五卷書》正是對這一講故事的悠久傳統的繼承和發揚。”(薛克翹,76)隨著《五卷書》的對外譯介傳播,這種框架式結構對東西方民間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五卷書》的框架式結構及特點
《五卷書》的具體成書時間難考,按照金克木先生的說法,“現在印度有幾種傳本,最早的可能上溯到公元二、三世紀,最晚的梵語本是十二世紀編訂的。”初始也是以口頭文學的形式在民間傳播,后期逐漸形成了一些本子,西方學者根據文本的繁簡不同,劃分出“簡明本”、“修飾本”和“擴大本”等。(季羨林,2)目前國內現有的《五卷書》譯本是由季羨林先生根據“修飾本”從梵文譯出的,下文皆依據這一版本展開論述。
《五卷書》共分五卷,因此稱為《五卷書》。開頭有一個序言部分,講述了《五卷書》的緣起,也就是串起整本書的主干故事:印度的一個國王請婆羅門毗濕奴舍哩曼以故事的形式教導自己的三個兒子。所講的這些故事構成了《五卷書》,在主干故事下,書中的每一卷都另有一個核心故事,比如說第一卷《朋友的決裂》的核心故事講的就是豺狼離間了獅子和牛的友誼,導致了兩個朋友的決裂。除這一核心故事外,第一卷書還通過核心故事中不同角色之口講述了30個小故事,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五卷書》的這一結構特點可大致分為以下三層:
主干故事→核心故事→小故事
整體結構如同樹狀圖,主干故事與核心故事相連,但發散出來的小故事與小故事之間未必有必然關聯,因此季羨林先生以“大樹干”、“粗枝”和“細枝條”的關系來形象地描繪這種框架式結構的特點。這種框架式敘事結構的特點在于其包容性強,可能性多,內容豐富。
二.《五卷書》的框架式結構對東方民間文學的影響
劉守華先生曾提到過,《五卷書》“對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童話和寓言的發展,有著廣泛深刻的影響。”這里的影響指的是故事內容情節相似,關于印度故事母題這一方面,國內外學者多有考證。在《五卷書》的世界流傳方面,德國印度學家,流傳學派的建立者本菲有著深入的研究。故事內容的借鑒與傳承方面已有定論,那么在作品敘事結構方面《五卷書》又有怎樣的影響,這是以下兩節準備討論的核心。《五卷書》在東方的影響分為三大部分,一是印度本土,二是西亞和中亞,三是中國。
首先說印度本土,與《五卷書》相關的故事文集有《佛本生經》、《益世嘉言集》、《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則》、《寶座故事三十二則》和《鸚鵡故事七十則》等,這些故事文集在故事內容和結構上都明顯受到了《五卷書》的影響。其中《佛本生經》通過佛教的傳播對中國文學也產生了極大影響,目前《佛本生經》和《五卷書》的成書先后仍沒有定論,薛克翹先生認為“從時間的先后和故事的數量看,《五卷書》顯然要比《本生經》晚出和遜色。”而趙國華先生則指出,《佛本生經》“是在佛滅后的華氏城(今巴特拿)結集時代,約公元前三世紀中葉,用接近梵文的巴利文編訂成集的。”而正如前文提到的,《五卷書》的幾個傳本“最早的可能上溯到公元二、三世紀”(金克木,215)無論時間先后如何,兩者在故事組織結構上有相通之處,即都有一個主線故事貫穿全文,將類型豐富的故事串聯在一起。
次說西亞和中亞,在這一地區地區產生影響最大的故事文本是《卡里來和笛木乃》,這一文本的形成經歷了由梵語到巴列維語,再從巴列維語轉譯至古敘利亞文,再到“公元七五○年,伊本·穆格法的《卡里來和笛木乃》阿拉伯語譯本問世,后者主要依從巴列維文和古敘利亞文本《五卷書》。”(宗笑飛,76)但相較于《五卷書》的主干故事:婆羅門講故事教育三個王子。《卡里來和笛木乃》的主干故事在翻譯過程中得到了擴充,但主干故事的核心仍是“某人講故事”,即印度哲學家白德巴講故事規勸專橫跋扈的國王德卜舍利姆。受這些譯自《五卷書》的故事集的影響,在西亞和中亞地區產生了《一千個故事》、《一百零一夜》和《一千零一夜》等。以《一千零一夜》的敘事模式為例,首先都有一個“某人講故事”的主干故事,《一千零一夜》的主干故事是:薩桑王國暴虐成性,日殺一女,宰相女兒莎赫扎德為拯救無辜少女,主動入宮為國王講故事。其次,故事內容十分豐富,包容萬象,故事數量逐步增大,嵌套技術越發成熟。最后,故事集中都含有大量的“隱含作者”(徐嫻,97),即敘事視角豐富多樣。
最后是中國,印度故事傳入中國,主要是經由佛教東傳,但經劉守華先生的搜集與比較,發現《五卷經》中“情節結構相類似,可以初步斷定源于印度的中國民間故事有二十三例”(劉守華,63)由此可見《五卷書》對中國民間文學的影響深遠,但在敘事架構上是否產生了直接影響,這一點仍需要考證,季羨林先生在《五卷經》序言中提出,“《五卷書》的結構也與中國一些故事有關聯,如隋唐間王度的《古鏡記》就是采取了‘連串插入式’的寫法。”所謂的“連串插入式”就是框架式結構的一種形象的說法。《古鏡記》的敘事特點在于,文本從第一人稱視角講述了王度如何獲贈古鏡之后,開始講述古鏡的流傳和奇聞異事,在這一過程中,“王度的講述是主線,主線中穿插其他人的講述,其他人講述中又穿插進一些人的講述。”(劉俐俐,112)可見《古鏡記》包含了眾多聯系不緊密的故事,但采用了以古鏡為敘事核心,多視角敘述的方法組織作品敘事結構,與《五卷書》的結構有異曲同工之妙。
三.《五卷書》的框架式結構對西方民間文學的影響
印度學者D.P.辛加爾曾在《印度與世界文明》一書中指出,印度的《五卷書》對西方寓言故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但它無疑是以《卡里來和笛木乃》為媒介的。(轉引自宗笑飛,77)另一種說法認為,在十字軍東征時期傳入歐洲的阿拉伯民間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才是對西方民間文學產生巨大影響的源頭。無論是哪種說法,都可佐證《五卷書》外傳對西方民間文學的影響。
首先,在內容上直接或間接受到《五卷書》影響的作品有伊索的《伊索寓言》、胡安·馬努埃爾的《盧卡諾爾伯爵》、薄伽丘的《十日談》、斯特拉帕羅拉的《滑稽之夜》、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拉·封丹的《寓言》等等。其中,據學者考證,寫于1335年的卡斯蒂利亞語小說《盧卡諾爾伯爵》“對《卡里來和笛木乃》的借鑒與模仿是十分明顯的”(宗笑飛,81),當時《卡里來和笛木乃》的卡斯蒂利亞語譯本(1251)已經問世了半個世紀,影響十分廣泛。“《盧卡諾爾伯爵》是由謀士帕特羅尼奧講述的五十一個故事。”可以看出,其主干故事也有“某人講故事”這一核心,符合框架式結構特點,并且“至少有四個故事”移植自《卡里來和笛木乃》。(宗笑飛,77)
其后,將框架式結構進一步發展的是意大利文學巨匠薄伽丘的《十日談》,這部作品比堂胡安·馬努埃爾的《盧卡諾爾伯爵》晚十多年,包含一百個故事,這些故事串聯在一個大的主干故事下,即十位青年男女在別墅躲避瘟疫時分別講述的故事。但薄伽丘對框架式結構的開拓性發展是在故事敘述外又加上了一層結構,即薄伽丘自詡作為觀察記錄者對《十日談》創作動機和經歷的一些敘述,學者稱之為“附表層結構”。(劉清玲,112)《十日談》的敘事模式對十四世紀英國詩人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產生了直接影響,這一部詩體短篇小說集講的是來自不同階級的朝圣者們在往返圣地途中應店主提議開始的講故事比賽。
總之,框架式結構經歷了一個東學西漸,逐步發展的過程,從吠陀時期到史詩時期的發展與積淀,到以《五卷書》為代表的印度民間文學采用框架式結構將形形色色的故事串聯在一起,外傳后經過改編和擴充,《卡里來和笛木乃》、《一千零一夜》等作品“整個主線故事由古樸簡單變得豐腴飽滿、扣人心弦”(穆宏燕,142),流傳到西方后這種開放式的結構與西方“整飭分明”(林文琛,43)的文學特點相結合,敘事結構變得規整的同時仍然具有很大的開放性,框架式結構由東方發源,在西方得到了發展,日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