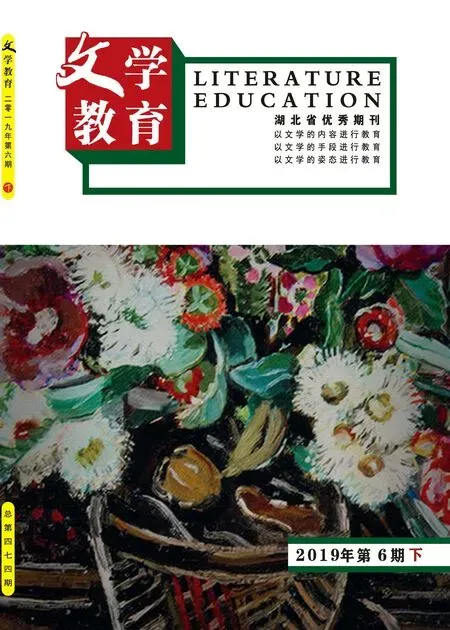阿契貝書寫真實的非洲文明
李金霞
一.弗朗茲·法農在《地球上不幸的人們》中提出,非洲被視為“野蠻,墮落和獸性”的家園。康拉德認為非洲是“黑暗的中心”。非洲人被描畫成生活在愚昧落后狀態中的野蠻人,沒有靈魂、沒有宗教、沒有文化、沒有歷史。而被譽為“現代非洲小說之父”的尼日尼亞作家欽努阿·阿契貝(Chinua Achebe)旨在通過創作小說來向全世界言說:非洲人不是第一次從歐洲人那里聽到文化的,相反,非洲自身擁有悠久而豐富的文化。阿契貝基于對康納德和卡里等歐洲作家所刻畫的非洲形象的不認同,旨在向世界再現真實的非洲文明。本文通過文本細讀,試圖梳理作家阿契貝是如何書寫豐富多彩的非洲文化的。
國內許多學者對阿欽努阿·契貝的創作作了諸多富有意義的解讀。王越認為,《瓦解》對康拉德的《黑暗的心》等歐洲小說中把非洲描寫成野蠻原始的、沒有文化的非洲進行逆寫,反映了物質非洲與精神非洲的原貌,傳達出一種未被充分表述的非洲的聲音。高文慧通過分析阿契貝公開發表的評論文章、訪談以及文學作品來探析其創作意圖:從內部向世界呈現非洲文化,建構真實的非洲形象,成為阿契貝最重要的創作目標,矛頭明顯指向歐洲的文化霸權意識。陳榕(2008)認為,《瓦解》體現了阿契貝重構非洲文化傳統的努力。段靜認為,阿契貝是非洲文學中對“口述性”極具代表性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他借助口述性將這種本土的經驗與哲思在文學寫作中進行了傳達。這些研究強調了阿契貝為重構非洲文化所作出的努力,為本文闡釋伊博族文化增加了信心。
非洲以口頭文學著稱。在《瓦解》中,作者阿契貝將伊博族獨具特色的文化傳統書寫下來,為讀者提供了了解非洲文化的窗口。伊博族人善于講故事,常將道理蘊含在故事中。非洲豐富的諺語正是從悠久、發達的口頭敘述中積淀下來的。此外,獨特的婚、喪習俗也充分代表了非洲傳統文化。下面我從非洲諺語和故事、非洲婚喪嫁娶等民俗文化等兩個方面進行闡述。
二.諺語是民眾的豐富智慧和普遍經驗的規律性總結,多以通俗易懂的短句或韻語等口語形式呈現。阿契貝恰當地將非洲諺語運用到伊博族人的談話中,反映了伊博族悠久的文化積淀。也使得道理通俗易懂,表達上更具說服力。
小說《瓦解》中諺語俯拾皆是,長者在集會上向大家講話時常引用諺語,老人教育后輩時也常用,而且在刻畫悲劇英雄奧貢喀沃時也多以諺語呈現。奧貢喀沃白手起家,向氏族中富有的恩瓦基比借他的第一批木薯種子時,恩瓦基比談及一位男子向神禱告時,神說他死去的父親讓他供奉一只山羊,而這位男子反問父親可曾有過一只家禽,大伙兒都大笑起來,唯有奧貢喀沃笑得很勉強,“在格言里提到枯骨的時候,老婦人是要感到不舒服的”。因為這間接映射了奧貢喀沃的父親,觸及了奧貢喀沃的傷痛。好在族人衡量一個人的價值的標準是依據他自身的價值而不是其父親的價值,奧貢喀沃方才以頑強的拼搏精神在青年時期便成成長為一名氏族領袖,從而贏得了族人的敬重,正可謂,“一個孩子只要把手洗干凈,他就可以同皇帝一道吃飯”。然而,正如另一則諺語所云,“看看皇帝的嘴巴吧,你還以為他從來沒有吃過媽媽的奶呢。”奧貢喀沃性格剛強,家業雄厚,他變得有些驕傲自大、粗暴無禮。當他在一次親屬大會上蠻橫侮辱一個沒得過任何頭銜的男人為女人時,會議上最年長的人說,“有些人的棕櫚仁是由慈悲的神靈為他們打開的,他們不應該忘記謙恭”,以此來提醒奧貢喀沃不該得意忘形。而當奧貢喀沃在埃賽烏杜的葬禮上由于槍走火致人死亡冒犯了地母,因此必須加以懲罰,否則,神的憤怒不僅會降臨到犯罪者本人,還會降臨到全境。正如長者所言,“一個指頭沾了油,就會弄臟其他的指頭”。
伊博人喜歡講故事,故事象征著智慧,承載著伊博民族的記憶。恩沃依埃的母親講到的蒼鷹向天求雨的故事酷似民間傳說,反映了非洲特定的社會歷史文化。于彬認為蒼鷹祈雨的故事,“不僅情節有趣,還反映了非洲大陸熱帶草原性氣候特點和人們生火供奉動物內臟的祭祀習俗。”而氏族長者烏成杜講的故事,印證了白人入侵、屠殺、征服非洲原始氏族部落的歷程。
千萬不要殺默不作聲的人……又一次母鷹派它的女兒出去找吃的東西。它帶回了一只小鴨。“你做得很好,”母鷹對女兒說,“但是,告訴我,你飛下來搶走小鴨的時候,小鴨的媽媽說了什么沒有?”“什么也沒說,”幼鷹回答說,“它走開了。”“你必須把小鴨送回去,”母鷹說。“沉默是不祥之兆。……
這個故事正揭示了白人消滅阿巴姆氏族的過程:一個白人來到阿巴姆,神說這個白人會帶來災難,會毀滅他們的氏族。于是族人在尚未弄清白人意圖的情況下便果斷殺死白人,接著是白人的沉默,但沉默之后便是白人對氏族的血腥屠殺。
三.結婚和死亡是人類必然要經歷的過程,因此結婚和死亡成了人生中的重要儀式。《瓦解》詳盡記述了非洲傳統文化中的婚俗和喪俗文化。這是作家阿契貝逆寫帝國的重要策略。
阿契貝濃墨重彩地描述了伊博族婚俗。求婚者伊比帶著棕櫚酒,在長輩的陪同下到奧比埃里卡家向阿庫埃基求婚。阿庫埃基穿著盛裝羞澀地同她的求婚者和親戚們一一握手。男人們吃著柯拉果,喝棕櫚酒,用短掃帚把商量新娘的身價。到了迎娶的日子,求婚者仍然帶著棕櫚酒來,請新娘的父母、近親和所有鄉親喝。結婚的日子成了烏姆恩納全村喜慶的日子,頗具儀式感。阿契貝向讀者展現了烏姆恩納全村人齊動員忙忙碌碌做飯的場景。按照禮節,親家送來的棕櫚酒先送給幫忙做飯的婦女們喝,再送給新娘以及裝扮新娘的女伴們。這一場景反映了非洲氏族尊重女性的一面。男人們則坐成半圓形,一邊聊天一邊等待求婚者。求婚者一行人陸續送來酒,也圍坐成半圓形,同主人們合成一個圓圈。新娘的母親帶著新娘和六七個女伴順著圓圈和所有人一一握手,之后退出去。緊接著,男人們剖開柯拉果,相互祝福,一起吃柯拉果。然后三五成群地圍坐在一起喝酒。黃昏時候,大家共吃晚飯。夜幕降臨,人們點起篝火,長者圍成一個大圓圈,青年們繞著圓圈走,對每個人唱贊歌。伴隨著姑娘們的舞步,新娘手提公雞出來,把公雞獻給樂師后便開始跳舞,“銅腳鐲咣啷咣啷地響,染了紅木粉的身子在淡黃的光線中閃閃發光。樂師們奏著木頭、泥土和金屬做到樂器,唱了一首又一首的歌”。人人興高采烈,歡天喜地。一直玩到深夜,客人們才帶著新娘,邊走邊唱回家去。小說還記述了新娘嫁到夫家時,對著滴了母雞獻血的祖宗手杖發誓自己忠于丈夫的傳統。高宏存認為,“從宗教方面來看,伊博人的婚姻禮俗文化中,透露出原始宗教的痕跡,例如母性崇拜、生殖崇拜、性崇拜等。可以說,小說里所展現的伊博族婚俗,實際上是千年來非洲文明的一個縮影。”伊博族獨特的婚慶習俗,反映了非洲注重禮節、井然有序的傳統文化。
阿契貝對伊博族喪葬儀式的詳盡敘述,給予世界讀者了解非洲獨特的喪葬習俗的窗口。首先是埃桂向氏族說話,報告埃賽烏杜去世的消息。接著,所有族人都來參加埃賽烏杜這個偉大人物的葬禮。鼓聲隆隆,槍聲、炮聲不斷,“男人們發瘋地到處亂沖,見樹砍樹,見牲口殺牲口,跳上墻頭,爬到屋頂上跳舞”。祖宗靈魂身披拉菲亞樹葉,從地下出來,有的會傷害人,有的則為死者賜福,祈求死者來世富有、長壽、充滿勇氣。祖先的靈魂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
活人的鄉土和祖先的國土相去并不遠。彼此之間原有來往,尤其在節日,或是老人去世的時候,因為老人是最接近祖先的。一個人的一生,從出生到死,要經過一連串過渡的儀式,這些儀式使他和他的祖先愈來愈近。”
阿契貝對伊博族葬禮儀式的描寫,映射了非洲敬重死者,祭奠祖先的文化傳統。
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把非洲描繪成“回到創世之初”。在姚峰看來,這“無異于說白人文明已經處于人類文明相當先進的階段,而非洲大陸的黑人則仍處于史前文明的狀態”。因此,阿契貝以非洲氏族生活為寫作源泉,用英語創作小說這一西方文體,來反映非洲文化特質,旨在向全世界還原一個真正的非洲。
當然非洲氏族內部也存在著諸多矛盾。烏姆奧菲亞的社會是典型的男權社會,實行一夫多妻制。只要有錢,男人可以隨意娶親;妻子只是丈夫的附屬品,沒有主體性。另外阿契貝也揭示了非洲相對原始和殘忍的習俗,如剖開死嬰的肚子、將雙生子和身患浮腫病的人看作是對地母的不敬而被扔進“兇森林”等。正如高文慧所說的那樣,“非洲傳統文化的分崩離析首先來自內部的精神危機,外來文化的影響只不過是一個催化劑而已。”可見,阿契貝正視了非洲原始文化的不足,并將其客觀書寫下來供世人評價。因此,他非但不會這陷于“二元對立的狹隘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藩籬之中,反倒成就了其“非洲文學之父”的功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