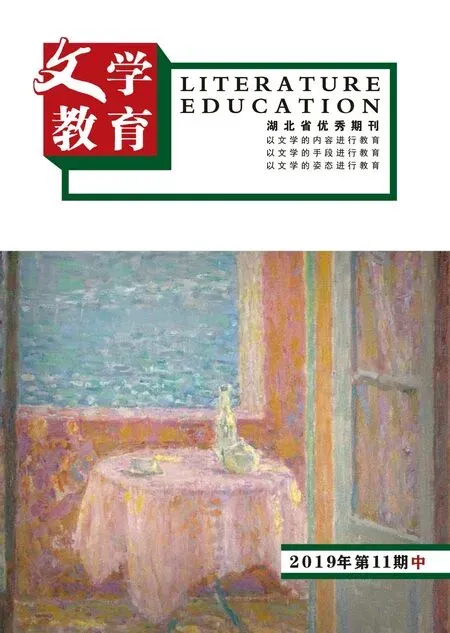詩歌《補墻》中的圖征及其意義
祁皓南
羅伯特·弗羅斯特不僅是美國20 世紀最重要的詩人之一,也是最受讀者歡迎的自然詩人,其詩歌廣為傳頌。他曾四次獲得普利策獎,并應邀在肯尼迪總統的就職典禮上宣讀自己的詩歌。究其原因有三:一是他詩歌中借以抒懷的多是一些日常所見、平凡而輕松的事物;二是雖然他生活在一個各種文學思潮流派風起云涌的時代,但他不隨波逐流,語言多用白描手法,追求質樸自然;三是在他質過于文的詩歌之后,往往蘊含著深刻的哲理。“以快樂開始,以智慧結束”(Greenberg,1961:37)于平凡之處見偉大是對他詩歌最好的總結。
《補墻》(Mending Wall) 是弗羅斯特1914年發表的詩集《波士頓以北》(North of Boston)中的一首敘事短詩,在純凈簡練的語言背后其蘊含的哲理值得讀者反復思考。詩歌徐徐推進,以敘事者“我”之口吻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我”是一個生活在鄉村的普通的勞動者,“我”的田野里種著蘋果,而一堵石墻之外山那邊的鄰居家種著松樹。春天來了,按照慣例,“我”叫著鄰居對共同的石墻進行一年一度的修補工作。在此期間,“我”開始反思補墻的必要并想就此和鄰居討論。然而最終,故事以鄰居固守父輩沿襲下來的傳統“好籬笆造就好鄰家”告終。
弗羅斯特始終拒接歸入任何流派,他不喜歡附庸理論創作詩歌,正如他本人曾經表示過,“我們有理由懷疑任何按照某種理論來寫的詩可以長久。我反對所有的主義,他們只是某些觀點的流行 和 失 寵。”(Barry,1963:121,212) 他反對評論家將自己歸入象征派詩人,他認為“象征主義非常可能妨礙或者扼殺一首詩歌,它可以看作跟血栓一樣壞,”但同時他宣稱自己是一個“圖征主義者”(區鉷,羅斌,2009:90),“如果我的詩歌一定要有一個名字的話,我寧愿叫它們圖征(Emblemism),我追求的是‘事物看得見的圖征’。”(Barry,1963:376)
在本文中,筆者選擇了《補墻》這首充滿哲理意味的敘事小詩,結合“圖征”理論,試圖找到圖征性在《補墻》中的表達,并闡釋詩歌如何借圖征傳達了其深刻的主題意義。文章將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1) 對“圖征”的界定;2)《補墻》中圖征的反映;3) 補墻》中的圖征對主題的闡釋。通過文本分析,筆者認為:弗羅斯特選擇運用更加直觀生動的圖征,不僅在詩歌中營造了一幅幅動靜結合的畫面,加深讀者對詩歌的理解;還通過讖語有意識的進行說教,拉近與讀者之間的距離,更直觀形象地揭示詩歌的主題及其普世意義。
一.圖征
從詞源上講,圖征 (emblem)一詞來源于拉丁文emblēma,其本意是鑲嵌或內嵌符號。現代意義上的圖征來自于1531年意大利律師兼人道主義者安德魯· 阿斯埃托的著作《圖征書》,其主要指“象征圖片的合集,通常伴有讖語、韻文或散文,從中世紀的寓言書而來。”(區鉷,羅斌,2009:91)1605 年,英國學者弗朗西斯·科特斯指出“圖征把知識分子的想象降低成可以感知的意向”(區鉷,羅斌,2009:91) 。既然如此,圖征包括直觀的圖片和具有說教意義或哲理意義的文字,那么二者結合,也就包括深層意義上的情感表達和思維傳遞。
弗羅斯特稱自己的詩歌是“看得見的圖征”,在詩歌的文本呈現中雖然沒有實實在在的圖畫,但詩人用自己的文字創造了一幅幅圖畫,或者說,他的詩歌容易讓讀者在腦海中形成比較直觀生動的畫面,由此“圖征的精髓并沒有失去”。“弗羅斯特所說的圖征是作為修辭手法的圖征,而不是作為體裁的圖征”(區鉷,羅斌,2009:93) 圖畫的運用以及讖語的呈現是詩人運用的修辭手法,借以更直觀更深刻地表達詩歌的主題,又能拉近與讀者之間的距離,真正發揮出文學應有的教育意義。
二.《補墻》中圖征的運用
詩歌平鋪直敘的開始講述故事。在詩歌的開頭部分,一堵破敗不堪、亟需修補的石墻映入眼簾,“有一樣東西它不喜歡墻/ 凍脹了墻下的基礎土壤,墻上石塊跌落在兩旁/ 墻體開裂,雙人并肩而過像穿堂”。詩人首先呈現出的畫面中有兩個平行的意向,詩歌中的敘述者和一堵傷痕累累的石墻。需要說明的是,“弗羅斯特在詩中所呈現的‘看得見’的圖畫中多是通過一個敘述者的眼睛看到的”(區鉷,羅斌,2009:94)。我們仿佛看到,春天到了,又到了一年一度修補石墻的時候,敘述者站立在墻的一邊注視著石墻,并思索著石墻破敗的原因,這樣“東西”到底是什么呢?
沿著這個思路往下讀,“獵人的行為則是另一番景象/ 我要緊隨其后修補不停的忙/ 他們拆掉石塊卻不放回原位上/ 而是把兔子趕出讓它們難躲藏/ 惹得獵狗叫汪汪”。圖畫中的敘述者腦海里開始回憶,并呈現出另一幅畫面,那就是平日里打獵者經過石墻時毫不吝惜的行為對石墻造成了破壞。這種畫中畫的呈現方式別出心裁,“弗羅斯特呈現的是一個心事重重的人的內心世界”(區鉷,羅斌,2009:94)。接著詩人繼續描寫這堵石墻,石墻的畫面也更加豐滿起來。“我所說的裂縫/ 沒有誰見過其開裂聽過其聲響/ 但到春天來修補,眼前已是百孔千瘡”。敘述者站在石墻旁邊,看到了墻上的裂縫,回憶起獵人們的行徑,并開始思考裂縫形成的原因,這一幀幀圖畫都在詩人簡單直白的敘述中生動地呈現了出來。
既然如此,敘述者于是“通知了山那邊的鄰居街坊/ 約好了一天沿著墻巡查一趟/ 重新壘起我們之間的這堵墻”。畫面由靜態切成了動態,敘述者離開這堵石墻,越過山和田野去通知鄰居一起修補石墻。隨后,鄰居如約而至,“我們沿著墻各自走在各一方/ 將各自一側的石塊收拾妥當/ 有些石塊成塊狀,有些近乎于球狀/ 我們不得不口念咒語確保其穩當/‘請呆在那兒不要晃,等我們折回來查訪!’/ 我們搬弄石塊,手指被磨得粗糙無光”。我們仿佛看到了這幅畫面:兩個農夫頭對頭,時而彎腰撿石頭時而直起身將石頭重新堆砌,他們的中間被這堵石墻隔開,石頭時不時掉落令他們白費功夫,他們或是嘆氣般或是咒罵般將石頭重新放好,仿佛一種“戶外游戲/ 玩家各站各一方”。
隨后,畫面切到遠處,“那邊種松木這邊種蘋果樹隔墻相望”,我們便得知敘述者家種的和鄰居家種的完全不一樣,既然如此,為什么還要在這之前修建石墻呢?原詩中,這一疑問也被敘述者提出,“這讓我若有所想/ 我們在這里并不需要修建這堵墻/ 我的蘋果樹永遠不會越過這一屏障/ 跑到他松樹下去把松果嘗,我對他講”。畫面逐漸由遠及近,又聚焦在兩個農夫身上,對話的加入使之更加直觀活潑,“我”不斷思索著補墻的意義所在并試圖與鄰居理論,但鄰居似乎不以為然地繼續補墻,“我見他用雙手將石塊上端牢牢抓住不放/ 就像石器時代武裝的野蠻人一樣”。最終畫面定格在這里,敘述者仿佛放下手里的工作,站著思考,而鄰居仍然繼續工作,并以一句“好籬笆會促成好街坊”搪塞他。
三.《補墻》中的圖征對主題的闡釋
《補墻》中展現的畫面是敘述者“我”眼中的畫面,詩人試圖以“我”的視角來闡發深刻的內涵。這個畫面看似簡單祥和,實則蘊含著深刻的人生哲理。弗羅斯特的詩歌在樸素的風格之下,常常閃耀著智慧的光芒,蘊含著生活的哲理。“讀他的詩,往往在一兩句輕描淡寫的詩句里就有笑意在蕩漾,而笑意還未收斂,筆頭輕輕一轉,就帶出一個閃耀著智慧光芒的命題”(方平,1983:25)。詩歌一開始就給我們提出問題,“有一種東西它不喜歡墻”,這種不喜歡墻的東西是什么?筆者認為,它可能是1)大自然。“這種不喜歡墻存在的東西很顯然就是大自然”(劉永杰,2011:48),“凍脹了基礎土壤”,“太陽一曬”,溫度和光照是大自然的代表。這是因為人類修建墻破壞了自然本來的面貌,將土地劃分區域,破壞了有機統一整體性;也有可能是2)詩人自己,這個我們可以從后文得知,詩人不喜歡這種人與人之間隔閡的感覺;究其背后深層原因,還有可能是3)自然規律在作祟,沒有什么東西是永恒存在的,萬物都在不斷地運動變化消亡的過程中,墻也是這樣。
石墻及墻上的裂縫在具有畫面感的同時還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這種傷痕無聲無息但就在那里。“許多批評家認為這首詩是諷刺人與人之間有形或無形的隔閡的”(程愛民,1994:67),筆者認為這種說法不無道理。弗羅斯特本人曾于1957年作為“友好使者”訪問蘇聯,當時正值美蘇兩大陣營“冷戰”,整個世界似乎被一堵無形的墻切割成兩個獨立的存在。在這期間弗羅斯特在一次會議上朗誦了這首詩,這很契合當時的時代背景,也印證了這首詩一個重要的主題就是人與人、人與社會等等之間看得見或看不見的隔閡。
“敘述者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作用,即圖征中讖語的承載者,讖語起到了闡釋圖畫和加深理解的作用”(區鉷,羅斌,2009:94)。借敘述者之口,詩人說明了詩歌的一大主題,“盡管該詩講的是‘修墻’,實則隱含‘拆墻’之意”(程愛民,2007:81)。《補墻》的文本呈現別具匠心,圖畫的第一幀和最后一幀的安排很好的說明了詩歌的主題:
(1)Something there is that doesn’t love a wall.(有一樣東西它不喜歡墻)
(2)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好籬笆會促成好街坊)
就像一幅對比強烈的立體派圖畫,詩歌的開頭和結尾反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對立態度。全詩共有45行,位于中央的詩的第23行表現出了這一主題:“There where it is we do not need the wall (我們在這里并不需要修建這堵墻)”。“我們認為這種絕妙的安排不可能是無意或者巧合,而是一種匠心獨運”(程愛民,2001:81)。筆者認為第23行恰恰是本詩中的讖語,它既是敘述者的發問,也是敘述者智慧的展現。
此外,圖畫中動態的對話也值得我們一再思考。雖然達成了補墻的共識,敘述者卻一直在思考補墻的意義和目的。“以前修建這堵墻,我就該好好想一想/ 我要把什么東西來設防/ 我是否有冒犯誰的地方”,我們仿佛看到敘述者悲傷地站在墻邊,憂郁地思索著石墻將他與鄰居隔開,交流甚少,他在考慮是否自己曾經的所作所為觸犯了他。他試圖嘗試勸鄰居放棄補墻,可是鄰居“似乎已墜入黑暗感到迷茫/ 他不去琢磨父輩曾如何對他講/ 倒是認為父輩所說的話非常棒”,“鄰居的信念與墻的實際用途毫不相干,只不過因襲了傳統的信念”(周桂君,劉建軍,2007,288),這里敘述者的懷疑精神與鄰居的守舊傳統形成了二元對立,也凸顯了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之間的激烈碰撞,使得詩歌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普世意義。
四.小結
羅伯特·弗羅斯特是一位具有現代意識和具有強烈批判意識的詩人,一位關注人類存在、深愛著人類的詩人,他在通過詩歌對人類進行心靈上的叩問。他的詩歌雖然常常以新英格蘭為背景,但卻以區域性反映了普遍性,以鄉土氣息表現普遍的社會現象。正如埃默里·埃利奧特 (Emory Elliot) 在《美國哥倫比亞文學史》一書中指出的:“如果僅僅認為弗羅斯特的詩只是提供了簡單的日常生活哲理及美國式的智慧,那就是再愚蠢不過了;同樣,如果覺得他的詩易讀而覺得淺顯,也是個錯誤。即便是那些著意描寫普通鄉村風景的詩……也可能極為深奧、復雜。”(Elliot,1988: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