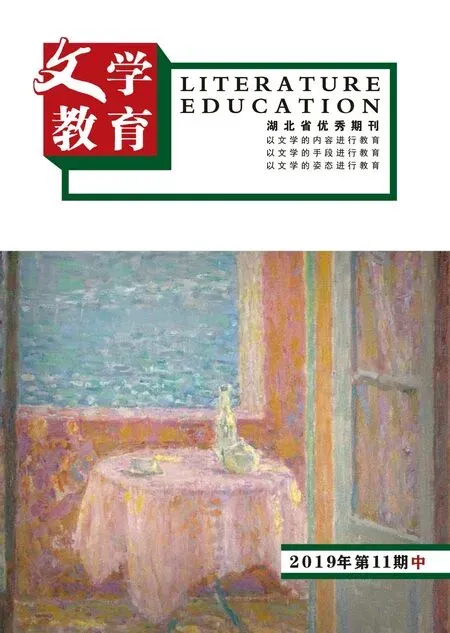小食光
陳紫青
此刻,父母送我的新年禮物陳列在桌上。我遙望著,盼望著,期望著,又是一年春節,一個我最喜愛的節日就那樣沿著時間的恒河,笑容恬靜,一步一步,如約而至。
最愛的是什么?是春節蘊藏的年味,是洋溢著年味的美食,是承載于美食背后,那一段段回不去的小時光。
小時候,每次過年前,姥姥都要忙前忙后。當我尚沉醉夢鄉時,她已忙著起早床,邁著健朗的步伐,手提一個大布袋,急匆匆的趕去了菜市場,只為了搶在別人挑走前,買一條大小適宜的草魚,一塊精瘦恰當的豬肉,帶回家為我們做炸草魚和秘制餛飩。
炸草魚的香氣最是特別。往往買回食材的當天下午,姥姥便開始著手炸魚了。那誘人的香氣撲鼻而來,經過我們家門的行人無不感嘆一句:誰家的炸魚這么饞人?而那時的我準會在聞到魚香的第一時間,立馬拋下電視里我最愛看的動畫片,守在姥姥身旁,癡迷的見證炸魚過程的誕生。
于年幼的我而言,剎那間,姥姥那布滿褶皺的雙手,那專注而又溫柔的眼神,那稀疏卻整齊的銀絲,那嘴角輕輕上揚的微笑,所有的一切,都變得模糊。站在廚房里的那個老人,不僅僅是我的姥姥,她在我的眼中,儼然已經是一位藝術家。狹小的廚房是干凈明亮的畫室,灶臺上的作料是她的顏料,手里不斷升溫的鐵鍋是她的畫布,陽光悄悄打在她有條不紊的身上,微風正好吻過她臉頰,時間突然變得好慢,好慢,仿佛一瞬即永恒。最終,姥姥朝我綻放出比陽光還要溫暖的笑容——偉大的藝術品就此誕生。
如果說第一天姥姥是繪出一副狂放盎然的野獸派畫作,那么第二天早上包餛飩,便是在演奏行云流水般的古典舞了。
作為我們家春節的主食,餛飩自是必不可少。與別人家現煮的冰凍餛飩不同,我們吃的餛飩都是姥姥親力親為制作出來的。
將長茶幾規矩的擺在客廳正中央,移開上面的閑雜物品,鋪上干凈的桌布,放上有剁碎拌好的豬瘦肉和面團的盆子,跟著一根搟面棍,一個裝餛飩的蒸鍋,準備工作便一切就緒。
只見洗干凈手的姥姥,沉穩的坐在沙發上,先麻利的抓起一小塊面團,快速用搟面棍磨勻稱,接著夾起豬肉輕輕放入,用獨特的手法包起大小適宜的面皮,不過幾個眨眼間,一個看相完美的餛飩就展現在我的眼前。
看姥姥包餛飩是種享受。也許是穿堂風太過溫柔,又或許是時光太慢太慢,仿佛一瞬即永恒。她蒼老卻靈活修長的手指如同人間四月芳菲間撲扇的蝴蝶,每一次的飛舞,都帶來了生機蓬勃,每一每一次的飛舞,都盛開出最美的姿態。
在旁人看來,或許餛飩、炸草魚比起博大精深的中國春節美食文化不值一提。但對我而言,它們不僅僅是普通的美食,它們在舌尖彌漫開的味道,是家的味道,是姥姥的愛,是我回不去的小時光。
又是一年春節,也是第一個沒有姥姥陪伴的春節。我不再回憶過去,笑著打開桌上的新年禮物,看到的瞬間我愣住了:那是一張本一直存在電腦里,過去與姥姥的春節合照,背景正是姥姥做的一桌子美食。
時間突然凝固,仿佛一瞬即永恒。我知道,那是我的小食光,是我回不去的,小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