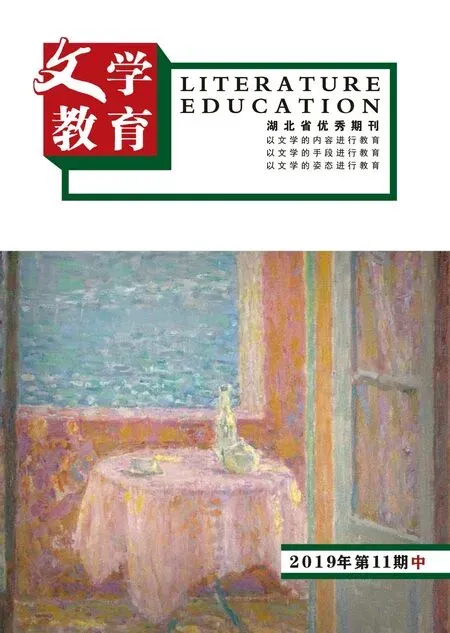《莊子》“真人之息以踵”詞條新詮
徐小曼
一
《大宗師》是《莊子》內篇里的一篇,第一部分反映莊子對于真人的理解。但是對于“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的翻譯理解一直眾說紛紜。主要分為兩類觀點。
第一類觀點認為莊子是實指一種科學呼吸方法,類似“踵息法”以修煉氣功,用足跟發力以調運呼吸。王世舜在《莊子譯注》里曰:“真人的呼吸是從腳后跟開始的。”陸欽《莊子通義》云:“真人呼吸從腳跟用力。”[1]張文江《〈大宗師〉析義》:“蓋全身筋脈易通,其息可達極深處。”[2]劉武曰:“其息深深,則下聚于丹田,因而通于足下涌泉穴。”明代尹真人、南懷瑾、陳廣忠[3]似乎也較為贊同。筆者認為這種自踵而上的呼吸方法理解還需商榷,踵息法是后來道教到晉代以降才逐漸提出的方法。《行氣玉佩銘》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氣功理論文物資料,據考為戰國后期的作品,氣功界人士將郭沫若在《奴隸制時代》的解釋發展為小周天調息理論。雖然,后代學者根據《呂氏春秋》等著作的只言片語推測氣功在三皇五帝時期已有濫觴,但是沒有確鑿證據證明踵息法在莊子生前被他接觸到,為他接受內化。
李歡友又吸收此觀點的部分內容,道明“踵”這一意象在道教里的重大意義,認為“踵”是連續天、地、人三才的前提條件。[4]筆者持不同意見,認為足在《莊子》中是“有待”的象征之一,并未發現莊子對它賦予了特殊的身體意義,何況《莊子》里記述諸多如叔山無趾、申徒嘉、王駘等兀者,莊子舉例形骸有缺時,腳上的殘疾占據很大的比重,但他們都是《德充符》里的正面形象,用來論述無用之用亦有大用處,形骸有缺卻可全精神。
第二類觀點認為莊子是對真人品質的虛指和譬喻。持此類觀點,既有因為針對實指論而提出的駁斥,也有為實指論的發展而提出。他們認為該句指真人沉心靜氣、定力深厚、保守自然,因此呼吸能到極深處,不同于常人心浮氣躁。持著這一觀點的主要是胡文英、王闿運等。胡文英認為“息以踵,亦不過靜極而深,后人添出許多作用工夫,反失真人面目。”王闿運認為是“喻深藏也”。王夫之在《老子衍莊子解莊子通》里將這種真人的沉靜淡泊更深的挖掘,指出真人的處世哲學和虛靜齊物的思想。[5]但是,這樣翻譯與下文無關聯,莊子也沒有必要采取“以踵”“以喉”的說法,直接用深、淺論之即可。
陳鼓應在《莊子今注今譯》里認為“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似乎是被養生服氣者篡改后的結果,“屈服者,其嗌言若哇”疑為“他處之文誤入”。[6]若是因句式不同、翻譯詰屈聱牙而斷定是為后人偽作,這是一種粗線條的邏輯思維,《大宗師》的“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段也并非句式完全整飭。
綜上,“真人之息以踵”無論采取哪一種理解方法,都有不恰當之處。筆者認為,“踵”字疑是“喠”字形近致誤,對于“息”字的理解應當不是氣息,而是采用滋養、生長之義。
二
“喠”字,《康熙字典》云:“《廣韻》之隴切《集韻》主勇切,音腫。《玉篇》不能言。又《廣韻》喠,欲吐。又《集韻》豎勇切,音尰。又取勇切,松上聲。又《廣韻》充隴切《集韻》蠢勇切音。義同。又《廣韻》氣急之貌。《集韻》急喘也。”“喠”古同“噇”,吃。根據材料,“喠”的本義疑為口中塞滿實物,引申出不能說話、欲吐、急喘等其他義項,在讀音為“zhǒng”時,主要指不能說話。
“踵”字,《說文解字》云:“追也。從足重聲。一曰往來貌。之龍切”。“喠”與“踵”都是形聲字,字形相似,字音相同,為二者謬誤提供了可能性。
“息”字,《說文解字》:“息,喘也。從心從自,自亦聲。相即切。”《段注》:“人之氣急曰喘。舒曰息。引伸為休息之稱。又引伸為生長之稱。”會意兼形聲字。從心,從自,自亦聲。自,鼻子。古人以為氣是從心里通過鼻子呼吸的。造字本義是以心為鼻,即胎兒不用口鼻、只借助母體的心跳來呼吸,沉靜安定,運氣若有若無。“息”字在道家里有特殊的意義。胎兒代表的混沌、原始、純凈境界使“息”字在造字之初便有了道的意味,消滅欲望,使心安寧,回歸混沌,增長道心、自然之心。“息”字有生長與消減兩種相悖的內涵。南朝吳均有“望峰息心”之語,佛家亦有“觀息”這一說法。李叔還的《道教大辭典》舉例“息土”,歸納了生長、滋養這一義項。[7]《莊子》里約有16處使用“息”字。[8]《莊子·秋水》云:“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周代其他書里也有“息”字翻譯為生長的例證,《易·剝》:“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喠”字譯為不能說話,結合文意指真人已經達到得意忘言、無法表達的混沌境界,“喠”與“喉”對舉,“息”字采用生長、滋養(道)這一意義,“以”翻譯為用。“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喠,眾人之息以喉。”的意思就是真人修道的境界很高深,他的生長、培育道心借助得意忘言的境界,一般人卻還要借助表達,借助語言技巧,借助蒼白的辯論。
“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談的是眾人,因為真人已到達“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的無待齊物境界,幽居默處,他的欲望是平的,他的胸懷是寬廣的。只有一般人才要分高低,欲望越重,自然之心越被遮蔽。再按照“真人之息以喠,眾人之息以喉。”的“真人——眾人”結構,“屈服者,其嗌言若哇。”的主語應當是真人,陳鼓應翻譯為:“議論被人屈服時,言語吞吐好似受到阻礙一般。”“喠”和“哇”都有欲吐之貌的意思。此句依舊說的真人不善言辭,如果強制他發表自己的見解,使用論辯的技巧,他會感覺到困難,因為他已經忘卻了自己的看法,拋卻使用語言時不可避免的成心和成見。
三
按照第二部分結論中的翻譯,不僅更加連貫順暢,“屈服者,其嗌言若哇。”不顯得突兀。也與接下來的內容相呼應,“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都在論述道是不可言述的、不可捉摸的,談道論道只會與道背道而馳。
莊子是不信任語言的,他不遺余力地表達對沉默的贊賞,對“一問三不知”的推介,《外物》:“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秋水》:“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這種獨特的言意觀形成原因有許多。
聯系莊子生活的戰國時代看,周天子的權威在消解,沒有統合貴族階層和底層民眾的合法價值觀,“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思想的困境沒有出路,狹窄的空間里眾人論辯交鋒,打著光輝的旗號,掩藏著炙熱的名利之心和茍且交易,權貴的勢力在主導著。莊子在這種環境里深知小國寡民政治理想的不可實現性,對人心的洞見使他陷入更深的絕望。他制造了與現實世界的隔膜,企圖用無言的方式與天外的天,超越現實的自然建立聯系、天人合一,重返太古的混沌恬淡。口若懸河不如絕圣棄知、各行其是。
其次,“言”無法盡“意”。朱立元、王文英在《試論莊子的言意觀》中將言意觀分成“言不盡意”與“意在言外”兩個維度。[9]道的隱秘幽微不能被描摹之萬一,道法自然,合乎天造,厭于人意。道成為一個實體化、可審視、可言說的對象后,已經喪失“無”的本體,沒有超越性,不足以稱為道。人施加的闡釋只會背離道的本義。“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無言才是至言,才是最高境界的言說方式。
最后,“言”象征著天人二分的思維模式。一旦談論道,意味著人從天人合一的境界里剝離開來,用對象化眼光去審視道。分出自己與外物,帶著成心和成見去議論、去判斷。純凈的蒙昧狀態就不存在了,如同混沌被鑿七竅而死,原有的自然靈氣消失了,沾染偏見濁氣。成玄英語:“夫以言遣言,言則無盡,縱加百非,亦未偕妙。唯當凝照圣人,智冥動寂,出處默語,其致一焉,故能無言則言、言則無言也,豈有言與不言之別、齊與不齊之異乎!”無言則抱樸守拙,靜觀萬變,齊物致道。“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都是莊子批判的境界,語言的形成,不可避免沾染說話者的小知。結合言與知的關系來看,絕圣棄知和得意忘言一定會達到高度的冥合,才能達到“吾喪我”的境界。小我旦暮琢磨著相互攻訐、傾軋,利用技巧取得勝利便洋洋自得、不可一世。真我要拋棄與摒除小我的偏見、利益。吊詭的是,莊子批判長舌講道,但自己卻孜孜不倦地扮演著一個勝人一籌、更高層次論辯者的角色。
四
綜上所述,之前古籍沒有明確載有“喠”字的“不能說話”義項的出現時間在《莊子》創作之前。雖然“喠”與“踵”均屬于形聲字,外形相似,字音相同,但周代直接文字材料稀少,尚未找到將“喠”與“踵”混同的先例。本文因為“喠”代入句中翻譯更加通暢、與上下文串聯更加緊密、與莊子哲學思想更契合這三個理由而提出一種可能性,但直接斷定“踵”字誤作“喠”字,還需要更多材料予以佐證。
注 釋
[1]陸欽:《莊子通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49頁.
[2]張文江:《〈莊子〉內七篇析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頁.
[3]陳廣忠:《〈莊子〉養生功法試論》,《諸子學刊》,2014年第2期.
[4]李歡友:《“踵”的身體意義:莊子“真人之息以踵”條詮解》,《阜陽師范學院學報》,2018年第3期.
[5]張昭煒:《由“踵息”看船山的精神趣味及思想深度》,《衡陽師范學院學報》,2013 年第2期.
[6]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202頁.(本文所引《莊子》原句皆出于此書,另不再注)
[7]李叔還:《道教大辭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5頁.
[8]洪業等:《莊子引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67頁.
[9]朱立元,王文英:《試論莊子的言意觀》,《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94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