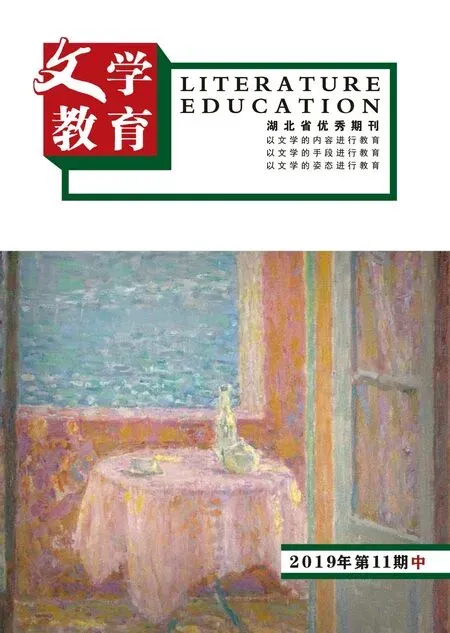身份認同視角下的美國墨西哥裔文學研究
黃曉梅
美墨戰爭使墨西哥近一半的領土淪為美國所屬,而這些領土上的居民也逐漸歸化為美國公民,即墨西哥裔美國人。自20世紀以來,在淘金熱的驅使下,許多墨裔移民來到美國,在美國他們始終對墨西哥文化有著較高的認同。同時,墨西哥裔美國人為了適應美國的社會,提高自身地位,在政治、經濟與斗爭等方面不及美裔、亞裔與非裔,唯有堅守墨西哥文化。美國墨西哥裔文學是由墨西哥裔與性作家在特殊的族裔背景下創作的,其為我們展現了當下美國墨西哥裔身份的困境與生活狀態的畫面。因此本文基于身份認同視角對美國墨西哥裔文學進行研究具有一定的意義。
1.美國墨西哥裔身份的困境
一方面,族裔身份的困境。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接收國,自美洲大陸發現以來,大量歐洲移民移居在這片土地上,后來拉丁美洲開始主導移民態勢后,墨西哥逐漸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移民輸出國,在此背景下,美國對有色人種的恐懼進一步加劇。墨西哥人作為美國最大的移民群體,其在美國的社會地位并不高,甚至成為美國社會的最底層。為何墨西哥移民社會地位低、普遍遭受歧視,本文認為原因如下:
一是墨西哥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數量增長迅速。從移民輸出國來看,墨西哥是美國移民最大的輸出國,而美國在此問題上堅持實用主義,當社會發展缺少勞動力時間,美國加墨西哥移民作為廉價勞動力;但當經濟增長緩慢、失業率高時,卻又對墨西哥移民普遍存在著仇視的心理;二是美國墨西哥裔身份背景較為復雜。回顧歷史,拉美大陸經過西班牙人的殖民統治,西班牙文化已經與當地的民族文化融合,而墨西哥文化就是西班牙與印第安文明融合的成果。而墨西哥移民在上述文化背景下又受到了美國文化的影響,這一點在桑德拉·希斯內羅斯《芒果街上的小屋》中可見一斑。在美國出生的墨西哥人,其思想觀念等受美國主流文化的影響,但仍無法擺脫其血脈,因此部分墨西哥移民仍時常回墨西哥探親,部分移民仍對墨西哥文化有著較高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從現實情況來看,雖然美國主流社會表面上承認不同民族與國家文化的多元性,但并未切實認識到不同民族與國家文化之間的差異。因此,美國墨西哥裔在經濟與政治上受限的同時,在文化方面也處于比較弱勢地位;三是文化身份的困惑。墨西哥裔美國人在美國備受歧視,同時從國籍上看也不屬于墨西哥。在《沒有姓的杰拉爾多》中“濕背人”(非法入境墨西哥人)一詞被反復提及,這些“濕背人”大多處于美國社會的最底層,他們負責最辛苦的工作,賺著最低的收入,他們在處于美國文化邊緣的同時,也成為墨西哥文化中的“外來人”。
另一方面,女性身份的困境。美國少數。美國墨西哥裔女性不僅面臨著族裔身份的困境,也遭受女性身份的歧視。在美國與墨西哥男權社會的背景下,女性的話語權少之又少,因此部分美國墨西哥裔女性對其身份認同有著更為復雜的感情。美國西南部的墨西哥裔男性在墨西哥男權觀念的影響下,當自己難以融入美國的文化圈、社交圈時,他們往往會將不滿情緒發現在女性的身上,美國墨西哥裔女性需承受著雙重壓力。
2.身份認同視角下的美國墨西哥裔文學
當第一批西班牙殖民者在1598年到達后來成為新墨西哥的地區時,他們遇到了美洲原住民,他們的祖先已經在美洲生活了13000多年。在殖民時期,西班牙人使用等級種姓制度根據西班牙和美洲原住民遺產的比例來描述和社會排列混合的個體。在美國的領土時期,新墨西哥的人口隨著美國其他地區移民而增長。面對新來的人可能在政治上被邊緣化,當地居民重新接受了西班牙語。后來,隨著墨西哥移民人數的增加,許多新墨西哥人開始接受和浪漫化長期居住人口的西班牙遺產。20世紀,來自墨西哥的移民率有所上升,如今,在美國人口普查中自稱HL的新墨西哥人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也自稱是墨西哥人或墨西哥裔美國人。由于這一地區特有的歷史,相對較近的墨西哥人與較深的西班牙人遺產的概念是今天新墨西哥州社會認同的一個顯著特征。
桑德拉·希斯內羅斯的作品圍繞少數族裔女性成長經歷進行創作,在其代表作《芒果街上的小屋》中,“房子”作為貫穿全文的意向,反映了女主角對平等社會環境的渴望與訴求。在《芒果街上的小屋》一文中,“房子”代表著政治與文化身份。奇卡諾運動是美國墨西哥裔爭取平等權利的民權運動,在二戰前,美國墨西哥裔與美國白人一同參與戰爭,他們認為戰爭后自己為美國所作出的貢獻可以換來社會的認可。然而,二戰后的美國經濟發展迅速,美國白人的生活條件進一步得到提高,但美國卻對有色人種有著較為強烈的排斥與歧視,這一現實情況使美國墨西哥裔充斥著憤怒與失望的情緒。在文中,桑德拉·希斯內羅斯將芒果街比作“悲哀的紅色小屋”,女主人公雖然住在芒果街上,但卻不屬于那里,這充分表現了美國墨西哥裔在美國主流文化邊緣化的地位。《芒果街上的小屋》中“房中的天使”指代的是妻子與母親,墨西哥是傳統的男權社會,在墨西哥傳統文化的影響下,桑德拉·希斯內羅斯筆下《芒果街上的小屋》中的妻子與母親缺乏自己的想法,對丈夫較為依賴,總是盲目的贊同他人的意見,心甘情愿地扮演著妻子與母親的角色,這些“房中的天使”將自己的一切都貢獻給丈夫與家庭。在文中,在男權社會下,莎莉父親認為美麗動人的莎莉是一個巨大的“麻煩”,為了避免莎莉姑姑的事情再度上演,莎莉的父親不讓她參加舞會,禁止莎莉與男孩說話。為了逃避父親的專制,沙麗不得不選擇輟學、結婚。但莎莉沒有想到的是,結婚后他從一個牢籠走進了另一個牢籠,莎莉丈夫對她的專制與獨裁與她的父親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莎莉不敢出門。受到母親與莎莉的影響,埃斯佩朗莎發誓不再做“房中的天使”,而是要有完全屬于自己的房子,不是誰的附屬品,而是完全獨立的自己。“屬于自己的房子”被桑德拉·希斯內羅斯賦予了更多的意義,作者通過這一意象希望能夠為更多的美國墨西哥裔在政治經濟與文化方面能夠獲得平等的地位。
在魯道夫·阿納亞作品《保佑我吧,烏勒蒂瑪》中,烏勒蒂瑪對主人翁的成長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安東尼奧的母親希望主人翁成長后能夠成為天主教徒,而他的父親則不希望他被宗教束縛。安東尼奧被他父親模糊的夢想和母親盧娜的理想所背叛,并被他們關于他未來職業選擇的爭論所困惑。與此同時,安東尼奧在學校中也遭受到白人同學的歧視,正是在安東尼迷茫時,烏勒蒂瑪來到了安東尼奧的身邊。烏勒蒂瑪行醫救人,是自然的化身,具有強烈的印第安文化意識。小說中穿插的10個夢境是主人翁對自己理解族裔身份集體記憶的映射。《關于出生的沖突》揭示了這種沖突根植于安東尼奧的無意識之中。在他出生后,他父母雙方的叔叔都聲稱他的出生是為了讓這個男孩和他們自己的團體綁在一起。他母親的仆人擦了擦黑色的山谷泥土在男孩的額頭上,并把農場的產品作為他的生活用品,同時把孩子和土地聯系在一起。然而,他父親的手下擦去了男孩頭上的污漬,給了他馬鞍和一把舊吉他。激烈的爭論幾乎演變成一場戰斗,雙方滿口咒罵和威脅,拔出了手槍。拔出了手槍。然后是可敬的助產士。”一位大人物讓他們安靜下來,聲稱只有她有資格埋葬這個孩子,而曾經把他和永恒聯系在一起的繩子。是她把這個男孩拉進了生命之光,而他自己也知道他的命運。在烏勒蒂瑪到來后,主人翁逐漸認識到萬物的靈性、人與自然的關系,并據此尋根,找尋身份認同感;同時也具有了包容差異性的思想。從烏勒蒂瑪身上來看,烏勒蒂瑪是一位民間藥師,處于社會邊緣的地位。盡管烏勒蒂瑪通過草藥挽救了一個又一個生命,在疾病面前她也會翻越千山萬水去治病救人,但正是這樣一位英雄,大多數人仍然對她有著敬畏的心理,甚至一些幼兒會在背后稱她為巫婆。
3.結語
在全球化背景下,身份認同問題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因為美國社會長期存有的族群問題,墨西哥裔面臨自我族群文化身份認同困境。在此背景下,以桑德拉·希斯內羅絲為代表的女性美國墨西哥裔作家將美國墨西哥裔邊緣化身份在文學作品中進行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