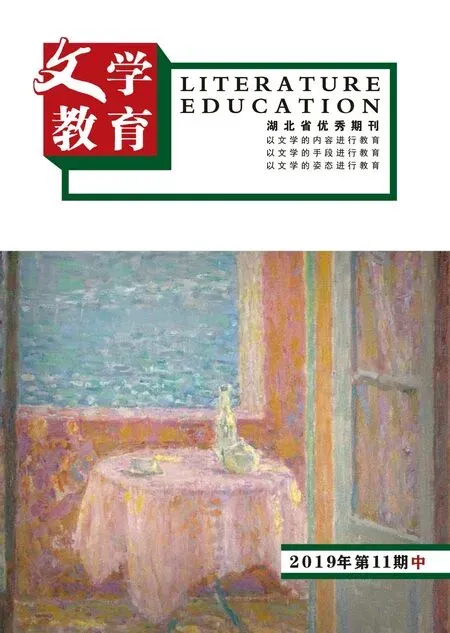孔子點贊曾皙之志的中西方美學底蘊
劉 瓊
孔子認為人的全面發展,是人在詩、禮、樂的全面熏陶中,不斷進步升華的,孔子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1]。孔子的這一思想與西方現代文藝理論、美學理論是一致的、契合的,康徳認為審美判斷力是溝通真與善、知識與道德、必然性與自由王國之間的橋梁(康德《判斷力批判》)[2]。席勒更是贊同人生的最高、最完美的境界是游戲,即只有當人在充分意義上是人的時候,他才游戲;只有當人做游戲時,他才是完整的人。席勒強調了游戲在人的精神自由、自我解放、自我去蔽上具有的獨特功效(席勒《美育書簡》)[3]。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出自《論語·先進》篇,是《論語》中少有的篇幅較長的一段文字。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爾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
對曰:“非曰能之,愿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愿為小相焉。”
“點,爾何如?”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孔子詢問四個學生的人生志向,前三個學生子路、冉有、公西華述志都不外乎是從政的人生理想,孔子都沒有點贊,而當孔子點到曾皙發言時,曾皙放下正在彈奏的瑟,述其志“異乎三子者之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畫面太美啦!這是《論語》中少有的寫景抒情文字,《論語》絕大部分的文字都是微言大義式的孔子教導學生的簡練語錄。而這段文字的格調與《論語》總體面貌大不相同,是吹進《論語》中的一股小清新之風。曾皙不過是希望在暮春時節,穿上春服,與五六個冠者,七八個童子,到沂水邊沐浴,然后唱歌跳舞,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對于為什么孔子認同曾皙志向,自古至今,各家眾說紛紜。
朱熹從理學及個人心性修養詮釋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于言外。視三子之規規于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嘆息而深許之。”(《論語集注》)[4]
南懷謹先生則認為,這是描繪的“大同世界”中,“個人真正的精神享受”,“曾點所講的這個境界,就是社會安定、國家自主、經濟穩定、天下太平,每個人都享受了真、善、美的人生,這也就是真正的自由民主一一不是西方的,也不是美國的,而是我們的大同世界的那個理想。每個人都能夠做到,真正享受了生命”(《論語別裁》)[5]。各位學者從各自信奉的思想學說出發,作出了不同的解讀,各有道理。
孔子的弟子曾皙說自己平生最向往的不過是與幾個朋友去郊外春游,穿著春服,在河邊沐浴,興致來了,就唱歌跳舞,然后詠而歸。為何這樣的人生理想,孔子卻深加贊賞呢?原來,孔子雖被后世尊為圣人,其實孔子和普通人一樣,也愛美,愛玩,愛與朋友聚會,愛大自然。其實,縱觀孔子的一生,不難發現,在孔子的內心深處始終充溢著文藝情懷。用我們今天的人物品鑒標準來講,孔子就是一位資深文青。孔子深諳文娛活動會給人帶來審美愉悅。這種審美愉悅是由內而外,使人的身心得以凈化與升華的快樂。
孔子深知人類一切文化、一切變革、一切知識,最終都是指向個人的幸福這個終極目標的。而人在什么狀態下才能進入這種幸福愉悅的體驗中呢?曾皙就描繪了這一情境:在無功利目的之下,與幾個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一起交游中,在感受大自然永恒地賜予我們最平凡又最美好的韶光時,我們身心會徹底放松,與大自然和諧地融為一體,我們會情不自禁地載歌載舞,這時審美愉悅是人處于真正身心快樂時的自然流露,無關乎政治,甚至可以暫時忽略現實的存在。所以,這樣率性的孔子不僅體現了真實的人性,而且十分地可愛。
人生中總要設法開辟出一段時光,任由自己沉醉于喜愛的文娛活動之中。只有在這種時候,我們的身心才是最為放松釋懷的,最自由與解放的,最幸福與開心的。所以,孔子要點贊曾皙之志。曾皙描繪的暮春郊游之樂,一如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中描繪的那樣,與群賢曲水流觴,共享美好春光;一如蘇軾在《赤壁賦》中記述的那樣,與好友泛舟江上,賞月抒懷那樣的韶光是生命中的最美之境。當我們身處繁忙而瑣碎的人生事務之中,若能偶遇這樣的閑暇,必當珍視,因為它是最美的遇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