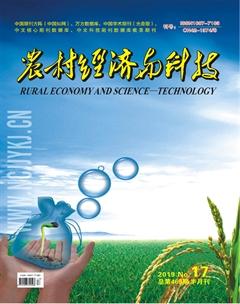中心城市產業嵌入縣域程度評價分析
劉漢卿


[摘要]在產業一體化、產業融合、產業轉移的理論基礎上,構建了江蘇省中心城市產業嵌入度的指標體系,圍繞產業融合和產業轉移兩個二級指標選取了12個三級指標,采用因子分析法對江蘇省44個縣域的中心城市產業嵌入度進行計算排名。根據嵌入度得分結果將江蘇縣域分為中心城市產業嵌入度高水平階段、嵌入度較高水平階段、嵌入度一般水平階段、嵌入度低水平階段四個類別。
[關鍵詞]縣域;嵌入度;因子分析法
[中圖分類號]F127[文獻標識碼]A
1 引言
近年來,我國的縣域經濟獲得了快速發展,對推動農業發展、農村繁榮、農民富裕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實現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同時,城鄉產業融合發展將城市和鄉村放在同等地位,改變了過去以城市發展為主、外延擴張城鎮化的戰略,逐步走向城市和鄉村共同發展、統一發展的策略(何紅,2018),這一發展過程中,無疑離不開中心城市集聚和擴散功能的發揮。中心城市要擴大規模,承載生產、生活與服務體系功能,提升城市文明和現代化水平,真正發揮對縣域經濟的帶動、輻射、調節和服務功能,需要縣域經濟支撐(袁中許,2014)。就現狀而言,中心城市強調自身中心作用卻忽略自身有限的條件,以致所屬縣域經濟無法感受向心引力和輻射,表現為孤立和分散(吳麗娟,劉玉亭,程慧,2012),縣域經濟要突破發展瓶頸,實現收入持續增加,農副業繁榮,要發揮中心城市在縣域經濟體系中的核心、引擎和重要支撐作用(張海豐,黃河東,2006)。
本文之所以選擇以江蘇省為例,首先,因為江蘇省地處長江三角洲,是我國經濟增長最快、最具活力的省區之一,到2017年底,江蘇省以占全國1.0%的面積,創造了占全國10.39%的GDP,2017年江蘇省對國家GDP的貢獻量居全國第二位。其次,江蘇省13個地級市的發展呈現一定的梯度性,蘇南地區較為發達、蘇中次之、蘇北地區則較為落后。再者,江蘇省的產業結構的失衡導致江蘇第一產業產值的增長速度明顯低于二、三產業的增長速度。綜上,以江蘇為例研究中心城市產業嵌入對縣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對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縣域都具有較強的典型性與現實意義。
2 中心城市產業嵌入度指標體系評價
2.1 指標體系理論依據
城鄉二元結構下的傳統農業與現代工業并存、農村社會與城市社會相互分割這種經濟態勢,是普遍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問題。而城鄉差距首先在城鄉產業上的差距顯現出來。城鄉產業發展不平衡、產業間的低關聯度及產業結構的高度同構化日益嚴重,因此,從產業一體化角度聯結中心城市與縣域,促進縣域經濟發展,推動實現城鄉一體是有必要的。
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根據區域生命周期理論,當一個區域進入成熟期后,生產規模的擴大,已經無法依靠創新時期的生產要素優勢獲得較低的生產成本,而且隨著勞動力價格的提高,產業的生產效益下降。因此產業資本的空間轉移成為必然,中心城市對縣域、或發達縣域對不發達縣域的輻射效應開始顯現(秦興方,2017)。在本文中,輻射效應是指以中心城市為經濟發展的基點,通過經濟、科技、人才等資源優勢及產業優勢,帶動縣域經濟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中心城市的部分企業傾向于將生產基地逐漸向縣域轉移,并將總部留在中心城市。這樣的轉移形式必然會給縣域經濟帶來產業結構、社會福利、生態環境等多方面的影響。
隨著信息化的發展和勞動分工的深化,產業間的邊界逐漸模糊化甚至出現了交叉點。因此,當中心城市的產業、資源等外源性動力不斷向縣域流入后,縣域如何善用其資源并結合自身產業優勢進行一定程度的產業融合則顯得尤為重要。產業融合不僅是現代產業發展的新趨勢,也是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新動力,產業融合從優化升級城鄉產業結構、推動城鄉空間互聯互動、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強化城鄉生態環境保護等不同層面,推動城鄉融合發展(顏培霞,2018)。利用電子信息、生物工程等新興產業與其他產業的廣泛關聯性,嵌入其他傳統農業。并用高新技術、綠色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提高了縣域農業的經濟效率和市場競爭力,推動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這對于發揮農業的多維功能、推動農業現代化,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綜上,本文將嵌入作為銜接中心城市與縣域的手段,來闡明產業輸入方中心城市對縣域產業轉移的效果、承接方縣域結合自身特點進行產業融合的效果。因此本文在構建評價體系時選取了產業轉移和產業融合兩個二級指標。
2.2 指標體系構建
根據產業一體化的內涵和中心城市產業嵌入的實現機制,以及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的原則,本文建立的統計指標體系從產業融合和產業轉移兩個層面選取指標,具體指標見表1。
2.3 指標體系綜合評價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對江蘇各縣域的產業嵌入度進行綜合評價,具體步驟如下。
2.3.1 對數據進行預處理。本文選取的11個指標中,除基尼系數、恩格爾系數以外均為正指標,因此本文將基尼系數采用公式轉化為正指標,其中k為適度標準,基尼指數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因此k取值為0.4對數據進行處理。同時,對恩格爾系數取其倒數進行處理,最后使用SPSS軟件對正向化的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2.3.2 對樣本進行可行性檢驗。對樣本數據進行KMO和Bartlett球形檢驗,本文KMO統計值為0.79,接近于0.8值,說明各指標之間存在較強的關聯性。
2.3.3 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用主成分分析法計算各個因子的方差貢獻率和累計方差貢獻率。按照特征值大于1和累計方差貢獻率為80%~85%的原則,確定4個公因子個數。并根據每個公因子下各個指標的占比來進一步解釋說明各個公因子的經濟意義。因此,本文將F1命名中心城市產業嵌入度因子;F2命名為經濟發展程度因子;F3農業服務業發展水平因子;F4社會收入公平度因子。
2.3.4 計算因子得分。將提取出來的每一個公因子都各自表示成原有12個指標的線性組合,估計得分的,四個因子的具體得分見表2。
2.3.5 計算41個縣域嵌入度得分。根據各個因子的得分,將這五個因子的貢獻率作為權數(軟件分析可得),對因子得分加權平均得到綜合評價函數。計算出江蘇省41個縣域中心城市產業嵌入度的綜合得分Z,計算結果見表2所示。
3 中心城市產業嵌入度的結果分析
由表2分析可知,江蘇中心城市嵌入水平差異顯著,區域上呈現出蘇南、蘇中、蘇北嵌入度水平逐步降低的分布規律。為了更直觀的看出各縣域的嵌入度水平高低,本文使用Q型聚類層次聚類法將因子綜合得分Z作為變量進行聚類分析,結果顯示為七類,由于類別過多,因此本文結合具體實際將其所處的階段劃歸納總結分為四類。
第一類:中心城市產業嵌入度高水平階段,包括常熟市、昆山市、江陰市、張家港市,以上皆為蘇南地區,根據表2可以看出此類地區的第一個公因子—中心城市產業嵌入度因子得分都很高,可見該縣域的產業轉移、產業融合對當地產業結構、經濟水平、社會福利有著顯著的效果。但是,第二個公因子的排名普遍較低,主要是由于縣域GDP指數較低造成,也見這類縣域在經濟總量達到了一定程度后,無需一味追求高增長率也能取得高嵌入度水平。
第二類:中心城市產業嵌入度較高水平階段,包括太倉市、揚中市、宜興市、海門市、泰興市、丹陽市、靖江市、儀征市、海安縣、啟東市、如皋市、句容市,主要分布于蘇南和蘇中地區。此類地區第一個公因子水平普遍較高,這些縣域經濟發展較好,產業結構以非農產業為主,如靖江市、揚中市等縣域的非農比例皆高于97%。但也存在不足之處,如靖江、揚中、泰興的第3個因子排名很低,主要是由于農業服務業的產值過低,產業結構同構現象嚴重,形成了地區間的不均衡發展。此外,這類地區第4個公因子的排名都較為靠后,主要由于縣域間收入不公平導致。
第三類:中心城市產業嵌入度一般水平階段,包括如東市、沛縣、高郵市、溧陽市、東臺市、邳州市、響水縣、建湖縣、寶應縣,主要分布于蘇北和蘇中。此類地區第1個公因子得分都比較低,但個別地區也有得分高的公因子,如沛縣的第2和第4個公因子,說明其經濟發展速度較為可觀,且城鎮與農村居民的收入差異不大,社會收入較為公平;東臺的第二個公因子得分最高,農業在與其他關聯產業的融合度較高。
第四類:中心城市產業嵌入度低水平階段,包括新沂市、射陽縣、興化市、盱眙縣、金湖縣、阜寧縣、東海縣、濱海縣等16個縣域。主要分布于蘇北地區,這些縣域的經濟發展水平都較為落后,工業化水平落后、產業間的融合度低、社會收入不公平,再加上縣域發展自身內生動力不足,造成了中心城市對這類區域的聚集與擴散較弱,產業嵌入水平低,從而一直深陷經濟發展落后的惡性循環當中。
[參考文獻]
[1] 何紅.城鄉融合發展的核心內容與路徑分析[J].農業經濟,2018(02):91-92.
[2] 吳麗娟,劉玉亭,程慧.城鄉統籌發展的動力機制和關鍵內容研究述評[J].經濟地理,2012,32(04):113-118.
[3] 張海豐,黃河東.提升中心城市競爭力,帶動廣西經濟發展[J].改革與戰略,2006(04):43-45.
[4] 袁中許.均勢型地方中心城市與縣域經濟的戰略協整[J].社會科學研究,2014(04):7-13.
[5] 秦興方,田珍.縣域經濟發展的動力結構及其變遷規律[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7.
[6] 李存貴.中國省域城鄉產業協調發展綜合評價[J].統計與決策,2016(09):6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