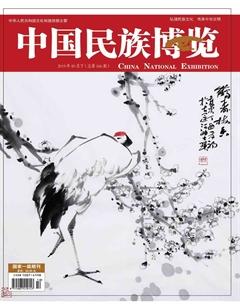從《詩經》燕饗詩看守禮以序
【摘要】《詩經》中的燕饗詩是周代宴席中必不可少的,“禮終而宴”。禮儀在《詩經》中是客觀存在的,燕饗詩中更是涉及到很多的禮儀。對《詩經》燕饗詩的研究主要是想要突出以詩載禮,詩歌在人際交往中的作用、在政治上的應用以及階層身份的劃分等方面的作用是本文研究的重點。本文主要以文獻整合的方法、社會學的方法和心理學的方法進行詩歌與禮儀的研究。
【關鍵詞】燕飲詩;禮終而宴;以訓共儉;守禮以序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詩經》是一代文辭之盛,漢代把《詩經》列為儒家經典。僅就先秦開始到清,《詩經》研究人才輩出,學派紛起,卓見層出。《詩經》中的燕飲詩從文學的角度進行情與禮樂的相關性研究,在宴享間使用《詩經》中的一些詩伴隨樂曲進行演奏的情況進行簡述。《詩經》編撰成詩集并廣泛流傳,行之以禮,世人認可。《詩經》之于禮樂文明,猶如承筐,其誕生于崇禮尚樂的繁榮時代,周代禮制文化與《詩經》的產生有著深刻的淵源。
一、以詩載禮,守禮有序
朱光潛在《詩論》中這樣記載:“詩歌在起源時是神與人互通款曲的媒介。人有所頌禱,用詩歌進呈給神;神有所感示,也用詩歌傳達給人。”朱光潛以宗教為中心論述了詩的起源,李澤厚則在《美的歷程》中闡述了詩與歌舞的密不可分。由此看來,詩、歌、舞的發展雖然有其各自的特點,但是也可以互相配合而存在。
《詩經》中的“頌”是宗廟祭奠之歌,“雅”多是“王畿”之樂,“風”則是各地方的民間歌謠。關于禮的起源,與原始祭祀活動有關。《說文》曰:“禮,覆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趙沛霖先生說:“原始氏族成員在祭祀祖先神靈時,必陳飲食供神靈享用。這種陳供開始比較粗糙,后來為了表示虔誠,飲食越來越豐盛,方式越來越講究,并且規格和儀式逐漸固定下來,久而久之形成了大家共同遵循的準則,這便是禮。”由此看來,《詩經》中“雅”“頌”中的一部分燕飲詩以及禮與祭祀活動有著密切的關系,體現著祭祀禮儀的秩序,是祭祀典禮的重要組成部分。
“禮終而宴”,燕飲是周禮秩序的體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禮的實施也離不開《詩》和樂曲。在《儀禮》《左傳》等典籍中記錄著燕飲場唱《詩》、配樂的情形。《儀禮·鄉飲酒禮》中這樣記載:“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逐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公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以上記載可見,《詩經》中的燕飲詩與禮樂二者關系密切,禮、樂與詩三位一體,共同完成燕飲禮儀儀式。顧頡剛曾經論述:從西周到春秋中葉,詩與樂是合一的,樂與禮是合一的。禮儀在《詩經》中是客觀存在的,鄉樂的演奏也規定了每一步需要用的《詩》、需要用的樂器,燕飲詩中更是涉及很多的禮儀,演奏者由堂上堂下交替演奏,詩樂與秩序交融,引導賓客,是守禮有序的體現。但是對《詩經》中存在的禮儀,如果不加以分析,人們就很難準確把握禮樂寓于詩的意境。
燕饗禮主要應用于周代親近四方賓客,反映周代宴席的禮儀。《周禮》:“以飲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燕饗之禮,是古時王室以酒肉款待賓客之禮;燕禮在寢宮舉行,烹狗而食,主賓獻酒行禮之后即可開懷暢飲。
《楚茨》中“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記載了祭祖祭神之時饗禮的情況,“絜爾牛羊”寫出祭祀過程所用的糧食、牲畜,“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邀請祖上前來享用,整個儀式莊嚴有序,恰到好處,主要形容祭典之盛、降幅之多。饗禮之后進行燕禮,以燕禮來說,主要就是君臣之間的燕飲禮儀。詩歌通過對禮儀過程的贊美來表達對客人的敬重,特別是旅酬言語之禮更是客人示道的重要場合。周禮的禮節比較復雜,但是燕禮比飲禮、食禮簡約,首先是陳設燕禮的器具。國君宴請臣屬是先讓小臣代表國君請各位大臣留下,準備參加宴請。然后準備燕飲間用的樂器、酒器,酒器的方位上也有講究,方向以南為上,卿大夫們的酒樽置于左側,左側即南方,公的酒樽在卿大夫酒樽之南,表示尊重。除此之外就是進行灑掃,此后就是賓客入席。如《小雅·伐木》對以上程序進行描述:“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於粲灑埽,陳饋八簋”,寫的就是以上準備宴席的場景。《毛詩序》云:“《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伐木》一詩,正是宣王初立之時王族輔政大臣為穩固人心,取消間隙從而增進親友之情而做。然而詩中“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可見宴請的叔伯舅親沒有到場,但是禮儀秩序井然有序,由此看出周代禮制中不僅涉及敬重還有宗族之間的情感,從而看出《詩經》也承載了以宗族血脈為紐帶維護周代政權的安定,從親親到尊尊的互相轉變。《詩經》所謂“大宗維翰”“宗子維城”就是說的周代以宗法制度得以代代相傳。
《札記·樂記》:“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禮之不可易也者。”由此可見禮樂也有情理之分。《禮記·樂記》所說的“禮、樂、刑、政,其極一也。”由此看出“禮”與國家章法制度聯系在一起,把“禮”上升到國家政治的層面。“禮”應包括了教育、文化、軍事、經濟、政治、外交等方面,是一個王朝的刑法、政法、章程以及典范,“禮”更是周統治者為該國帶來和平與穩定秩序的保障。《左傳·禧公十一年》中載:“禮,國之干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陸奎勛《陸堂詩學》載:“《鹿鳴》《四牡》《皇華》三詩,用之燕禮及鄉飲酒禮。”由此可見對當時的禮樂制度有嚴格的管理,必須以適應禮制為前提。這些表演音樂的工作人員必須隨著禮的秩序,按照周代禮制順序進行奏樂。可見周王朝時期,在詩歌演奏過程中隨著演奏人員遵循的禮樂秩序,上至諸侯下至禮樂演奏人員,對君王來說,他們在身份上不僅是自己的臣下而且需要按照絕對的秩序服從王命。《毛詩序》云:“燕群臣嘉賓也”。但是隨著周王室由盛轉衰,尤其是至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經常在禮樂方面做出有違禮儀的事情,《左傳·襄公四年》有關于穆叔去晉國的記載,從禮儀上說,穆叔去晉國,晉悼公宴享穆叔,金屬樂器演奏《肆夏》第三章,穆叔不答拜,樂工歌唱《文王》第三章,穆叔又不答拜。歌唱《鹿鳴》第三章,穆叔三次答拜。其實這里外交官子員問過穆叔,穆叔對于錯誤的演奏不和身份的樂章,都給予了反駁,《三夏》適用于天子見諸侯,《文王》適用于兩君相見,所以,對于不適當的樂曲用在不同身份的人是外交禮節上的失誤。所以,由《詩經》與樂的合奏,不同篇章代表的意義上可看出,演奏樂曲的不同也代表了身份的不同,此引折射的是尊卑秩序,有此方可行政天下,此為禮的實質之一。
二、場合多變,盛行緣由
《詩經》的流傳有多種方式,宴飲詩歌多應用于儀式與典禮。在周代,制禮作樂,禮樂昌隆,經過長時間的審定匯編,《詩經》已經適應禮樂,成為了合乎禮樂制度的樂歌。詩樂的融合,更加便于人們對《詩經》的記誦。使《詩經》的燕飲詩歌向貴族階層普及與流傳,西周與春秋早期更多的運用這種普及方法。
(一)《詩經》燕饗詩的適用場合
根據《儀禮》《禮記》等記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已經多應用于典禮禮儀的場合。其主要用于鄉飲酒禮、大射禮、燕禮等場合,歌唱時的儀式、演奏的順序都是固定的。《儀禮·鄉飲酒禮》記載:“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儀禮·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若舞則《勺》。”用于大射禮儀,《儀禮·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顯然,《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首詩歌發生了場所的變動,由鄉大夫擴大到宴請諸侯。可見燕飲詩也根據場合、宴請對象而發生變動,例如《左傳》成公十二年記載:“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由場所的漸變、鄉飲酒禮的記載上可以看出當時的禮樂制度已經相當完善了,而且也是用于典禮樂曲的原因,《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一起入樂的形式也具有規范化的屬性。《儀禮·燕禮》鄭玄注曰:“正歌者,聲歌及笙各三終,間歌三終,和樂三終,為一備。各亦成也。”正歌是指樂師先歌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各三次;演奏《南陔》《白華》《華黍》各三次;接著唱《詩經·小雅·魚麗》,以笙吹奏《由庚》應之;歌《詩經·小雅·南有嘉魚》,以笙吹奏《崇丘》應之;歌《詩經·小雅·南山有臺》,以笙吹奏《由儀》應之,歌與笙吹交替進行各三交。最后配樂合唱《周南》《召南》六詩各三次。
比如,《小雅·鹿鳴》反映了完整的燕禮過程,全詩以“呦呦鹿鳴”起興,營建了一個熱鬧而又諧和的氣氛,如果是君臣之間的宴會,那種本已存在的坐立不安和緊張的關系馬上就會緩和,這是燕禮重于慈惠的一點。《詩集傳》云:“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飲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假如主人為君,客為臣,君臣之間的等級、思想上的隔閡也會隨著宴會的氛圍慢慢趨于和諧的基調,溝通君臣之間的感情,此后又把這種意境帶入到“鼓瑟吹笙”的音樂伴奏中去,雖然樂譜早已失傳,但是從詩歌的整體內容上看,整個宴會應該是在一個歡快、和悅的氛圍中進行的。雖然君臣在燕飲場合具有上下等級以及政治色彩的情況,但是賓客通過“承筐是將”,獻上所盛的禮物,而后主人又向來賓致辭:“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是在說現在宴席上的一些客氣話答謝來賓,主賓之間這種你來我往的關系也描繪了融洽的君臣關系。
(二)《詩經》燕飲詩流傳的原因
《詩經》作為禮樂的載體而存在,除此之外,《論語·子路》中也提到:“頌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始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所以,《詩經》在當時的流傳方式除了作為禮樂制度存在也是人人爭相誦讀的語言溝通工具。又如《論語·陽貨》:“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由此也看出《詩經》在當時的各個階層是廣泛流傳的。又如《論語·陽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這就是說《詩》能夠激發人的感情,洞悉仁德,促進人的團結,能夠學得譏諷的方法。近到能夠明白如何侍奉父母,遠到可以學習如何侍奉君主,還可以多學習些鳥獸草木的名字。
《詩經》燕飲詩也可以作為賦詩言志的一種直接流傳和應用存在于宴會場合。金景芳在《論宗法制度》一文中也指出:“……在其政權所及范圍內,宗法不適用,決定身份的是政治地位不是血緣關系。但是,如遇到另外一種情況,即與諸侯尊卑相同,則宗法還適用。”春秋時期,諸侯國之間的會盟十分頻繁,燕飲詩上可以看出周代的禮制特征,燕飲詩即體現出了濃厚的君臣之間的互敬精神,即君以仁愛治臣,臣以恭敬敬君的思想。《禮記·樂記》:“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同文,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樂是為了和同人們的情感,情感和同就會互相親近。禮是為了區別人們的差異,有了差異就會互相尊重。但是樂過分或者禮過分都會造成威脅,所以禮樂之間相互制約,君臣之間的關系也是如此。《小雅·彤弓》:“彤弓弨兮,受言藏之。”寫出了有功諸侯接受恩賜的莊嚴典禮,而且寫出了所賜彤弓的行狀和受賞者對弓矢的珍愛,非直接地傳達了受賞者的感激之情。“我有嘉賓,中心貺之。”周天子把自己的臣下稱為“嘉賓”,對有功諸侯的鐘愛之情溢于言表。從“鐘鼓既設,一朝飲之”能夠看出宴會充滿了歡暢的氛圍,雖然是謳歌周天子的文治武功,也可以看出燕飲詩在當時禮樂制度下傳播的必然性。
周王室對于諸侯的宴請,燕飲禮儀的復雜,臣下對君王的尊敬之情都在《詩經》的燕飲詩中有所體現,具備君王宴請諸侯的政治用意。《桑扈》中“君子樂胥,受天之祜。君子樂胥,萬邦之屏”為起始,整首詩歌是以君子、諸侯為人物中心,然后涉及上天所賜的福祿,福祿如何延綿,是依靠諸侯的力量,如果把這里的君子看做君王,那么就是君王借燕飲來籠絡諸侯,可見,這里所謂的安邦是少不了諸侯的安定與支持的。此后兩章分別敘述了飲者的身份與限制:“之屏之翰,百辟為憲”,而后又提出“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希望各位遵守禮制限制自己的行為。“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以酒隱喻柔軟順從是美酒的特點,人不傲才能福祿不斷。對于君王對于諸侯的勸解來說,是非常具有政治隱喻色彩的。
三、結語
綜觀以上分析不難發現,周代統治者對禮樂制度提出了諸多的要求,同時《詩經》中的燕飲詩在當時祭祀典禮之后的宴席上也擔任著守禮有序的義務,并且禮樂詩與周代禮儀之間的相互制約,可見周代統治者為了自身政治的鞏固,對《詩經》燕飲詩歌在宴席上進行了嚴格的規范應用。在周代各種燕飲場合,《詩經》燕飲詩歌作為燕飲禮的載體,側重于溝通君與臣之間的感情以及以訓共儉;通過《詩經》中的燕飲詩歌也表現出周天子的慈惠之心以及共儉以行禮的思想,加強臣下與諸侯國的情感聯系。《詩經》中的燕飲詩也反映了燕飲的場所不同,嘉賓的具體指代內容也不同。《詩經》燕飲詩作為禮樂制度的載體,守禮有序的同時確定了各個階層不同的身份等級。同時,燕飲場合的不同、君臣對答的不同也寓意著濃厚的政治色彩。燕飲禮儀之間,賓主在歌舞杯盞聲中,談笑頻頻,其樂融融,美食旨酒傳遞著賓主間的綢繆之意,也遵循著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即親親、尊尊相互轉換。《禮記·文王世子》云:“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周禮最大的特點不僅僅在制度和禮儀這兩個方面,還在于周統治者把“人倫關系”很好的融入到政治統治方面,統治階級需要的“忠君”“愛國”的政治思想是維系權利的紐帶。中國文化在“則以觀德”的全新時代上,還衍生出了統治者借守禮以序強調階級的層次劃分,同時也可以看出當時從對神的崇拜中走出來,上升到了對人重視的新維度。
參考文獻:
[1]王文錦.禮記譯解[M].北京:北京中華書局,2001.
[2]阮元.儀禮·鄉飲酒禮十三經注疏本[M].北京:北京中華書局,1980.
作者簡介:李楊(1986-),女,博士,中級,研究方向:中韓詩歌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