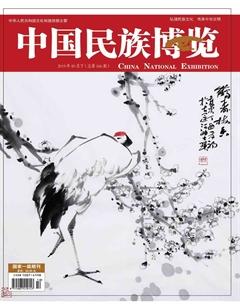淺談嚴歌苓筆下《扶桑》中主人公形象的大智若愚
【摘要】嚴歌苓以冊唐人街正史、野史為背景,以百余年前中國女子扶桑漂洋過海、在異域他鄉賣笑以艱難求生為線索,在長篇小說《扶桑》中塑造了扶桑這一人物形象。她作為第五代中國移民的代表,在欺凌、死亡和暴亂的背景下不僅僅象征著中華民族忍辱負重、寬容博愛的精神品質,更是近代以來飽受戰火摧殘的古中國的縮影。前人研究中多認為扶桑是位天性愚鈍、逆來順受的女性,這與她的母性氣質密不可分。但如果將她視為第五代中國移民的代表,作為受苦受難的近代中國的縮影來分析,則能凸顯出其深廣的智慧與非凡的膽識。
【關鍵詞】扶桑;智慧;中國
【中圖分類號】G623.3 【文獻標識碼】A
一、扶桑的智慧
嚴歌苓多次在小說中強調那些不可思議的情節都是真實的,它們都來源于“史稿”。 但由于這個被發掘出來的經歷太像傳奇,如果作者轉述不小心帶上了雕琢的痕跡,那它就偏向于一部編造出來的、取悅世人的故事。
《扶桑》開頭便以第二人稱方式介紹扶桑,“這就是你。這個款款從喃呢的竹床上站起,穿著猩紅大緞的就是你了。緞襖上有十斤重的刺繡,繡的最嚴密的部位堅硬冰冷,如錚錚盔甲。” 瞬間拉近了讀者與扶桑的距離,刺目的紅色成為了作品中的典型視覺符號,也成為扶桑本體的代表。扶桑出生于湖南采茶人家,14歲嫁于廣東,由于丈夫一直遠在海外故由一只公雞代為成親,6年后扶桑在人販子“出海尋夫”的哄騙下,被掠至舊金山為妓。在遠洋航行的途中,扶桑并不像其他女子一般尋死覓活或不吃茶飯,她異常聽話甚至坐著也睡得爛熟。人們通常認為她似乎是有些癡傻的。
出現在嫖客們眼中的扶桑就像遙遠而神秘的中國,具有一切東方古典美的特征,吸引著西方人好奇的目光,其中便有一位十二歲男孩克里斯,他是一個不成熟的、無偏見的“他者”。克里斯沒有父輩們對中國根深蒂固的成見,他用一顆兒童純真的心靈去感受扶桑迷人的東方情調、鴉片般的魔力。在克里斯眼中,“她撮起的嘴唇和垂下的睫毛使她臉上出現了母牛似的溫厚。她每吹一口氣,半透明的綢衣就變動一回光影”。這些充滿溫存的場景帶給了美國男孩克里斯靈魂上的震顫。他逐漸發現扶桑總是順從地接受一切,看似像一團毫無抵抗能力的霧氣,總能在被撕裂、被分割之后重新聚合,恢復成原來的模樣。然而,扶桑并不愚蠢,此時的扶桑知道自己的力量薄弱,她知道在異鄉的自己仿佛無根的草,生死、命運難以掌控,所以,她似乎正是以這種全然接受、莫不在乎的態度,在發起無聲的反抗,她越是漠然不語,她的抗爭意識似乎就更強。同時,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環境下從容仁厚、謙恭倔強等氣質也影響了她的行為,讓這位少女在紛亂的戰火中接受了苦難,卻并不自怨自艾,而是在苦難中獲得利益,在毀滅中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定位,從而找到了精神上的安寧。
作品中扶桑永遠記不住客人姓名的行為往往被視為是其癡傻的表現,她因此而攬不到“金招牌”被多次轉賣,多次受到老鴇的毒打,她似乎對這些毫不在意,總對自己的糊涂回以一個平實而真切的微笑,這種微笑沒有絲毫諂媚與做作。但我們認為扶桑并不是健忘的,她是不想記得又不愿記得,因為記得客人姓名不僅不能讓生活發生真正的轉折,還常常會因為對部分客人寄予太多希望而像其他女孩一樣,過早死于黑暗之中。相反,她的微笑讓接觸她的每個人感受到平等、甚至感到“洞房的熱烈以及消滅童貞的隆重”。扶桑用真誠的微笑打動了不少嫖客卻又無心于利益得失,因為她明白活著就是最大的奢侈。海港之嘴廣場兩彪人馬為爭著贖出扶桑進行了血腥殘忍的械斗,而扶桑只是安靜孤獨地在小屋中與死神決戰,外界的一切似乎都與己無關,她關心的只有活下去。在經歷械斗爭奪、與克里斯的愛恨糾葛、大勇為其抬高身價之后,扶桑成為了唐人街歷史中風華絕代的名妓。
近代中國的血淚歷史也是如此,在被列強分割爭奪的百年歷史中,中國始終在用盡全力修補自己,掙扎著進行從器物到思想再到制度的近代化改革,來不及關心其他國家政治形勢的變革和國際潮流的發展,為救亡圖存而努力掙扎。
二、扶桑的精神
扶桑的微笑里有著看透生活本質卻又無法改變的無奈。被救濟院從生死邊緣拉回之后,她發現讓情人克里斯漸漸產生距離感的是身上的白麻布做的病服,她很快意識到失去了那身紅綢衣她就不再是具有神秘魅力的扶桑,她已經和那片紅色融為一體。大勇來抓她的夜里,她對偷竊的誣陷微微一笑,讓大勇帶走了自己,這似乎難以理解但卻又最為合理。這不是一位有些失智的女子的選擇,而是扶桑的一種高傲,她被迫來到異國他鄉,身份與地位的改變并不是容易的,也不是沒有任何代價的。紅衣是卑微甚至骯臟的,但擁有它扶桑可以感知到世間的一切冷暖,真情或虛偽,這是一種有溫度的、有觸感的生命體驗,而不用改變自己,在救濟院里過寄人籬下的生活。扶桑用微笑蔑視了救濟院的環境,包容下自己卑微的生活。很顯然,作為處于邊緣狀態的女性,扶桑并沒有被生活的重擊所壓倒,她在默默地忍受,并利用自身強大的生命力努力活得更好,而正是因為如此,這位女性也成為洗滌諸多人靈魂的關鍵所在。
同時代移民中的中國男性勞工亦是如此,他們都不接受行乞的生活方式,也不因為被嘲弄欺凌而改變自己的氣節,寧愿安靜地忍受著非人的生存環境、低廉的工資,靠一小罐米飯和一撮鹽在這片土地上頑強地活下去。更不會懼怕外界的歧視、驅趕、毆打,因為即使是面對死亡也懷有從容而心甘情愿的態度。
平凡的中國百姓在西方文明下承受著排斥與重壓,近代中國亦在近代化進程中抵御著西方列強帶來的生存危機。扶桑的身上傳達了一種觀照東方弱勢文化生存力量的全新角度,強者可以踐踏弱勢文化,卻不能剝奪它存在的權力,弱者文化有其自身的巨大魅力。近代化進程中,中華民族傳承著獨立、清冷又堅強的文化氣質,并沒有在戰火與硝煙中迷失自我。近代中國在經濟與科技等領域處于相對落后的階段,但中國文化始終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對自身的確認、肯定指引著戰后中國精神的回歸與重建。中國傳統的身份特征就像移民們放在舊金山唐人街的巨大鹵缸和扶桑的那一身紅綢衣。人們始終在以尊嚴和生命為代價為之守護,才使大洋彼岸的中國堅守住了傳承了千年的文化精神,最終在自救中走向新生。
扶桑的智慧不止于此,她的內在靈魂里不僅有著超凡的遠見,還擁有偉大的犧牲精神。當克里斯沖破狹隘的民族偏見、拉著扶桑的手走在美國街頭,向整個社會宣戰的一日之后,扶桑卻靜悄悄離開了。她穿著一身重彩、頂著丹鳳朝陽的蓋頭去刑場與大勇完婚,陰差陽錯地完成了他們兒時的婚約。她此舉既保護了克里斯,讓克里斯在剩下的人生中可以重新選擇,在一個正常婚姻的保護下享受生活,又保護了自己,從此遠離所有的愛恨糾葛;找到了婚約里的丈夫,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她錯過的人生,死去的大勇也從此保護了她的自由。扶桑的結局是一團迷霧,有人說她用積蓄買船回家,也有人說隨著美國民主平等的進步,扶桑定居于美國,但終究扶桑已經依賴自己的智慧和膽識走過了這一段悲慘而艱難的歲月。
作品中的大勇是一個混跡于美國社會,身材彪悍、惡事做盡卻在內心深處對回歸傳統田園生活始終抱有期待的中國男子。他相信妻子的懷抱就是他的歸宿,相信“妻子還在那邊,推磨、繡花的等他”。然而造化弄人,他擁有的最后一個妓女扶桑,就是本應在鄉間等他回家的妻子。他們不約而同地來到不同文明的領地卻身不由己,為了生存一個背著一身血債,一個卑微且備受凌辱,只能看著自己的癡想和期待一個個破滅。大勇最后因維護扶桑的尊嚴而與美國商人爭執被送上法場,也又一次讓扶桑收獲名利,為她留下開啟自由生活的資本。二人的悲劇也象征著近代中國社會中,傳統男耕女織的小農生活在西方文明被碰撞得支離破碎。為大勇送行的隆重婚禮既是為了滿足大勇最后的心愿,又傳達出經歷過戰火的中國百姓對傳統生活方式向往之心的埋葬。
老子在《周訓》中所言:“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扶桑的大智若愚也是近代中國忍辱負重的智慧縮影,是用智慧與堅強熔鑄的民族精神的獨特表現。隨著世界歷史的推進發展,近代中國告別了帶有江湖色彩的英雄好漢時代,在惋惜遺憾與迷茫興奮的情緒中重新選擇未來的道路,但從血泊中活下來的中國從此也是自由的、光明的。苦難所錘煉的品格進一步豐富了中國的民族精神,為后世的發展提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
參考文獻:
[1]嚴歌苓.扶桑[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32,156.
[2]宋雅.論嚴歌苓小說中的邊緣女性形象[D].河北:河北師范大學,2017,36,37.
[3]李燕.跨文化視野下的嚴歌苓小說研究[D].廣東:暨南大學,2008,75.
作者簡介:張婉榮(1995-),女,漢族,安徽省淮北市,研究生在讀,新疆師范大學,研究方向:文藝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