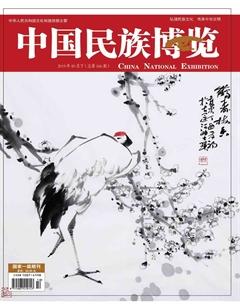趙丹——用生命現實譜寫民族詩意
【摘要】趙丹被稱為新中國影壇“五大天皇巨星”,抑或是新中國“22大電影明星”之一。更多人關注的是趙丹留下的難以復制的成功塑造的人物影響,但是很多人忽略了趙丹對于表演本身的執念。趙丹一生都渴望建立與“三大表演流”的“詩意”現實主義表演體系,雖然這一流派并沒有傳芳后世,但是這種表演方式可謂是空前絕后。
【關鍵詞】趙丹;“詩意”現實主義
【中圖分類號】J605 【文獻標識碼】A
20世紀30年代,隨著各種藝術思潮的涌入和興起,中國電影藝術在這種強勁的風潮下受到了強大的推力,蓬勃之際應運而生,形成了全民觀影的時代,此時中國的電影明星也在方興未艾的文化激流中,依托于他們出神入化的演技獨占了中國電影史中最輝煌的風騷。趙丹正是這一時期脫穎而出的表演藝術家之一,趙丹熱情澎湃、獨樹一幟的表演風格塑造了眾多性格鮮明、反映實時且不矯揉造作的影視及話劇人物。《趙丹傳》的作者倪振良說,他采訪了白楊、張瑞芳等等藝術者,總共收集了百萬字有關趙丹的資料,而這其中有一半以上強烈地透露著趙丹縈繞一生的夢想——建立屬于自己的“趙氏”表演體系與流派——“詩意”現實主義。然而,趙丹所渴望建立的體系與流派似乎如同滄海中的明珠,難以尋覓。
一、“詩意”現實主義
(一)自發性的現實主義
一個具有疑問精神的哲學家,想通過縝密的邏輯和難以推翻的結論達到普世的思考和借鑒,這似乎如同一個偉大戲劇者,他們欲創立自己的主義與體系,希望后人能夠按照他的既定公約進行排演,而趙丹就是這樣的一位戲劇者,他希望建立屬于自己的“詩意”現實主義,然而這并沒有實現,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趙丹在進行戲劇創作中依托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體驗派表演方式結合中國民族元素的風格,雖然沒有實現后世的代代傳香,但是這種表演方式可謂是空前絕后。這種風格的創立也經歷了幾個階段:
早起趙丹參與的左翼戲劇,多以宣傳主旋律題材為主,人物過于類型化,而且此時的戲劇多借鑒戲曲,程式化和模仿成分過重。隨后趙丹進入影壇,出演了《琵琶春怨》《啼笑因緣》等,初入影壇依然是以舞臺表演為重要依托。當趙丹排演《玩偶之家》時遇到瓶頸,在困頓時接觸到斯坦尼,斯坦尼表演體系成為趙丹表演中的一盞明燈,它與趙丹自發性的現實主義表現風格極為貼切,他意識到塑造人物要從生活出發,相信一切所做都是合理的,這也為后期趙丹的“詩意”現實主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35年拍攝的《十字街頭》和《馬路天使》,趙丹飾演的老趙和小陳,趙丹對角色進行反復的思考與揣度,盡量從生活中去找尋表演依據,在朦朧探索中趙丹用自己的靈魂觸角去碰及角色的內心世界,雖然表演略顯青澀也談不上什么高深的演技,但是趙丹憑借最深刻的體驗與真實的表現賦予了角色真實質感。在今天看來,這種現實主義的體驗與表現更多來源于演員的自發性,也正是這種樸實體現出角色潛在的戲劇美學和文化價值。與其說趙丹選擇了現實主義,不如說現實主義選擇了中國。
經歷了抗日戰爭的現實沖擊,提高了趙丹對現實的通透的把控,他成功塑造了《烏鴉與麻雀》中的“小廣播”,表演風格上比較徹底地超越了前一階段的樸素與本色,向著現實主義邁進,不僅僅再是人物的模仿與再現,而是更多地將對生命的感悟和社會的認知自覺銘刻進了角色靈魂。
(二)“詩意”現實主義的確立
20世紀50年代,趙丹最終形成了帶有詩意色彩的現實主義表演風格,更通俗的理解則為趙丹把其他相關的藝術在表演中進行了有機的結合,更加體現出中國藝術的意境所在。其中三部最帶有典型性的影片分別為《李時珍》《林則徐》《聶耳》。
《李時珍》成為逐步確立“趙氏”表演體系的開山之作。李時珍從青年到老年,從幻想的破滅到理想的實現。他的一生在逆水中行進,但逆流、惡浪、漩渦并不相同,隨著李時珍年齡、知識和經歷的增長,他的性格、外形與內心都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年輕時的李時珍初生牛犢不怕虎,趙丹將年輕的李時珍不分場合、不分對象、棱角分明、直來直去的斗爭方式刻畫得活眼活現,并且在表演中加入了戲曲舞臺程式化表演,借助老生的身段甚至是服裝來捕捉具體人物的特征,使得此人物靈動飄逸又深沉含蓄。
在《聶耳》中,趙丹最求自然,人物棱角分明,“愛”與“憎”建立起人物的多面性,有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在《林則徐》中,他在影片的首次亮相中就運用了京劇中“上場風”的嘗試,以一種搖曳的步伐和舞蹈化的身段姿態來刻畫人物的瀟灑自在。當得知自己被委任為御名欽差后,附上了這樣一句臺詞“臣——領旨——謝恩!”簡單的五個字,用陰陽頓挫將其錯落有致地進行排列,這也是依托于京劇中的念白凸顯出人物的感激、沉重與剛毅。
趙丹前期一直擺脫舞臺表演的程式感,而且力圖還原人物的原貌,但到了20世紀50年代,趙丹卻又將這種假定性與程式性重新帶入到自己的創作手段中,雖然趙丹所想呈現的“詩意”現實主義是過度夸張的,與現實主義的主旨也有所偏離,但他所建立或者運用的元素都建立在人物的邏輯基礎之上,而且又符合當時中國的已有審美,所以這是在建立現實主義基礎之上更具有中國藝術傳統神韻的表達。趙丹在表演中孜孜地摸索,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希望能夠建立屬于自己的表演體系與學派。趙丹想要建立的“詩意”現實主義更像是特定時代下的產物,雖然與現在的審美有所出入,但是趙丹獨創的表演風格獨樹一幟,乃是中國近代表演歷史中不可獲缺的組成部分。
二、斯坦尼表演體系對趙丹表現風格的影響
20世紀30年代的早期話劇創作隨已從“文明戲”逐步轉向有文本的中國話劇,但是對于角色的創作依舊是“瞎貓碰見死耗子”,創作人物沒有方法更不成體系。對于趙丹而言,人物的創造僅僅是憑借多年的登臺經驗以及天資作為創作支點,而且前期進行創作的人物多為主旋律類型人物,表現遠遠超越了體驗。而當接觸到來自于西方現實主義大師易卜生的《娜拉》時,趙丹的創作則遇到了瓶頸。
趙丹所扮演的海爾茂臉,因為受到文明戲的類型化表演方式的影響,臉譜化的人物形象極為嚴重。當人物上場之后趙丹所扮演的海爾茂就自動顯露出資本主義厭惡的嘴臉,缺乏人物在戲劇規定情景中的人物內核和行動主線,人物看上去是缺乏層次的。這樣的人物是無法形成“場上之曲”,據著名的話劇導演以及電影教育家章泯回憶到,在接觸到西方劇本的時候趙丹出現了很多創作問題,因為西方的戲劇對于當時的中國演員來說是一個挑戰。《趙丹傳》的作者倪振良說,當趙丹創作無果時,章泯引用了斯蘭尼斯拉夫斯基的話引到了迷茫中的趙丹,斯坦尼說:“在舞臺上,不可能用一套千篇一律的刻板的公式、舞臺臉譜和角色類型來表現先進的蘇維埃人。”
斯坦尼的話,一語點醒夢中人,使趙丹意識到創作人物必須要從生活出發,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極為合理的。趙丹自此發現了斯坦尼表演體系的重要性,并產生了極大的學習興趣。
當走入新疆魔窟時,趙丹依然強烈地抱有希冀——去莫斯科學習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體系,但這一切都似乎成為了徒勞。五年之后逃脫牢籠,相繼拍攝了《遙遠的愛》《幸福狂想曲》和《麗人行》,可以說此時的趙丹已經具備了較高的表演理論素養,對現實有了超越他人通透的把握,使他的表演邁向了更高的境界。在進行《林則徐》和《李時珍》的創作時,雖大量加入了舞蹈性的身段和適當的夸張,但是創作的真切體驗依然沒有離開斯坦尼創作體系,但是如果單純地從斯坦尼體系的角度看,這無疑是一種過分的表演,甚至是劍走偏鋒,在進行狀態的表演,但是由于它是建立在人物內心情境之上的,而且又符合中國觀眾的審美,再加上表現題材多為歷史劇,這種表演形式反而會建立一定的疏離感,感受作品所帶來的超脫。
三、美術素養與表演藝術的關系
對于擁有極高造詣的藝術者而言,他的藝術積淀成為了捍衛其精神思想的重要基石。兒時的拳術,30年后被趙丹運用到了《林則徐》中;孩時的“咿咿呀呀”,成為塑造人物的重要依托。對于趙丹而言,他在演繹事業中創造的輝煌已足斐然,同時他在美術領域也有所建樹,也正是由于與美術結緣,才開始了趙丹的藝術生涯。
(一)與藝相識,緣于美術
13歲的趙丹已能書畫佳作,16歲考入上海美專國畫系,師從繪畫大師黃賓虹,有著極深的美術造詣。
中國畫中講究“六法論”,此為中國人物畫的六項標準,趙丹也將其準則和表演進行了融合:無論是歷史人物還是當代人物,無論是歷史梟雄還是無名卒輩,他都能夠在人物的姿態、表情及行動中凸顯人物的精神和志趣,如同顧愷之所言“內在性情外在化”,而這種外在是真實且具有生命力的,謂“氣韻生動”;每一個鮮活的人物都在于抽離的人物個體,所以其體態與表情截然不同,趙丹通過對人物準確性與力量感的把控,細致勾勒人物,人物保有張力且具有時代力量,謂“骨法用筆”;自亞里士多德的《詩經》起,“臨摹”與“模擬”成為了表演中恒定不變的主題,趙丹將人物形成于本我,表現于自我,達到“第一自我”與“第二自我”的高度契合,所謂“應物象形”;人物色彩豐富,可用筆墨揮灑,可用筆尖勾勒,所謂“隨類賦彩”;人物構思獨具匠心,立于世事創于才思,所謂“位置經營”;模仿基礎之上進行人物再度創作,真實再現,詩意升華,所謂“傳移模寫”。
(二)美術與影視作品的融合
趙丹從小飽受傳統文化的熏陶,使他對中國文化中的“意境”有著濃郁的感知力,在趙丹的后期作品中也能瞥見其美術素養所帶來的美學效力。《李時珍》中運用“大寫意”的繪畫風格,也如同山水畫中的沒骨山水,沒有明顯的骨架,卻在揮灑中凸顯著客體的立體與多面。《李時珍》的塑造或濃或淡,或掃或揮,應手隨意,掂筆即出,不追求過分的人物細節,不吹毛求疵人物的工整,而是一種精神的表現和意趣的表達。塑造的人物靈動飄逸又深沉含蓄,古樸內斂且有深沉之氣,有力地推動劇中人物深入人心。《聶耳》則是工筆畫,層次分明,脈絡清晰,將其細致地刻畫與描繪,與“大寫意”恰恰相反。
通過對趙丹作品的深刻解析及對其生平了解后,不難發現,美術與表演相差甚遠,但它們之間不是存在著一條難以跨越的鴻溝。在趙丹的創作中,美術給予舞臺以生動,而舞臺則給予美術以沉淀,趙丹也曾經說過:“繪畫與電影藝術相通,有異曲同工之妙。繪畫講求意境,講求精神,虛虛實實,追求高尚的品味。演戲借鑒繪畫藝術可以提高藝術素養,對表演大有益處。”
趙丹的一生多舛起伏,或綺麗或暗淡,或失意或開朗,這構成了他完整的一生。作為一名藝術家,趙丹對藝術的追求總是那么執著,那么迷戀,直到他病情惡化時,他依然牽掛著電影《一盤沒有下完的棋》的拍攝。趙丹在病床上寫下了《管得太具體 文藝沒希望》的文章,這是他用他堅強的毅力和風險的精神寫出來的,他將赤誠的心毫無保留地獻給了藝術,為藝術發展點亮了自己微小的光芒。趙丹說過一句話:“一個藝術家,無論什么時候,都應該給人以真、以美、以幸福!”他做到了。
作者簡介:馮華(1992-),男,山東省濟南市人,研究方向:演劇藝術研究、傳媒與公共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