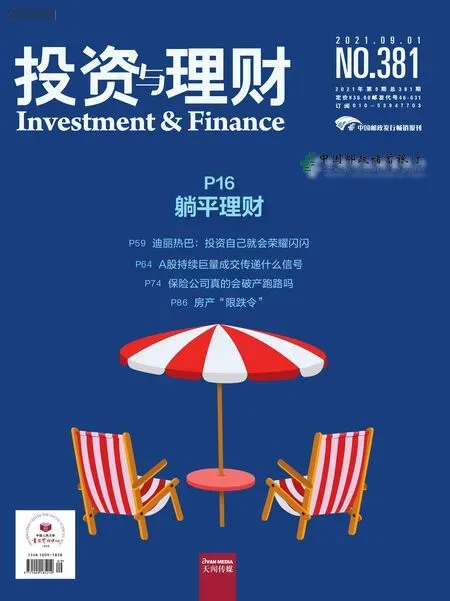避險組合三劍客之美元 人民幣破7后的避險工具:美元
和廣

談到美元和外匯,實際上是投資中間最頂尖、最難做的。為什么還要叫做避險工具?說外匯最難做,是因為真正的大宗外匯交易,都是加了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杠桿,千分之幾的擾動都會帶來資產的大幅波動。也正是因為大量的杠桿資金,24小時不停在全球外匯市場套利,才使得整個外匯市場趨于一致。那么對普通投資者來說,一定不要加杠桿做外匯投資,只要進行配置就好,做一個較長階段的持有。
近期,人民幣外匯破7,美元走強,是不是預示著人民幣兌美元的貶值周期到來?回答這個問題,筆者首先想簡明扼要地說明,決定一國貨幣外匯市場價格的因素有哪些。概言之,一個國家主權貨幣的強弱,長期看GDP增長,中期看貿易,短期看政策。
現在人民幣破7,很多人緊張了。其實,從筆者1990年代讀書期間,剛開始接觸美元時候,“7”真的不算什么。1995年前后,那個時候“外匯券”剛剛退出歷史舞臺,官方的美元牌價大約在8.4左右,這個牌價是不能隨便換的,當時的黑市價格大約10。當時要申請外國學校或者出國讀書的同學,需要從各種渠道買美元,所以知道有個自由市場價格。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為7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美元快速貶值,突破7之后,一度貶值到6.3附近,當時中國仍然保持住了高速增長。所以,從歷史更長的時間來看,主權貨幣的內在價值是這個國家GDP增長決定的。
當前情況與2008年“7”的變化方向正好相反,美國擺脫了10年前金融危機的陰影,近幾年GDP穩步增長,特別是就業率保持高水平;而中國這邊,受制于包括債務等多重因素,增長的速度大幅放緩。2004年,當時人民幣匯率為8.1左右。筆者的碩士論文是在杰弗瑞·弗蘭克(《美國90年代的經濟政策》一書作者)指導下完成,當時采用一個經濟學模型,采用回歸方法,預測結果是如果按照當時的GDP增速,人民幣應該溫和升值15%,也就是大約7左右。實際上到2007年,中國強勁的增長進一步推動了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態勢,達到了7.5左右。我一直覺得這個模型應該經得住考驗,因此大約兩年前,人民幣貶值的壓力越來越大,當時測算7應該是重要的關口位置,不會突破,但的確會從6.6開始貶值。近兩年,7的關口壓力越來越大,特別是特朗普開啟的中美貿易戰日趨緊張。這就聯系到了外匯的中期因素:貿易。
影響外匯的中期因素貿易,很好理解。一個國家持續順差,對外出口超過進口,則對本國貨幣的需求會越來越大,從而本幣升值;反之持續逆差,進口需求大于出口,則對外幣的需求變大。在正常的經濟發展模式下,匯率是調節貿易水平的工具之一。中國對美國,始終保持著順差,所以疊加快速增長的GDP,也就是長期因素疊加中期因素,人民幣兌美元此前十幾年呈長期升值狀態,直到6.20左右的水平。隨之而來的是,美國經濟恢復,與中國增速放緩的對比,以及試圖以關稅削弱對華貿易順差的特朗普貿易戰。從這點看,長期因素和中期因素是個轉折性改變,至少在中國恢復增長以及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基調之前,人民幣貶值的中期趨勢基本確立。美元,就成為國內投資者對抗人民幣貶值的一個避險品種。我們用同樣的觀點再去看其他貨幣兌美元,就會發現,英鎊因為脫歐、歐元因為經濟、加元因為石油價格下跌等等,兌美元都處于不利地位;而日元算一枝獨秀,因為經濟的穩步增長,其長期趨勢上下波動受經濟增長因素干擾更為明顯。
再看一下短期政策因素。短期政策因素對匯率干擾最大的是利率政策。提高利率意味著提升本幣的價格(使用成本),在對手貨幣沒有動作的情況下,短期會助推本幣升值。美聯儲從2015年到2018年持續加息的政策,對美元升值起到了這種助推作用。那么,進入今年后,美聯儲采取了降息措施,為什么人民幣仍然破七了。如前所述,匯率是長期、中期、短期因素疊加,長期因素是長達幾年的趨勢,中期因素是幾個月到一年的階段性波動,而短期因素只是幾天到幾周的擾動,所以美聯儲降息形成了短期擾動。另外是因為此次美聯儲降息并非基于刺激經濟,而是緩解美國股市的下行壓力。
2015年以來人民幣匯率月度變化(2015.12-2019.8)

概括說來,從長中短因素來看,相對人民幣,美元成為組合多元化進行很好避險的三劍客之一(上期講到黃金)。投資者的疑問是,在當前對資金管控非常嚴格的情況下,如何做到美元分散風險呢?首先,個人換匯的額度為每年5萬美元,家庭可以達到10萬美元以上,這是一個途徑。其次,一些較為穩定的美國股市指數基金,例如標準普爾500(納斯達克不如標普500穩定)可以成為投資標的。國內很多基金公司發行了這種人民幣計價、在國內申購贖回和交易的開放式基金,人民幣購買經過匯率折算,即使指數沒有升值,也會因為美元升值而受益。未來何時美元兌人民幣達到階段性頂部,回到影響因素方面,體現在中國經濟穩定的、有質量的增長,中美貿易戰結束,貿易達到一個相對平衡的區域,人民幣降息的寬松周期結束。這些目標想要實現,還需要假以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