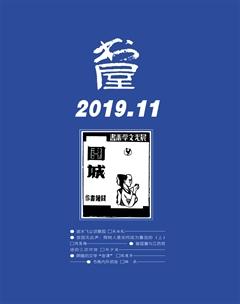清泉冷月映古今
劉少勤
一
說起來叫人難以置信,有的音樂大師看不懂樂譜,更不會寫譜。比如美國樂圣邁克爾·杰克遜,樂思泉涌,卻沒有能力拿起筆來寫下曲子。幸好現代科技幫了他的忙,他每當靈感來了,想要作曲,立刻跑到錄音機前,按下錄音鍵,打開嗓門盡情唱。美妙的旋律留在了錄音帶里,專業作曲家再照著他的錄音寫成曲譜,邁克爾·杰克遜以這種方式向世人奉獻了眾多金曲。
阿炳也不識譜,不會寫譜,對現代樂理一無所知。這位大師憑借過人的天賦,直接在二胡和琵琶等樂器上傾瀉滔滔汩汩、綿綿不盡的樂思。阿炳會的曲子很多,據他友人介紹,有一百多首。可惜他不會記譜,又沒有錄音設備,人亡曲盡,大部分樂曲被他帶進了另一個世界,我們再也聽不到了。所幸,1950年,中央音樂學院楊蔭瀏教授提著簡陋的舊式錄音機,和友人一起找到阿炳,請他錄音,錄下了六首曲子(三首二胡曲,三首琵琶曲),其中最受歡迎的就是《二泉映月》。
錄音時,阿炳已經兩年沒碰過琴,身邊連一把二胡都沒有。兩年前,老鼠咬破了他的二胡,阿炳覺得是上天在告誡他,懲罰他。他心里一直有個疙瘩。他原本是道教的樂師,彈琵琶,吹簫,拉二胡,會很多樂器。依照教規,他只能演奏道樂,不然會有報應。道樂清虛、空靈,少了一點世俗的情調,阿炳不滿足,廣泛涉獵俗樂,包括地方戲曲。他惶惶不安,覺得是自己違背了教規,罪孽深重,才有了眼前的報應。再拉奏俗樂,將來可能會有更大的報應,于是干脆告別二胡了事。好友黎松壽一再勸說,他才同意錄音。沒有二胡,黎松壽幫他借了一把。別說兩年,一個月不拉琴,手就生了。楊蔭瀏先生說沒關系,先讓他練幾天再錄。畢竟功力深厚,把玩了幾天,遛遛手指,兩年來僵硬的手指很快又活過來了。錄音很順利,一遍過。錄完了,聽錄音,阿炳很吃驚。以前可從沒有見識過這種新的技術,他伸出拇指,夸楊蔭瀏先生是神仙。三個月后,阿炳去世。好險吶,曠世稀有的神曲差點兒就沒了。
樂曲起先沒有名字,阿炳憑靈感和直覺隨意拉奏。他眼瞎了,由妻子牽著穿街走巷,每天拉響這首曲子,無錫當地居民正要關門歇息,于是人們管它叫“關門曲”。
楊蔭瀏先生自然不能接受這個曲名,要阿炳另取。阿炳一時無語。楊先生循循善誘,問他經常在什么地方拉曲,他答“二泉”(無錫一處景點)。楊先生的話叫他心有所悟,他沉吟片刻,說就叫《二泉印月》吧。楊先生覺得這名好是好,只是廣東音樂有一首叫《三潭印月》,“印月”重復不妥,不如換成“映月”。阿炳點頭,美妙的樂曲就有了富有詩意的名字。楊先生后來根據錄音,用樂譜忠實地記錄下來,為人們的演奏提供了準確可靠的參照。今天阿炳家喻戶曉,楊蔭瀏先生卻很少被人談起,有點不公。
阿炳了不起,楊先生也非等閑之輩。楊家是書香門第,出了許多名人。姐姐楊蔭榆是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校長,與魯迅有過沖突。侄女楊絳,翻譯家、作家,是錢鍾書的夫人。楊蔭瀏本人音樂造詣很高,是作曲家、琵琶演奏家,文學修養也好。他的開山之作《中國音樂史》厚厚兩冊,時間跨度大,材料搜羅廣,論斷謹嚴,文筆通暢。眼下坊間充斥著各種各樣的中國音樂史,我做過比對,不過是楊氏專著的翻版,除了個別材料的補充外鮮有獨創。
二
一千個演奏家,一千種《二泉映月》。音樂的內涵比文學更復雜,從作曲家到演奏家再到聽眾,經過三級傳遞變數更大。聽眾的反應暫且不去說它,《二泉映月》在不同演奏家的手下變化萬千,足以叫人驚嘆。海內外發行的《二泉映月》版本不知其數,我收藏的就有五十多種。甚至同一個演奏家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錄制的版本也相去甚遠。
歌曲有歌詞的提示,音樂的意義被框住了。純樂曲,給演奏家的發揮留下了最大的空間。每個演奏家都用自己的心靈詮釋《二泉映月》。
張銳先生的演奏照著原譜,不刪不減,運弓蒼勁,節奏偏快,有阿炳的風骨。但是過于強調旋律的重音,有很多的“力點”,少了一點水鄉的柔情。
著名二胡演奏家、教育家王國潼先生感到阿炳原曲重復太多,有點累贅,把六個樂段中多余的去掉,保留四個樂段,讓全曲通貫,一氣呵成。后來的演奏家大多數用這個改編版,《二泉映月》的廣泛傳播有王先生的功勞。王先生本人的演奏中規中矩,不慍不躁,節制,內斂,勻速,典型的學院派風格,似乎少了一點激情。
《二泉映月》原本用低音二胡演奏,比正常的二胡低五度。因為音調低沉,到了六拍子的顫弓部分,聲音模糊,許多演奏者舞臺表演時靠揚琴伴奏來遮短。“二胡皇后”閔惠芬女士拉奏《二泉映月》,把音調提高了兩度,音色變得通透、明亮、圓潤,顫音部分一下子有了“珠玉蹦跳”的效果。閔惠芬女士的版本在海內外深得好評。
周維先生是出色的二胡演奏家,技巧嫻熟,手上的功夫了得。但他拉的《二泉映月》卻并不是很成功。演奏光有出色的技巧不行,還有生命的頻率能不能對接的問題。假設《二泉映月》的頻率是七十三點五兆赫,周先生的頻率則是二百八十九點七兆赫,兩者差得很遠,沒有共鳴,沒有交集。周先生常用大滿弓,很有力量,很有氣勢,音色飽滿、華麗,情感濃烈,斷句如刀,干凈利落。可是,旋律推進沒有層次的變化,少了一點回環曲折,也少了靈魂深處的樸質、滄桑和堅忍。他好像把《二泉映月》拉成了一朵鮮艷怒放的玫瑰,熟透了,就要凋謝,所以華麗中還透著一點悲涼。我不是否定周先生的音樂成就,他碩果累累,拉過許多曲子,都很出色。即使是頂級的大師,往往也只能演奏與自己的生命氣息投合的曲子,而對于某些類型的曲子,縱有萬般技巧,也使不上勁。這是生命的秘密。
當紅二胡演奏家宋飛長時間揣摩《二泉映月》,她的演奏自成一格。她注重景和情的平衡。《二泉映月》寫景也抒情:一面是微風輕拂,月華千里,溪水潺潺,花朵幽香陣陣,一片江南的美麗風光。一面是在美景中行走的人嘆息連連,“我心憂傷”。《二泉映月》有許多重音,那是樂曲的“力點”。同時,它又有柔美綿長的旋律“線條”。有的演奏者只顧“力點”,拉得很有勁,柔美的神韻盡失。另一些演奏者卻只顧旋律“線條”的流暢,“蒼勁”的風味全無。
該說說阿炳本人的演奏了。阿炳百年誕辰,國內一家唱片公司發行了阿炳本人錄音版,總共出了五百張CD,我買了一張。為何阿炳本人演奏的版本不能在聽眾中廣泛傳播?我想,有多方面的原因。阿炳錄音時貧病交加,離生命終結只有幾個月,聽力下降,加上已經兩年沒有拉琴,左手的指觸和右手的運弓都不如從前,能順暢地錄音已是萬幸。用舊式七十二轉錄音機錄制,音效不理想。
阿炳是民間藝人,平常為生計奔波,掛著琴,拖著疲憊的腳步邊走邊拉,沒有心思也沒有條件打磨細節。民間音樂包括民歌,天然地帶著原始的粗糙,需要后來者加工。今天舞臺上傳唱的各種民歌,都經過了專業音樂家的藝術處理。
也有人說只有阿炳本人的演奏原汁原味,最有價值,后來無數演奏家的努力在他看來一文不值。這是典型的外行之見。我懷疑他沒有認真聽過阿炳的錄音。藝術批評容易犯兩種錯誤:一是“民粹主義”,神化民間藝術,好像民間的東西就完美得不得了。二是“原教旨主義”,過分強調原汁原味,好像作曲家本人的演奏一定比后來者要好。肖邦是偉大的鋼琴作曲家,也是卓越的鋼琴演奏家。他公開承認,他的曲子,李斯特彈得更好。
優秀的樂曲“內存”豐富,含蘊無限,經得起無數演奏家反復詮釋,也呼喚各路演奏家深挖細掘,把埋在樂曲深處的寶藏、意義和隱微開發出來,讓樂曲立體地綻放,多面地呈現。
三
二胡原先地位不高,主要用于戲劇的伴奏。琴師拉奏時左手按弦只用一個把位,手指固定在上方,不作上下移位,通常只拉八個音。音位不夠,便用低音代高音或高音代低音,行話叫“低翻高,高翻低”。右手拉弓,手法單一,很少有弓法的變化。阿炳極大地拓展了二胡的音區。拉《二泉映月》時,他的手指在兩根弦上自如地上下游走,往來穿梭,跨越低音區、中音區、高音區和超高音區,差不多用盡了琴弦上的所有音位。西洋小提琴四根弦,音域寬,共四點五個八度。二胡經過阿炳的妙手,也有了三點五個八度,只比小提琴少了一個八度。阿炳運弓,弓法多樣,短長弓的交替,波弓和大段的顫弓的應用,讓人耳目一新。
阿炳提升了二胡的表現力,給二胡帶來了榮耀和尊嚴,改變了二胡只能充當伴奏的境遇,讓二胡挺起腰桿成為獨奏樂器。從此,看起來簡單的兩條弦不再簡單。內弦和外弦,是天和地,是陰和陽,是老和少,是男人和女人,是你和我,是得和失,是晴和雨,是歡樂和憂傷。人世間的各種酸甜苦辣,各種興衰際遇,都能在兩根弦上拉過來推過去,咿咿呀呀,從春到夏,從秋到冬,拉出了萬家燈火。
音樂直入心魂。不需要翻譯,《二泉映月》早已在世界各地不同膚色人群的靈腑中拉響,為無數人聆聽和喜愛。世界級交響樂指揮大師小澤征爾一生沉浸在西洋音樂中,第一次聽閔惠芬女士拉《二泉映月》,一下子被震到了,感慨這樣的音樂應跪著聽才是。后來他還念念不忘,說西洋音樂有很悲的,但不美;有很美的,但不悲。《二泉映月》是在美中悲,在悲中美,美悲無間,真真神奇。還是這位小澤征爾先生,聽閔惠芬女士拉另一首二胡曲《江河水》,當場躺倒在地,不肯起來。身邊人員將他扶起,他說“這是東方的《命運交響曲》”。二胡的魅力再次在交響樂指揮大師身上得到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