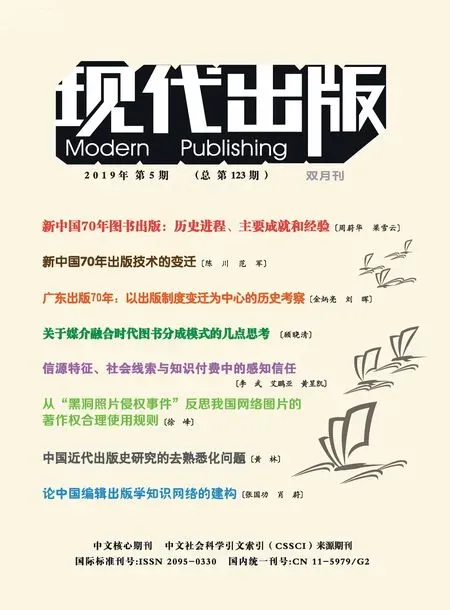中國近代出版史研究的去熟悉化問題
◎ 黃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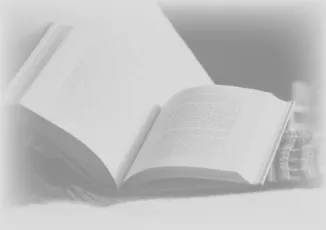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近代史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表征之一就是,作為對傳統政治、經濟、軍事史的一種反動,人們對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產生了濃厚興趣,從而為中國近代史研究開一生面。
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中國近代出版史研究一改過去的冷清場面,迎來了自己的輝煌時期,進入了發展快車道。其一,研究隊伍逐步壯大。現在的出版史研究,不再是行業內少數精英分子的自說自話,取而代之的是歷史學、新聞傳播學等學科領域的學者紛紛加盟其中,一時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其二,研究成果盛況空前。四十余年來,無論是全國性的綜合出版史料,還是地方性出版史料,無論是通史類研究著作,抑或專題性研究成果,可以稱得上是汗牛充棟,并填補了中國近代出版史研究領域的諸多空白。
可是,在這熱鬧喧囂的背后,也不無隱憂的存在。例如:有關中國近代出版史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及敘事模式等方面,與中國近代史研究高度趨同,缺少學科特色;因為論題單一、題材雷同,研究成果大都千人一面,了無新意;對中國近代出版史研究領域中一些最基本的問題,幾乎沒有展開爭鳴和討論,共識不多;等等。其中,研究方法和敘事模式的陳陳相因,更是成為中國近代出版史研究走向深入的一大障礙,存在“去熟悉化”,亟需推動“去熟悉化”以提升研究興趣。
一、日漸固化的研究范式與敘述模式
在中國近代出版史研究中,至少存在“后見之明”、結果預設、刻板印象等三種學界慣用的研究范式和敘事模式。以下分別述之。
1.“后見之明”
“后見之明”的出現,與考察歷史的順序相關。
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克提出,“如果認為,史學家考察歷史的順序必須與事件發生的先后完全吻合,那真是個極大的錯誤。雖然,他們事后會按歷史發展的實際方向敘述歷史,但在一開始,卻往往如麥特蘭所言是‘倒溯歷史’的,這樣更為便利”。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相對而言,時代愈近,事情就愈清晰”。“在歷史學家審閱的所有畫面中,只有最后一幅才是清晰可辨的。為了重構已消逝的景象,他就應該從已知的景象著手,由今及古地伸出掘土機的鏟子。”
這種“由今及古”的歷史考察方法,讓研究者處在天然的“后見之明”的優越地位,使其了然歷史發展結果,熟知歷史發展脈絡,從而可以發現當事人未能注意到的許多重要事件及細節。使用這一手法,他們可以編撰出邏輯嚴謹、條理清晰、層次分明的歷史文本。其不足之處是會忽略看上去與結果關系不大的一些枝節,損害歷史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還常常會不自覺地用現在的價值尺度去評判前人,以今情度古意。
在中國近代出版史的研究中,大家使用得最為嫻熟的考察及敘述方法,就是這種從最清晰、最熟悉的研究對象入手的“倒溯歷史”法。一談到近代出版機構,研究者就會習慣性地想到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開明書局等少數幾家出版巨頭;一論及出版人物,其研究視野總出不了張元濟、王云五、陸費逵、鄒韜奮等幾個人的圈子。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這些出版機構經受住了歷史和市場的嚴峻考驗,最終存活了下來,成了殘酷競爭中的勝利者。人以社存,這些出版機構的主事者,也自然在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留下了自己應有的印記。它們或他們就成了歷史學家眼中“已知的景象”和“最后一幅”“清晰可辨”的“畫面”。
以這些活化石為依托來重構這一段歷史,對于中國近代出版史學者來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但遺憾的是,我們在書寫勝利者歷史的同時,往往遺忘了曾經的同臺競爭者。例如,商務印書館最初成立的時候,它只是一個印刷機構。這從它的企業名稱可以看得出來。在辛亥革命之前,與商務印書館處在同一起跑線上的出版機構還有不少,諸如文明書局、有正書局、彪蒙書室、廣智書局之類。但在充滿“后見之明”的研究者那里,進入視野的只能是最終的勝利者,文明書局等作為“分岔的歷史”則被無情排除了。
“后見之明”不僅體現在歷史的敘述中,也深刻影響著歷史的評價。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張元濟作為商務印書館主持人,曾經拒絕出版孫中山的《孫文學說》。張元濟的解釋是言論出版不自由,官吏專制太甚,商人不敢與抗,并非反對孫君。有人就說,張元濟的這套說辭多少有些推諉,以致惹惱了孫中山。孫甚至指責商務印書館已被封建余孽所把持。但凡從事過出版工作的人都知道,出版有著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體現政黨和國家意志,是有禁區的。必須確保出版安全,才能談得到其他。如果就此指責作為出版商人的張元濟,那就有苛責古人的嫌疑了。我想,如果張元濟能夠預知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以后的影響與地位,選擇可能會不一樣。
2.結果預設
對人類歷史發展前景抱持樂觀之態度,是許多歷史學家的共識,哪怕其分屬不同陣營。他們力圖讓人相信,人類的歷史是一步一步向前演進的,后一階段總是比前一階段更為進步,并聲稱,這種演進是受社會發展規律支配,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例如,中國臺灣學者杜維運就曾說:“就大體而言,歷史是在進步之中的,逐漸由草昧幾于文明,即使是躑躅而進,即使像蟹沿圓石而行,不時翻轉。”
與這種歷史發展規律論相呼應,一些中國出版史研究者每每將中國出版業發展的歷史,建構為一個有目的的、有序的、通往某一個終點的不可避免的過程。這一過程,又被相應劃分為幾個不同的階段和時期。1840-1949年這一區間內的中國出版史研究,也不例外。例如:公開出版的各種中國出版史教科書,就基本上沿用中國歷史的分期方法來編排相關內容,分為古代出版、近代出版和現代出版等幾個部分。中國近代出版史教科書,也大體上是按照中國近代史的歷史分期方法來組織內容的。
這種歷史發展規律論,本質上就是一種結果預設理論。這種理論,在面對豐富多樣的原生態近代出版歷史時,往往顯得捉襟見肘,顧此失彼。以上述出版史的歷史分期為例。由于是生搬硬套中國歷史分期法,忽略了出版發展歷史的特殊性,有些研究者甚至對“古代出版”“近代出版”“現代出版”等基本概念都不甚了了。因此,他們編撰出的中國出版史和中國近代出版史著作,與其說是試圖將相應出版歷史構建成一個由古代、近代到現代的層累遞進的發展過程,不如說他們書寫的古代、近代和現代出版史,只是某一歷史時期內出版活動的言說,彼此之間并不存在邏輯聯系和替代關系。
3.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是一個心理學名詞,指的是人們對某一類人或事物產生的比較固定、概括而籠統的看法。它既有簡化認知過程、節省認知成本、迅速做出認知判斷的優勢,又存在以偏概全、忽視個體差異、導致認知錯覺的風險。
在中國近代出版史研究中,就存在著這種現象。例如: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的商務印書館,從一開始就被研究者貼上了如下標簽:這是一家在近代中國做出了巨大貢獻的文化企業,與那個時代的北京大學并稱為近代中國文化的“雙子星座”。在這一巨大光環下,很少有人會去思考該館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以及其他不為人知的另一面。例如,作為一家私營文化企業,商務印書館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引發了頻繁的勞資糾紛,反映出了資本對勞動者剝削的一面。曾為商務印書館學徒和店員的陳云,以及服務于該館編譯所并主編《小說月報》的茅盾,就領導或參與了該館的罷工運動。
中華書局內部勞資雙方之間的斗爭,也長期存在,有時還很激烈。因為“中華書局職工的待遇,除高級職員和主要編輯工資較高外,普通職員的工資是比較低的,可以‘清貧’二字來概括”。例如,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后,該局動員職工回鄉避難,上海總廠也于1938年1月4日正式關閉。不滿被遣散的工人占領廠房,并與書局對簿公堂,堅持斗爭長達九個半月,最終捍衛了自身的權益。
從出版人物研究看,也還存在臉譜化、簡單化的傾向。我們現在都知道,王云五在商務印書館的成長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他是國民黨陣營的人物,又逃到了臺灣,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學界并不能客觀公正地評價他。
二、去熟悉化的進路
要去除中國近代出版史研究中日漸固化的研究范式、敘述模式,達成去熟悉化的目標,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
1.回到馬克·布洛克,消除“后見之明”
馬克·布洛克主張“由今及古”地考察歷史,但他同時也強調“由古知今”考察歷史的重要性,認為“脫離特定的時間,就難以理解任何歷史現象”。這就是說,要“理解任何歷史現象”,研究者都要將事件和人物置于彼時彼地,回到歷史的原點,按照“事件發生的先后”進行考察。這時,映入我們眼簾的,定然是另一番光景:除了那些勝出的媒體、出版機構和出版從業者外,還有無數為勝出者的光芒所遮蔽的競爭者。
那么,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實際的出版生態又如何呢?
如果我們承認中國近代民營出版業產生、發展并逐步取得優勢地位的歷史,就是中國出版業近代化的歷史,那我們就不應忘記西方在華宗教出版和世俗出版的引領帶動之功,也不應忽略官辦書局的探索促動之力。而民營出版業內部不同出版機構之間的相互支持和激烈競爭,更是中國近代民營出版業快速發展的基礎。
以近代中國出版業的中心上海為例,有資深出版人就搜集到的資料和記憶所及,整理出上海一地近六百家近現代出版單位的材料,其中在1900~1911年間存在或創建的出版機構就有一百四十余家。還有人曾統計,僅上海一地,生前對上海出版工作有過貢獻的近現代出版家就有三百多人。
在百舸爭流、千舟競發的背景下,中國近代歷史上任何一家出版機構,都有可能在競爭中勝出,成為行業的標桿;任何一個出版人,都有機會將自己的名字鐫刻在中國近代出版歷史上,成為行業的楷模。反之亦然。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及其創辦人、主事者,當時只是這眾多近代出版機構和出版從業者中的一分子而已。他們或它們并不必然會成為后來我們所熟知的那個樣子。如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后,日軍蓄意炸毀了商務印書館位于上海的總管理處、編譯所、印刷廠、東方圖書館、尚公小學等,商務印書館損失了總資產的80%,被迫暫時停業,解雇全部職工。中華書局的狀況更加危險。民國六年經營危機發生后,它幾乎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甚至曾希望商務印書館接盤。如果商務印書館應對失誤,而中華書局倒閉成為現實,那中國近代出版史又不知會是怎樣一番模樣。
回到馬克·布洛克,從歷史的原點出發,由古及今地考察歷史,我們就能發掘中國近代出版史蘊含的復雜性、豐富性及可能性,消除“后見之明”的弊病。
2.創新研究范式,破解“結果預設”
創新出版史學理論,引入各種不同的研究范式,是破解“結果預設”的最佳解決之道。任何一種史學研究范式,都不可能窮盡歷史的解釋。每一種研究范式,都只是從某一個角度接近真實的歷史,但很多種研究范式得出的成果,則庶幾可以重構或還原真實的歷史。這種真實的歷史,或許就是馬克·布洛克所追求的“總體的歷史”。“唯有總體的歷史,才是真歷史,而只有通過眾人的協作,才能接近真正的歷史。”
以中國歷史學界現有的實力,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仍處在借鑒和模仿西方史學理論的階段,還無法真正建立起自己的本土化解釋體系。中國出版史學界就更不用說了。有學者坦陳:“出版史學的理論建構比較難,出版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也比較難。”相較而言,引進、消化、創新運用各種不同的研究范式,還是切實可行的。革命敘事模式和近代化敘事模式,注重文本的書籍史研究與關注讀者的閱讀史研究,“倒溯歷史”或者是順溯歷史等,這些都是中國近代出版史研究可資借鑒的研究范式。
可喜的是,一些中國出版史研究者已在此領域開始了可貴的探索,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例如:
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就組織團隊,“嘗試寫出不同的報刊或媒介歷史,在范式上有一個根本創新”,即“以媒介為重點,以媒介實踐為敘述進路,報刊不是本質的而是構成式的;要有多樣的視角和分析單元,以實現范式的變更”。
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科學研究中心一班人,則將生活史的理念、方法引入出版史學研究,探討出版從業人員以及與出版關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主要研究出版人的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休閑娛樂等精神生活以及人際交往生活。此舉不僅“有利于促進出版史學領域的拓展與深化,呼應國際出版史學潮流,同時也有助于觀照當前出版轉型中面臨的諸多問題,尤其是出版人才、出版文化建設問題”。
多樣化研究范式的實踐,能夠有效擴大中國近代出版史的研究領域,并促成不同研究范式成果之間對話局面的出現。
3.發掘原始資料,改變“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是出版史料的欠缺,或者是有選擇性地使用出版史料造成的。后者姑置不論,我們更愿意來談一談出版史料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問題。
實事求是地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近代出版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工作所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全國性和地方性的綜合出版史料,以及各種專題出版史料,都相繼面世,品種繁多,空前豐富。但是否可以說,已整理出版的史料,足以保證研究者客觀完整、不帶任何偏見地認識與描述中國近代出版史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其一,已有的出版史料,從結構上說,并非無懈可擊。例如,在革命敘事語境中,蘇區、邊區、解放區的出版史料整理和傳播得到了較多的關注和支持,而國統區、租界,特別是淪陷區,乃至臺灣日據時期的出版史料的整理工作,就明顯滯后,有些幾乎無人關注。雖然情感上難以接受,但后者無疑是中國近代出版史的組成部分,應當本著歷史主義的態度來看待這部分出版史料的整理和傳播。
其二,近代出版史料的搜集整理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一個明顯的例證在于,每當一種新的史學理論和研究范式出現,都會發掘出一批全新的出版史料。例如:中國近代報刊中登載的讀者來信或編讀往來之類的內容,從來都不曾引起出版史研究者的注意,但這些資料在閱讀史研究者眼中,卻是彌足珍貴、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
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在多樣性方面,也存在諸多不均衡之處。如文字史料與書報刊實物史料、檔案史料與口碑史料、中文史料與西文史料的失衡,等等。
只有占有足夠豐富和多樣的出版史料,并正確地使用它,改變“刻板印象”才會成為可能。
總之,推動中國近代出版史研究領域的“去熟悉化”,是促進該領域學術研究進步的必然要求。這一目標的實現,主要仰賴兩種方式:其一是研究范式的借鑒與創新,其二是出版史料的發現與挖掘。而從中國近代出版史研究的現狀來看,研究范式的引入、消化和創新顯得更為迫切和重要。
注釋:
①③康樂,彭明輝.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80,118.
②⑤⑧布洛克.歷史學家的技藝[M].張和聲,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53-54,46,55.
④中華書局編輯部.回憶中華書局[M].北京:中華書局,1987:80.
⑥朱聯保.近現代上海出版業印象記[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
⑦宋原放.出版縱橫[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25.
⑨范軍.深化中國出版史研究之淺見[J].出版參考,2019(3).
⑩黃旦.新報刊(媒介)書寫:范式的變更[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5(12):5-19.
?范軍,歐陽敏.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學研究新視閾[J].現代出版,2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