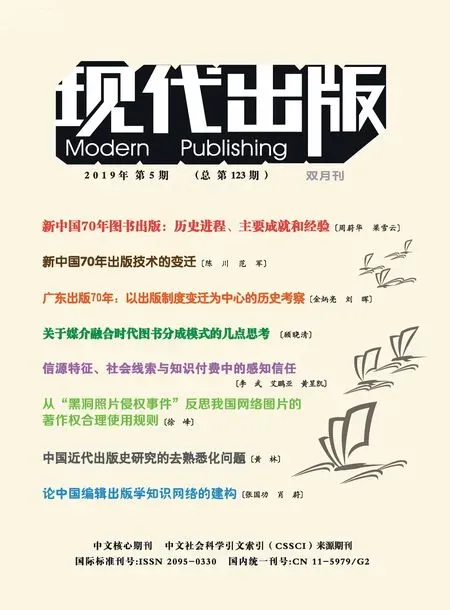《新青年》的科學傳播
◎ 李 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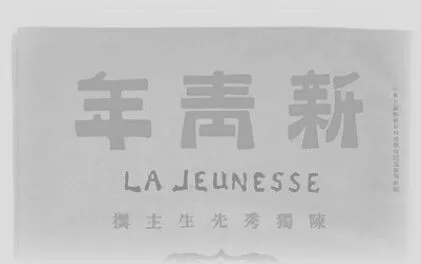
近代意義上的科學技術誕生于西方,中國在開眼看世界時,學習西方科學是題中之義。在西學東漸曲折且悠長的歲月中,五四運動時期中國對西方科學技術的學習和引介可謂是重要一環,其科學傳播涉及內容之豐富、波及范圍之廣闊以及產生效果之深遠在中國科學傳播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筆。《新青年》作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刊物之一,既是這一時期科學傳播事業發展的見證者、記錄者,也是一股突出的力量。
縱觀中國科學傳播史,《新青年》在其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它一方面承接之前的傳播科學活動并迅速將其推向高潮,另一方面其自身的停刊及科學傳播的退場也標志著中國科學傳播運動的階段性終結。此后,科學再也沒有被當作“重頭戲”如此大規模地傳播。“新聞事業,是活的社會事業”,對《新青年》科學傳播的考察和回顧,對當下科學傳播實踐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誰在傳播:科學傳播的主體
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志》于上海創刊,交由群益書社印行,時為月刊,首卷共6號。在創辦之初,雜志便發表社告稱“本志之作,蓋欲與青年諸君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本志以平易之文,說高尚之理。凡學術事情足以發揚青年志趣者,竭力闡述。冀青年諸君于研習科學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
欲通過傳播科學提高民智,《新青年》便需其撰稿群體具有一定的科學知識和科學素養并能夠運用編輯手段,熟練地將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等述之于大眾。據統計,在《新青年》上,直接撰寫專門文章參與科學傳播的作者主要是陳獨秀、王星拱、馬君武、李寅恭、吳敬恒、高一涵、任鴻雋等二十余人。一批志趣相投的知識分子,是一股強大的編輯力量,也是雜志進行科學傳播活動的基礎。
從學歷狀況來看,撰稿群體普遍受教育水平較高,具備一定的科學素養。在直接參與科學傳播的作者中,大部分作者均接受過正規的學校教育且畢業于國內外知名大學,其中王星拱曾獲得碩士學位,胡適、劉半農、陶履恭和馬君武等人擁有博士學位。可見,雜志主要作者均具備較高的學識水平,能夠滿足科學傳播的需要。
從知識結構來看,大多數作者都經歷了由舊學向新學、由中學向西學的轉變過程。辛亥革命后,盡管封建帝制被推翻,但相應的價值信仰和道德倫理體系尚未建立,此時,“政有新政、舊政,學有新學、舊學,道德有所謂新道德、舊道德,甚而至于交際酬應,亦有所謂新儀式、舊儀式。上自國家、下及社會,無事無物,不呈新舊之二象”,這種新與舊、中與西的范式糾纏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反映在《新青年》撰稿群體的受教育經歷上。留學經歷使得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真正開始接受西方科學文化教育,接受科學觀念和科學精神;從中學到西學的巨大轉變,既使當時的知識分子意識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別,意識到社會革命的重要性,也使一大批五四知識分子接受了科學知識的啟蒙以及科學教育的熏陶,為其植入了科學觀念和科學信仰,為后續的科學傳播提供了基礎。
由此可見,《新青年》的科學傳播群體在早年多接受中國傳統教育,但后來大都改為接受西方科學教育且大多都有海外留學經歷;較之前相比,這些人能夠親自觸摸到西方科學的命脈,具有更高的學識水平和科學素養,這種新學與舊學交纏的教育經歷形成了《新青年》科學傳播主體的精神特質。
二、傳播什么:科學傳播的內容
《新青年》創辦的宗旨是立足青年,改造社會,而民主與科學正是其實現自身目的的兩大法寶。自1915年創辦至1926年終刊,雜志共發表文章近六百篇,期間雖歷經多次停刊風波,但是其對科學的關注始終不變,這始終如一的辦刊志向也引導著編輯隊伍的工作實踐。通過對《新青年》在不同階段刊登的科學傳播文章進行統計和分析,可以發現其科學傳播的兩大主線,一是對生物學類、地學類、醫學類等科學知識的介紹,二是對科學觀念、科學方法、科學精神等科學總論的傳播。
1.科學知識類
生物學是一門歷史悠久的自然科學。19世紀初,西方生物學正式脫離博物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并在晚清經由傳教士、譯書等途徑逐漸進入中國。生物學作為自然科學的基礎學科之一,對科學體系的建構和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進入20世紀,這一學科取得了長足發展,《新青年》在進行科學傳播時自然會對其有所關照,其中與進化論有關的文章占比最大。必須提到的是,彼時的進化論已不再被視為一種簡單的科學理論,而更多地成為陳獨秀等人用來觀察、改變、推翻舊社會的理論依據和武器。在雜志創刊號中,陳獨秀就曾將進化論和社會發展聯系起來稱:“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變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煥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權說,一曰生物進化論,一曰社會主義是也。”因此,《新青年》對進化論的傳播主要圍繞兩方面展開:一是將進化論單純地作為一種自然科學知識進行介紹,以開啟民智;另一方面則是將進化論視為破除封建迷信、開展社會革命、改變近代中國舊面貌的依據和武器。
《新青年》在科學傳播中對醫學類知識也有所關注。據統計,《新青年》上刊登的有關醫學傳播的文章主要有五篇,涉及人口與生育、梅特尼廓甫的醫學貢獻以及西醫的體檢和治療等內容。《新青年》所傳播的醫學類內容全部與西醫知識有關且對其表現出積極正面的態度。相比之下,雜志從未刊登專門介紹中醫的文章,但從雜志的邊角文字中能夠看出《新青年》對中醫的態度并不友好。雜志對于中醫的態度實際上反映了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一切“舊”的文化、思想和道德的徹底批判和推翻具有鮮明的反傳統色彩,中醫作為傳統文化中的一部分自然被貼上落后的標簽,因此成為被批判的對象。
地學是對“以我們所生活的地球為研究對象的學科的統稱”。《新青年》對于這一部分科學知識的介紹文章并不多,主要集中在與地質構造、演變和進化等有關的知識上。其實,中國自古以來便有豐富的地學知識,但中國傳統的地學研究大多以記載為基本手段,側重于對地質現象的描述而忽視對客觀規律的把握,始終未形成系統的地學理論。因此,《新青年》對這一科學知識的傳播也主要是以介紹西方學術界生產的概念、學說和理論知識為主。
2.科學總論類
科學總論文章是指與科學觀念、科學方法、科學思想、科學精神等相關的文章,《新青年》在不同階段共發表此類文章二十余篇。總體來看,這些文章以科學為對象,有的討論科學的概念、本質和分類等內容,有的關注具有代表性的科學家和最新研究成果、技術發明,有的對科學的效能和功用以及正確對待科學的態度進行闡釋,有的探討人生觀、迷信等與科學精神相關的問題……體現出《新青年》欲通過科學破除封建迷信的意愿。舊時的中國人始終缺乏一定的科學觀念和科學精神,《新青年》通過科學總論類文章介紹科學成果、普及科學方法、宣傳科學精神,以培養人們樹立正確的科學價值觀念。
《新青年》以青年為目標受眾,始終堅定地進行科學傳播,其中既包含基本的科學知識又容納深刻的科學精神,同時提倡用科學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為普及科學知識,《新青年》介紹了各學科內部的基礎知識和理論并緊緊圍繞這一時期各個學科內部的熱點和前沿;科學傳播者還有意識地將婦女、性欲等社會問題與科學傳播相結合,幫助讀者在現實生活中體會科學的效用。
三、如何傳播:科學傳播的策略
《新青年》在創辦之初,“銷售甚少,連贈送交換在內,期印一千份”,遠遠未達到陳獨秀預想中的效果。隨后,雜志在短時間內銷量劇增,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領跑者,將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傳入中國社會,這與其靈活的傳播策略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1.傳播欄目的全覆蓋
《新青年》自創刊以來便借助一切可能的形式和力量進行科學傳播,除了通過在時政、思想、社會問題等欄目上發表專論文章外,通信和廣告等也是其進行科學傳播活動的主要陣地,實現了科學內容傳播的全欄目覆蓋。
通信欄目是編輯部與讀者溝通的陣地,也是雜志向讀者傳播科學的重要渠道。在《新青年》第1號第6卷中,讀者輝暹來信詢問有關灰塵的危害、手指足趾之爪自行脫落、“異族結婚,后嗣多慧鍵”等問題,編輯部記者則在通信欄中對此一一解答,其中便涉及不少生理學的知識;王星拱在回答讀者來信中也介紹了分子、原子和電子并澄清了放射的概念以及原子分解的原理等化學知識;陳獨秀在回復讀者來信時介紹了實驗法;高铦在致《新青年》的來信中說明化學實驗室建立所需的水力、煤氣和電力供給等條件……
五四時期,雜志刊物普遍較少有經營的概念,廣告的出發點主要是為實現“傳播某種政治思想的目的”,以科學傳播為指導思想的《新青年》所刊登的廣告中自然也有很多與科學傳播有關的內容。與其他刊物相比,《新青年》廣告的主要內容并不是服裝、煙酒等推銷廣告,而是大量的圖書廣告,體現出圖書作為公共資源所應具有的啟蒙意義。《新青年》還刊登了大量報紙雜志的廣告,包括《數理雜志》《學藝》《科學》《民鐸雜志》《時事》等上百種,這些都是此時與《新青年》共同傳播科學與民主,致力于社會改革的代表性刊物。這些書刊廣告雖然并未直接指向科學傳播,也并沒有涉及具體的科學知識,但卻為想要了解和研究科學的讀者指明了方向,將科學傳播實踐擴大到同一時期的各種出版物。
2.傳播過程的雙向互動
《新青年》在科學傳播實踐中,除不斷擴大自身的編輯隊伍,還積極引入讀者的力量,吸收讀者的智慧,以提高自身的影響力;在科學傳播過程中,編輯隊伍格外注重讀者關注的問題,在與讀者的商榷與討論中進行科學傳播,和讀者群體保持良好的互動,雜志的科學傳播中始終有著深刻的讀者痕跡。
《新青年》自第2卷第1號便增設了“讀者論壇”一欄,其宗旨是“容納社外文字,不問其‘主張’‘體裁’是否與本志相合,但其所論確有研究之價值者,即皆一體登載,以便讀者諸君自由發表意見”;直至第6卷第4號,這一欄目一直斷斷續續出現在雜志中,在擴充《新青年》稿源和豐富其觀點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些讀者,如傅斯年等后來繼續在雜志上發表專論文章,擴大了雜志的作者隊伍。讀者論壇雖為讀者發表觀點的論壇,但其中也包含不少有關科學傳播的內容。
除了通過“讀者論壇”借讀者的力量豐富自身內容和擴大影響外,《新青年》也借助這一欄目,始終保持與讀者的通聯,在與讀者的互動過程中,討論與科學有關的問題,這些都成為《新青年》科學傳播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新青年》科學傳播的特點
《新青年》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堅決傳播科學、擁護科學的先鋒刊物,其科學傳播活動與先前相比,自然呈現出不同的特質。
1.傳播內容的深入:從常識介紹到觀念傳播
中國最早的科學傳播并不是從《新青年》開始的。1840年,西方列強通過大炮和鴉片撬開中國大門,中國從此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迫使當時封閉的中國人“開眼看世界”,尋求救國之路。此時先進的知識分子對西方科學的認識還停留在“器”的層面,提倡通過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來實現變法,從此開始了近代我國向西方學習的思潮。但是,對西方技術的引進卻并未改變中國落后被打的局面,民族危機的加深迫使近代中國對西方科學的學習轉向制度層面,維新派和革命派共同提倡政治制度的改革,盡管方法和落腳點有所不同,但這一時期的科學傳播開始擺脫技術層面的限制,觸碰到中國社會的制度層面。
共和政體建立后,獨裁統治仍暗涌流動,落后的道德倫理仍束縛中國社會的發展,陳獨秀等人意識到“自西洋文明輸入吾國,最初促吾人之覺悟者為學術,相形見絀,舉國所知矣。其次為政治,年來政象所證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殘之勢。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為倫理問題”。經過傳教士、洋務派和維新派三個階段的科學傳播活動,到五四時期,中國人對西方科學的學習在經歷了技術介紹和制度借鑒后,才真正涉及精神層面的內容。《新青年》刊登大量專論文章澄清科學概念,大力宣揚科學的價值和功用,傳播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在這之后,科學已經不僅僅被視為抵御外侵的技術和社會改革的工具,而是成為衡量社會一切事物的價值準則,科學的權威地位自此被樹立起來。正如胡適所說,“近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
2.傳播主體的專業:從傳教士到科學家
近代中國并未產生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因此“中國的近代科學不是對中國傳統科學的繼承,而是西方科學傳播的結果”。與之前相比,《新青年》科學傳播的主體出現了明顯的專業化傾向,從傳教士時代的“一人全寫”和戊戌變法洋務派階段的“一人多寫”轉向了“專人專寫”。
“一人全寫”時代的開啟者是利瑪竇。作為“西學東漸”的第一人,他通過結識士紳和官僚使自己的傳教活動公開合法化,但效果仍不理想。因此,利瑪竇決定采用“學術傳教”的方式,在傳播西方科學的過程中夾雜教義傳播。在中國的28年間,利瑪竇翻譯、撰寫著作18本,其中大部分是對西學的介紹,涉及地理學、天文學、數學等多門學科知識。由于利瑪竇本身并不是職業的科學家,但是作為西方科學知識的“二傳手”,他一人承擔起多學科、多種類的西學譯介工作,呈現出“一人全寫”的特點,這也體現在后續的傳教士刊物和科學傳播實踐中。
晚清時期,為延續封建帝制統治,清政府內部的有識之士開始走上了學習西方之路并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洋務派的科學傳播活動以翻譯科技書籍為主,呈現出機構化的特征,江南制造總局翻譯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一階段,從事科學傳播實踐的主要是翻譯家和外國傳教士而非科學家,他們記錄、加工和潤色學者的口譯內容并最終出版符合中國人閱讀習慣和接受心理的科技類書籍。這批機構內的翻譯家成為西方科學和中國社會的中介,幫助讀者越過語言障礙,掌握一定的科學知識。
到了五四運動時期,這種非職業科學家進行科學傳播的現象仍然存在。陳獨秀、劉叔雅、傅斯年、吳敬恒、高一涵和瞿秋白等人都是研習社會科學問題的學者,但此時一大批來自自然科學領域的專業科學家也積極投身其中。在《新青年》上,王星拱、高铦、馬君武、周建人、吳祥鳳等具有專業背景的科學家開始從事有關特定科學知識的傳播:化學家王星拱主要負責化學和生物學知識的傳播,高铦重點對數學知識和生理學相關知識進行介紹,馬君武則主要介紹生物學相關知識,李寅恭主要負責介紹植物學知識,周建人和吳祥鳳則依托自身專業背景分別主攻生物學和醫學知識的傳播……這一時期,原先“一人全寫”和“一人多寫”的科學傳播格局被打破,科學家參與到科學傳播的實踐中來,與社會科學學者各司其職、各有側重,出現了“專人專寫”的轉向。盡管與后來的中國科學化運動相比,科學家在《新青年》的科學傳播實踐中尚未居主導地位,但是這種專業化轉向已經是中國科學傳播史上的一大突破。
3.傳播取向的逆轉:從以中釋西到全盤西化
受封建專制制度和人才選拔制度的影響,科學曾長期不為人所重視,最初傳教士的科學傳播活動也只吸引了一批具有好奇心的士大夫,而并未引起中國社會對西方科學的關注。進入洋務運動時期,知識分子意識到列強在器物層面的遙遙領先,因此紛紛加入介紹西學的隊伍,此時“西學中源”的觀點也隨之出現。這種觀點認為“西方近代科技文明,不過是中華文明衍生出的支流旁系而已,隸屬于中華文明的主枝干”,并嘗試“以中釋西”,用中學來收編西學,洋務派和早期維新派的很多人都支持這一主張。
進入戊戌變法后期,嚴復、梁啟超等人開始對“西學中源”的說法進行批判。這一時 期的科學傳播者大力介紹西學,但又表現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期待,提出“對于中學擇其精要,明了中國要籍之大義之后,旁證援引西方之學”和學術不可偏廢的思想。相比于洋務運動時期,后期維新派對于西學的看法轉向更包容和更積極的一面,不再保持敵對的態度,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也體現出一定的文化自信。
這種對傳統文化的肯定和期待在五四運動期間蕩然無存,陳獨秀曾明確提出“歐洲輸入之文化,與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斷斷不可調和和遷就的”,因此中學與西學是絕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在這種思路的指導之下,《新青年》始終將中學與西學置于截然不同的對立面,旗幟鮮明地批判中學,提倡西學,這種“中西對立”的態度也體現在其科學傳播的實踐中。首先,《新青年》將科學視為一種推翻舊社會、批判舊思想、舊倫理的武器和依據,在相關科學知識的介紹方面也呈現出明顯的推崇西學,批判中學的傾向。到這一階段,原先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盲目自大和自信轉向全盤批駁,對西學的態度也由敵視、借鑒發展到全盤西化,這種“中西對立”的觀念也是構成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判性和徹底性的重要因素。
結語
作為五四時期的重要啟蒙刊物,《新青年》聚集了一批高學識的作者,通過撰寫專論文章普及科學知識、傳播科學精神,同時在科學傳播實踐中,借助讀者的力量,積極互動,在各個欄目上實現了科學傳播的全覆蓋。與之前相比,雜志的科學傳播內容從原本的技術、制度轉向對科學知識、觀念、思想和精神的傳播,科學傳播者也有了明確的專業分工,出現了“專人專寫”的專業化轉向。最重要的是,雜志在科學傳播過程中立場鮮明,呈現出全盤西化的轉向。
《新青年》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始終貫徹最初的辦刊宗旨,科學傳播內容既具學理性又貼近社會生活,有關近代科學知識的介紹和闡釋對中國人尤其是當時的青年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起到了開啟民智,提高國民素質的作用,動搖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思想基礎,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睜眼看世界”的步伐。
注釋
①⑩陳獨秀,等.新青年(第1卷)[M].北京:中國書店,2011:15,377.
②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第二編)[M].北京:中華書局,1959:316.
③陳獨秀,等.新青年(第8卷)[M].北京:中國書店,2011:448.
④陳國燦,等.《新青年》雜志書刊廣告述評[J].編輯之友,1993(12):64.
⑤陳獨秀,等.新青年(第2卷)[M].北京:中國書店,2011:70.
⑥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24.
⑦汪孟鄒.科學與人生觀[M].上海: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2.
⑧樊洪業.中國近代科學社會史研究的幾個問題[J].自然辯證法通訊,1987(3):34.
⑨曾平.晚清知識人以“中學”收編“西學”的嘗試—以黃遵憲“以中釋西”的文化整合策略為例[J].中華文化論壇,2016(1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