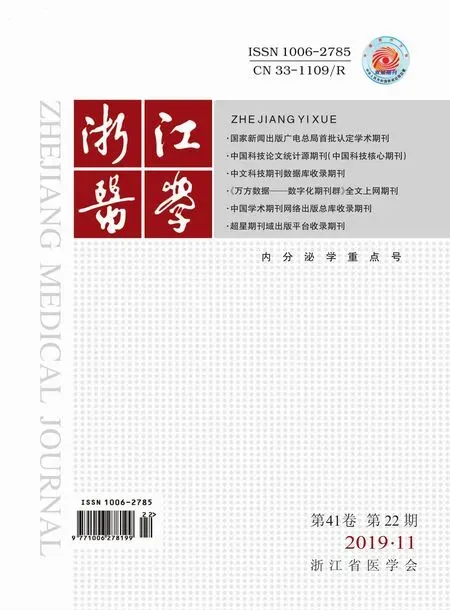以微創為核心的胰腺惡性腫瘤MDT 新模式的臨床應用
邵紅亮 馬君 牟一平
隨著醫學科學的發展,單一學科的治療常常無法滿足腫瘤患者整個治療階段的需求,也無法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診療策略。以患者為中心的多學科綜合治療協作模式逐漸取代了傳統診療模式[1]。浙江省人民醫院胃腸胰外科2016 年5 月成立胰腺惡性腫瘤多學科協作(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團隊,結合本院胃腸胰外科微創手術的優勢,逐漸探索出以微創為核心的胰腺惡性腫瘤MDT 新模式。結合多學科的力量,對于晚期胰腺惡性腫瘤患者,制定個性化治療方案,準確把握病情變化,為許多晚期“不可切除”患者贏得了手術機會。并以微創腹腔鏡手術方式,實現腫瘤R0 切除,患者術后恢復快。現以1 例典型病例,分析該模式的特點,并探討其可行性及安全性。
1 臨床資料
患者女,70 歲。因“腹部隱痛1 個月,加重2d”,于2017 年7 月2 日入住浙江省人民醫院胃腸胰外科。既往史:高血壓病史10 年,口服纈沙坦膠囊1 片/d。查體:神志清,精神可,全腹平軟,無壓痛及反跳痛。輔助檢查:癌胚抗原(CEA)10.9μg/L,CA19-9 5 326.0U/ml。腹部CT 增強掃描示:(1)胰尾部占位,大小約5.0cm×6.0cm,胰腺癌可能性大,累及脾血管及部分脾臟。(2)左腎上腺受累可能,腹膜后多發淋巴結腫大。(3)肝VⅢ段結節,轉移瘤可能(圖1)。正電子計算機斷層成像(PET-CT)檢查示:(1)胰尾部團塊狀低密度腫塊,氟代脫氧葡萄糖(FDG)代謝不均勻增高[標準攝取值最大值(SUVmax)6.3],首先考慮胰腺癌伴中央壞死,脾門受侵,鄰近脾臟和左腎受累可能。(2)椎前、腹主動脈旁及左側髂總動脈旁見數枚淋巴結影,FDG 代謝活躍(SUVmax 6.1),考慮轉移。(3)肝右葉(VⅢ段)低密度灶,FDG 代謝增高(SUVmax 4.6),考慮轉移可能性大(圖2)。初步診斷:胰腺惡性腫瘤伴肝轉移。首次MDT 討論:患者目前首先考慮胰腺尾部惡性腫瘤侵犯脾動脈及左腎上腺,伴肝臟轉移可能。建議行肝臟穿刺活檢以明確病理診斷后暫予化療,2 個月后再評估。遂予B 超引導下肝臟穿刺,但因周邊毗鄰血管,風險大而未成功。次日行腹腔鏡胰腺腫塊活檢,術中見胰腺體尾部腫塊,質硬,與胃后壁邊界不清(圖3)。術中穿刺病理檢查結果示:腺癌。于2017 年7 月17 日至9 月15 日,第1 天和第8 天各予以紫杉醇針靜脈滴注1 次,200mg/次;從第1 天起開始服用替吉奧,2 次/d,每次3 粒,連續口服2 周,然后停藥1 周;每個化療周期21d,共3 個周期。化療期間無明顯毒副反應。化療后行第1 次評估:CA 19-9 下降明顯(590.0U/ml);腹部CT增強掃描示腫瘤病灶較前稍有縮小,腹膜后淋巴結較前稍有縮小,肝轉移灶無明顯變化。結腸內致密影,炎癥或腫瘤可能(圖3)。第2 次MDT 討論:(1)患者胰腺癌新輔助化療3 個周期,腫瘤標志物較前下降,淋巴結較前縮小,化療效果顯著;(2)胰腺病灶本身及累及犯脾血管、脾臟及左側腎上腺情況較前相仿;(3)結腸腔內占位影,考慮炎癥病變可能性大,不能排除實質性占位,建議行腸鏡檢查。遂查腸鏡:未見明顯異常,對比CT 檢查結果首先考慮炎癥病變。于2017 年10 月17 日至2018 年1 月29 日,第1 天和第8 天各予以紫杉醇針靜脈滴注1次,200mg/次;從第1 天起開始服用替吉奧,2 次/d,每次3 粒,連續口服2 周,然后停藥1 周;每個化療周期21d,共5 個周期。化療后行第2 次評估:CA19-9 下降至37.0 U/ml;腹部增強CT 檢查示:腫瘤病灶、腹膜后淋巴結、肝轉移灶均有所縮小(圖4)。第3 次MDT 討論:(1)患者胰腺癌新輔助化療8 個周期后,腫瘤標志物較前下降,胰尾部病灶及淋巴結較前減少;(2)肝臟未見明顯轉移灶,化療效果顯著。建議再次PET-CT 評估,進一步評價療效及排除遠處轉移,行腹腔鏡根治性順行性模塊化胰脾切除術(Lap-RAMPS)。復查PET-CT:胰尾部軟組織密度灶伴鈣化灶,FDG 代謝同正常胰腺組織近似,腹膜后淋巴結未見FDG 代謝異常增高灶,首先考慮化療后改變。對比2017 年7 月4 日PET/CT 圖像,腫瘤處于抑制狀態,肝內未見明顯異常FDG 代謝增高灶(圖5)。于2018 年3 月5 日在全麻下行Lap-RAMPS。術后病理檢查示:未見明確惡性腫瘤殘留(符合治療后改變),胰腺切緣陰性,淋巴結(0/10)。術后再于第1 天和第8 天各予以紫杉醇針靜脈滴注1 次,200mg/次;從第1 天起開始服用替吉奧,2 次/d,每次3 粒,連續口服2周,然后停藥1 周;每個化療周期21d,共3 個周期。

圖1 腹部CT 增強掃描檢查所見(a:胰腺尾部占位侵犯脾門及脾靜脈;b:腹膜后多發腫大淋巴結;c:肝臟占位,轉移瘤可能)

圖2 PET-CT 掃描檢查所見(a:胰腺尾部占位伴FDG 代謝不均勻增高,考慮胰腺癌伴中央壞死,脾門受侵;b:椎前、腹主動脈旁及左側髂總動脈旁多發淋巴結,轉移可能;c:肝右葉低密度灶,FDG 代謝增高,轉移可能)

圖3 3 周期化療后腹部CT 增強掃描所見(a:肝臟轉移瘤大小未見明顯改變;b:胰腺尾部病灶及腹膜后淋巴結縮小;c:升結腸致密影)

圖4 8 周期化療后腹部CT 增強掃描檢查所見(a:胰腺尾部病灶明顯縮小;b:腹膜后淋巴結化療后縮小;c:肝轉移病灶較化療前縮小)

圖5 化療后PET-CT 掃描檢查所見(a:胰腺尾部腫瘤未見明顯FDG 代謝;b:腹膜后淋巴結未見異常FDG 代謝;c:肝臟未見明顯異常FDG 代謝增高灶)
2 討論
傳統的醫療模式是以疾病為中心,導致患者接受的治療方案和療效僅取決于單科醫生水平。近幾年發展起來的MDT 模式,是以患者為中心,多學科合作,為患者提供規范、個體、精準的醫療服務。隨著醫療模式的發展,外科也由切除病變、修復缺損為目的的傳統外科,走向以微創外科、精準醫療、快速康復為特點的微創精準外科。正是基于醫療模式和外科的協同發展,本研究團隊創新實施了一種以微創手術為核心,實現精準醫療、快速康復的MDT 新模式。本例患者共經歷8 個周期的新輔助化療,歷時6 個月余。通過3 次MDT 討論,精準地把握病情變化,通過化療,腫瘤標志物較前明顯下降,肝臟轉移灶消失,胰尾病灶本身縮小,淋巴結較前明顯減少,最終達到根治性切除目的。
在對胰腺惡性腫瘤發生及其本質認識非常膚淺的現實背景下,MDT 模式是發揮多學科所長、盡量減少無效性治療、爭取個體化施治的有效途徑[2],而微創化的MDT 新模式將之進一步升華。對于胰腺癌,特別是那些潛在的可治愈的、無遠處轉移、可耐受手術、無腸系膜上血管受累、CA19-9 水平提示腫瘤負荷不高的患者,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SCO)指南強烈建議直接手術切除;對于不排除遠處轉移、存在可糾正的內科并發癥、腸系膜上血管受累、CA19-9 水平提示腫瘤負荷較高的患者,存在上述任何一種狀況時,ASCO 指南強烈建議行術前治療;該指南同時認為可直接手術切除的患者,行術前治療亦是可行之選[3],真正從“手術優先”向MDT 模式轉變[4]。
通過MDT 模式主要討論能否手術,一般能手術者先手術,術后輔助化/放療,不能手術者則先行輔助化療/放療,再評估,爭取(轉化)手術[5],對于胰腺惡性腫瘤的診療堅持“以精準評估為前提、微創手術為特色,綜合治療為本”的理念,不僅關注能否手術,更關注能否首選微創方法進行診斷,特別是腹腔鏡分期。治療上也應重視腹腔鏡微創手術。其優勢是腹腔鏡分期對腹膜轉移更敏感,可彌補影像學分期的不足;且微創治療患者出血少、痛苦輕,術后恢復快,可早期開始輔助化療治療,優勢明顯[6]。總之,以微創為核心的MDT 新模式使許多已經轉移的惡性腫瘤變得可切除,且多數為微創手術治療,具有很好的社會和經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