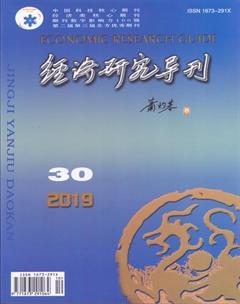美國青年學(xué)者對1924—1953年間蘇聯(lián)成就的肯定性評價(jià)
任冬梅
摘 要:通過以西方蘇聯(lián)研究實(shí)力最強(qiáng)的美國為國別考察,以研究內(nèi)容涉及1924—1953年間蘇聯(lián)問題的美國相關(guān)博士論文為選材范圍,歸納美國青年學(xué)者對于這一時(shí)期蘇聯(lián)的政治、經(jīng)濟(jì)、外交、軍事和文化教育方面成就的肯定性評價(jià)。
關(guān)鍵詞:美國;青年學(xué)者;蘇聯(lián);成就;肯定性評價(jià)
中圖分類號:C67? ? ?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19)30-0181-03
長期以來,人們往往形成一種思維定式,就是西方學(xué)者對蘇聯(lián)研究,尤其是對1924—1953年間蘇聯(lián)的評價(jià)基本都是全盤否定,似乎西方學(xué)者由于價(jià)值觀和意識形態(tài)的偏見,對1924—1953年間蘇聯(lián)各方面的巨大成就視而不見。一般而言,從西方學(xué)界一些老派保守學(xué)者身上,的確可以看到,似乎年齡越大,反蘇傾向越強(qiáng)的現(xiàn)象。倒是西方初出茅廬的年輕學(xué)人,往往對蘇聯(lián)抱有一種理解似的同情。基于此,筆者通過以西方蘇聯(lián)研究實(shí)力最強(qiáng)的美國為國別考察,以美國涉及1924—1953年間蘇聯(lián)問題的相關(guān)博士論文為選材范圍,歸納美國青年學(xué)者對于這一時(shí)期蘇聯(lián)成就的一些正面看法。
一、政治成就
加利福尼亞大學(xué)博士約翰·布林利·哈奇(John Brinley Hatch)通過研究1921—1926年莫斯科的黨—工關(guān)系(Party-worker relations),發(fā)現(xiàn)黨與工人階級的關(guān)系正在經(jīng)歷一個(gè)重新定義的過程,同時(shí)黨內(nèi)的組織安排正在得到解決,工人階級本身也在重組。很明顯,到1923年,復(fù)興工人運(yùn)動(dòng)的目的與黨的產(chǎn)業(yè)政策是相互交叉的。在經(jīng)濟(jì)不滿的推動(dòng)下,工人運(yùn)動(dòng)的特點(diǎn)是有彈性的集體行動(dòng)傳統(tǒng)以及初期的政治化,工人運(yùn)動(dòng)是一種力量,黨只有在嚴(yán)重危及其經(jīng)濟(jì)計(jì)劃的風(fēng)險(xiǎn)下才能忽視它。黨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可以在1924年出現(xiàn)的社會(huì)政治形態(tài)中找到,這種社會(huì)政治形態(tài)由官僚集中制和工人積極主義的特殊混合組成,涉及到工人表達(dá)階級地位的權(quán)利、部門和個(gè)人表達(dá)利益的權(quán)利以及以某種方式擁有這些利益的權(quán)利的默許。這是通過大量吸收工人入黨,黨領(lǐng)導(dǎo)動(dòng)員工人參加生產(chǎn)和工會(huì)生活,以及提拔工人到行政和負(fù)責(zé)崗位來實(shí)現(xiàn)的;1923年工人積極主義的重新興起以及黨需要使其權(quán)力合法化,釋放出一種動(dòng)力,這一動(dòng)力最終為革命英雄式的唯意志論(Revolutionary-Heroic Voluntarism)的重新確立奠定了社會(huì)基礎(chǔ)[1]。
普林斯頓大學(xué)博士林恩·維奧拉(Lynne Viola)探討了1929—1931年期間蘇聯(lián)農(nóng)業(yè)集體化中的二萬五千人運(yùn)動(dòng)。這2.5萬人是蘇聯(lián)無產(chǎn)階級“先鋒隊(duì)”的成員——共產(chǎn)黨黨員、熟練工人、內(nèi)戰(zhàn)退伍軍人、激進(jìn)工人等,他們于1929年底被征召參加集體化,并在新組建的集體農(nóng)場擔(dān)任集體農(nóng)場領(lǐng)導(dǎo)。這2.5萬人在集體農(nóng)業(yè)形成時(shí)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是第一次五年計(jì)劃革命的領(lǐng)導(dǎo)干部。這項(xiàng)研究的貢獻(xiàn)在于,關(guān)注對斯大林早期諸多被忽視的社會(huì)歷史。第一次五年計(jì)劃革命的實(shí)施基礎(chǔ)在于國家政權(quán)與蘇聯(lián)社會(huì)的工人階級、共青團(tuán)、共產(chǎn)黨人這些重要政治力量結(jié)成同盟[2]。
二、經(jīng)濟(jì)成就
喬治敦大學(xué)博士馬特·F.奧賈(M.A.Matt F.Oja)分析了1929—1941年間的斯大林主義的烏托邦主義與蘇聯(lián)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指出,認(rèn)識到農(nóng)村文化革命是黨的基本目標(biāo),對于理解20世紀(jì)30年代的農(nóng)村政策是至關(guān)重要的。人們希望,這場文化革命的一個(gè)關(guān)鍵來源是按照工業(yè)模式進(jìn)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尤其強(qiáng)調(diào)將生產(chǎn)集中在更大的生產(chǎn)單位,通過引進(jìn)拖拉機(jī)和大型聯(lián)合收割機(jī)實(shí)現(xiàn)機(jī)械化,按照現(xiàn)行的科學(xué)管理原則進(jìn)行重組。馬特·F.奧賈認(rèn)為,斯大林對蘇維埃農(nóng)村的偉大改造,是試圖將勞動(dòng)過程從小規(guī)模、個(gè)體化的農(nóng)民耕作轉(zhuǎn)變?yōu)榘凑兆瞵F(xiàn)代的科學(xué)管理原則組織起來的大規(guī)模、高度機(jī)械化的集體企業(yè)。簡而言之,這是把農(nóng)場改造成糧食工廠的嘗試,也是把農(nóng)民改造成農(nóng)村無產(chǎn)階級的過程。這種改革的核心支柱之一是使農(nóng)民接觸并適應(yīng)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機(jī)械,特別是拖拉機(jī)和后來的聯(lián)合收割機(jī),這在當(dāng)時(shí)被稱為牽引化(traktorizatsia)或農(nóng)村機(jī)械化。斯大林從1929年到戰(zhàn)爭時(shí)期的農(nóng)業(yè)計(jì)劃,是一次全面的嘗試,不僅是在經(jīng)濟(jì)上改造農(nóng)村社會(huì),而且是在文化上改造農(nóng)村社會(huì),從而減少并最終消除了城鄉(xiāng)之間以及蘇聯(lián)城市居民和農(nóng)民之間的文化差異[3]。
三、外交成就
加州大學(xué)圣巴巴拉分校博士雷米·艾倫.納多(Remi Allen Nadeau)分析了二戰(zhàn)期間蘇聯(lián)的勢力擴(kuò)展到歐洲的一半——比沙皇野心下的俄國軍隊(duì)向西推進(jìn)的更遠(yuǎn)。這導(dǎo)致西方列強(qiáng)在戰(zhàn)后立即集結(jié)強(qiáng)大的政治、經(jīng)濟(jì)和軍事防御力量,以確保歐洲其他地區(qū)的安全,并維持不穩(wěn)定的世界力量平衡。雷米·艾倫·納多的研究發(fā)現(xiàn):首先,在歐洲強(qiáng)權(quán)政治方面經(jīng)驗(yàn)豐富的英國人,不斷推進(jìn)限制蘇聯(lián)擴(kuò)張的步驟,雖然不是全都可行,但其中一些具有可行性;其次,由于缺乏歐洲政治經(jīng)驗(yàn)、對蘇聯(lián)意圖的誤判、對原則上無法實(shí)施的協(xié)議的篤信,依靠戰(zhàn)后的國際組織來確保人民的自決等原因,美國的努力一再受挫。簡言之,美國擁有權(quán)力,但不知道如何使用權(quán)力;英國知道如何使用權(quán)力,但又沒有權(quán)力;蘇聯(lián)擁有權(quán)力,并且知道如何使用權(quán)力[4]。
四、軍事成就
耶魯大學(xué)博士大衛(wèi)·羅素·斯通(David Russell Stone)探討了20世紀(jì)20年代和30年代蘇聯(lián)國防經(jīng)濟(jì)的轉(zhuǎn)型,認(rèn)為到20世紀(jì)20年代中期,蘇聯(lián)的總體經(jīng)濟(jì)復(fù)蘇使沙俄時(shí)期遭受戰(zhàn)爭和革命破壞的國防工業(yè)得以重建。然而,重建迅速變?yōu)閿U(kuò)張。現(xiàn)代戰(zhàn)爭要求經(jīng)濟(jì)和國家完全服從戰(zhàn)爭的需要,布爾什維克對外部世界堅(jiān)持不懈的敵意信仰確保了對蘇聯(lián)重新武裝的堅(jiān)定承諾。1927—1928年間,財(cái)政資源稀缺,限制了軍事預(yù)算和軍工投資,但蘇聯(lián)工業(yè)化進(jìn)程的加快緩解了這一制約[5]。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xué)博士莎莉·韋伯·斯托克在考察1928—1933年俄國軍事革新的起源與政治時(shí),發(fā)現(xiàn)盡管有軍隊(duì)的一再努力,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直到1931年日本入侵滿洲時(shí),才把防御作為一項(xiàng)重要任務(wù)。出于對日本野心的恐懼,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開始將更多的國家預(yù)算份額分配給蘇聯(lián)紅軍。在1931年之前,在那些鼓吹和平時(shí)期國防建設(shè)的人與那些支持工業(yè)逐步發(fā)展(以及最低限度的和平時(shí)期采購)的人之間,展開了一場爭論。由于最初的時(shí)候,國防是一個(gè)不那么令人擔(dān)憂的問題,莎莉·韋伯·斯托克闡述了軍隊(duì)如何試圖說服共產(chǎn)黨,在國內(nèi)動(dòng)亂和競爭性的工業(yè)計(jì)劃時(shí)期,其重整軍備訴求的重要性。在莎莉·韋伯·斯托克看來,紅軍現(xiàn)代化的核心是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的創(chuàng)造性作用(the entrepreneurial role)。圖哈切夫斯基巧妙地運(yùn)用意識形態(tài)來推動(dòng)他雄心勃勃的重整計(jì)劃。莎莉·韋伯.斯托克認(rèn)為,圖哈切夫斯基除了具有非凡的才能和技術(shù)專長外,還具有相當(dāng)強(qiáng)的政治能力(bureaucratic prowess),這使他能夠最終實(shí)現(xiàn)他的職業(yè)軍事目標(biāo)[6]。
耶魯大學(xué)哲學(xué)博士大衛(wèi)·羅素.斯通(David Russell Stone)論述了1926—1933年間的斯大林革命對于國防工業(yè)與蘇聯(lián)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的影響。斯大林獲得最高權(quán)力后,布哈林和里科夫等支持保守財(cái)政政策,從而導(dǎo)致軍費(fèi)開支低的人被免職。這與針對所謂的怠工者和“破壞分子”(wreckers)的大規(guī)模運(yùn)動(dòng)相結(jié)合,使那些反對加快擴(kuò)張以滿足紅軍日益增長的對現(xiàn)代武器的渴望的聲音名譽(yù)掃地。1929年4月批準(zhǔn)的第一個(gè)五年計(jì)劃導(dǎo)致了1929年7月的另一項(xiàng)指示,即進(jìn)一步投資軍工和紅軍全面現(xiàn)代化。最后,1931年的滿洲危機(jī)使人們對“資本主義包圍”的恐懼被一種具體的威脅所取代。結(jié)果,蘇聯(lián)經(jīng)濟(jì)動(dòng)員到半戰(zhàn)爭—半和平狀態(tài),以應(yīng)對日本日益增長的威脅,這導(dǎo)致了將一直延續(xù)到蘇聯(lián)解體的一種國防經(jīng)濟(jì)的形成。國防工業(yè)現(xiàn)在在經(jīng)濟(jì)政策中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而紅軍將永遠(yuǎn)不會(huì)再為匱乏大量現(xiàn)代武器而苦惱[7]。
五、文化教育成就
哈佛大學(xué)哲學(xué)博士大衛(wèi)·布蘭登伯格以1934年至1956年間的文藝、電影和藝術(shù)背景下的黨政教育為研究對象,分析了斯大林主義歷史教科書、大眾文化與俄羅斯民眾民族認(rèn)同的形成之間迄今未被重視的聯(lián)系。在大衛(wèi)·布蘭登伯格眼里,1937—1956年期間由國家批準(zhǔn)的歷史教科書,為蘇聯(lián)社會(huì)提供了一種敘事,這讓俄羅斯人作為一個(gè)群體第一次想象它作為一個(gè)國家共同體的成員意味著什么。由于沙皇和蘇維埃國家早期對俄羅斯民族認(rèn)同的培養(yǎng)的挫敗,以民族為中心的歷史在革命后二十年左右才成為公共教育和政黨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1937年后這一代的歷史教科書在語氣和內(nèi)容上與其說是國際主義的,不如說是民族主義的,這標(biāo)志著意識形態(tài)的深刻變革,到20世紀(jì)40年代末,這將影響到國家支持的大眾文化。盡管蘇聯(lián)社會(huì)的俄羅斯人在20世紀(jì)60年代就開始明顯地表現(xiàn)出民族主義情緒,這些情緒與環(huán)境保護(hù)主義、保存歷史古跡和慶祝“鄉(xiāng)村散文”有關(guān),但人們普遍認(rèn)為,這些運(yùn)動(dòng)借鑒了舊觀念。俄羅斯的國家身份已經(jīng)廣泛傳播,雖然其中一些信仰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shí)期,但在20世紀(jì)30年代之前,不可能將其稱為有助于形成一個(gè)統(tǒng)一的民族認(rèn)同,因?yàn)樯鐣?huì)的政治和歷史意識在不同地區(qū)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大衛(wèi)·布蘭登伯格認(rèn)為,現(xiàn)代俄羅斯的民族認(rèn)同只有在斯大林統(tǒng)治下的大眾層面上得以融合,這是由于社會(huì)第一個(gè)大眾歷史課程的引進(jìn)以及隨之而來的包括從文學(xué)、電影到戲劇和歌劇等大眾論壇所發(fā)生的變革[8]。
哈佛大學(xué)博士卡爾·菲利普·霍爾指出,作為革命后基本得到鞏固的一門學(xué)科,蘇聯(lián)的理論物理在科學(xué)研究方面,占據(jù)著一個(gè)特別微妙的地位,與之相比,國家規(guī)定科學(xué)研究越來越被要求要遵循嚴(yán)格的經(jīng)濟(jì)生產(chǎn)標(biāo)準(zhǔn)。諾貝爾獲獎(jiǎng)理論家伊戈?duì)枴ぐ7蚪鹨S奇·塔姆(Igor Evgenievich Tamm)和列夫·達(dá)維多維奇·蘭道(Lev Davidovich Landau)等人一貫致力于以特有的蘇聯(lián)方式,為現(xiàn)代物理學(xué)的事業(yè),做出了巨大的貢獻(xiàn)(無論是基于信念還是基于環(huán)境),即使他們在大多數(shù)方面,都在與從事類似智力任務(wù)的理論物理學(xué)家所組成的國際網(wǎng)絡(luò)中,顯示了自己的專業(yè)性。蘇聯(lián)的理論家只能通過參加文化“第三戰(zhàn)線”(the third front of culture)的戰(zhàn)斗,來為理論研究創(chuàng)造一個(gè)制度性的場所,這是自革命最初歲月開始,由布爾什維克倡導(dǎo)的更寬泛的軍事術(shù)語的寬泛運(yùn)用。這就要求編寫?yīng)毺氐奶K聯(lián)教科書,培養(yǎng)新一代物理學(xué)家,以超越斯大林所譴責(zé)的那種“無原則的實(shí)踐主義”(unprincipled practicalism)[9]。
參考文獻(xiàn):
[1]? John Brinley Hatch.Labor and Politics in nep Russia:Workers,Trade Unions,and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oscow,1921—1926 (Working Class,Management,Industry,Stalinism,Leninism)[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5.
[2]? Lynne Viola.The Campaign of the 25,000ERS:a Study of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Soviet Agriculture,1929—1931(Russia,Stalin)[D].Princeton University,1984.
[3]? M.A.Matt,F(xiàn).Oja.The Quest for the Ultimate Smychka:Stalinist Utopianism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oviet Agriculture,1929-1941[D].Georgetown University,1994.
[4]? Remi Allen Nadeau.The big three and the Partition of Europe,1941—1945(Roosevelt;Churchill;Stali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1987.
[5]? David Russell Stone.The Red Army and Stalins revolution:Defense indust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economy,1926—1933[D].Yale University,1997.
[6]? Sally Webb Stoecker.Forging Stalins army:The sources and politics of military innovation in Russia,1928—1933[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95.
[7]? David Russell Stone.The Red Army and Stalins revolution:Defense indust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economy,1926—1933[D].Yale University,1997.
[8]? David Brandenberger.Theshort course to modernity:Stalinist history textbooks,mass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popular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1934—1956[D].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1999.
[9]? Karl Philip Hall.Purely practical revolutionaries A history of Stalinist theoretical physics[D].Harvard University,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