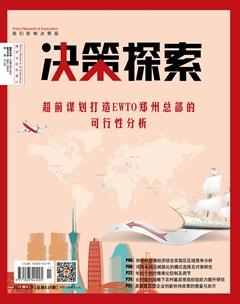基于中西科技發展特點 淺析近代中國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
張軍威
在17世紀中葉之前,中國的科技水平曾長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然而,在17世紀中葉以后,中國科技日漸衰微,其中緣由十分復雜,學界稱為“李約瑟難題”,研究這個難題對推動現代中國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具有重要意義。目前,大部分學者均從政治、經濟、 文化等方面找原因,很少基于中國科技發展的特點進行剖析。本文基于中西科技發展的特點,試分析近代中國科技落后的原因。
一、重技術輕科學,重實用輕理論
“科技”顧名思義就是指科學與技術,二者既是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科學是對自然規律進行探索的學問,也是人類探索研究感悟宇宙萬物變化規律的知識體系的總稱,科學的重點在于知識的發現和創造,而技術的重點在于將知識應用于實踐。在亞里士多德的技術思想中,技術的主要存在形式表現為技巧、能力、方法。
古代中國的科技,從研究目的上來講是以實用為核心的,并且大力發展工匠技術以及實用科學。追溯到春秋末,第一部中國已知最早的手工業技術文獻著作《考工記》就是如此,全書重點以技術介紹為主,對于理論、原理研究上的內容少之又少,整本書涉及了車輿、宮室、兵器等制作工藝和檢驗方法,并未提及相關科學原理,這就造成當技術遇到新問題時,由于缺乏新的科學成果而難以解決。同樣,在北宋時期,沈括在《夢溪筆談》里描述了對磁的探究,描述了磁偏角,同時他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描述磁偏角的人,至此以后中國對于磁的研究也基本趨于停滯,對于磁的應用也僅僅依靠指南針來體現,并應用于祭祀、禮儀、軍事等,這樣造成了中國的科技發展由于存在對理論的嚴重忽視,及主體作為世界觀缺乏科學的理性,在進行科技研究時以直觀和經驗為出發點,難以跳出經驗的牢籠。
然而在西方,具有鮮明特色的古希臘科學技術體系就有“為科學而科學”的非功利性,形成了理論與實驗、科學與技術的循環機制及動力結構,實驗對理論進行檢驗,實驗的可重復性從而給技術的發展提供動力,同時技術的發展又能夠借助實驗推進理論的發展。因此,在文藝復興之后西方科技突飛猛進,技術的發展得到更新。在技術的作用下,西方在制造、農耕、貿易和航海等領域得到了改進和發展。例如19世紀20年代奧斯特發現了電流的磁效應,到了19世紀下半葉,麥克斯韋總結了宏觀電磁現象的規律,并引進位移電流的概念,預言了電磁波的存在,而后在赫茲那里得到了證實,二人構成了經典電動力學的基礎,為后來西方工業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雖然最早發現了磁,但是更多的是把精力放在對技術的追求上,理論研究上少有建樹,沒有了足夠科學理論的支撐,在技術發展上明顯動力不足難以突破。
近代的中國,把眼光僅僅放在了對自己有用的局部上,從而忽視了整體的存在,只能看到技術的應用,卻看不見理論的不足。因而,重技術輕科學、重實用輕理論的特點嚴重阻礙了中國近代科技的發展。
二、重綜合輕分析,重歸納輕邏輯
從學術分類來看,中國古代在學術分類上主要以六藝為核心,以經、史、子、集為框架,文史哲是沒有明確分類的,強調以綜合為主的學術分類。對此傅斯年曾說“中國學術,以學為單位者至少,以人為單位者轉多,前者謂之科學,后者謂之家學;家學者,所以學人,非所以學學也”。也就是說,中國的學術界追求“博學”和“博通”,造成了學術分類是以綜合的思維建立起來,不著重對立。以中醫為例,中醫學以陰陽五行作為理論基礎,作為中國影響深遠的一部醫學著作《黃帝內經》就是在黃老道家理論上,建立了中醫學上的“陰陽五行學說”“經絡學說”“脈象學說”“病癥”“診法”等學說,在整體上對醫學進行論述,形成了以心理、社會、自然、生物于一體,以辯證論治、整體觀為精髓的“整體醫學模式”,同時在素材的來源上也是中國古人對生命現象的長期觀察、大量的臨床實踐以及簡單的解剖學知識歸納而成。這就造成了只能通過綜合的情況對病癥進行治療,在治療過程中難以發現精準的病因,依靠歸納得出來的知識服務實踐,在實踐中缺少邏輯的推理,很難根治病癥。
西方的學術分類通過將研究對象作為區分,從而形成了不同的“學科”。傅斯年曾說“西洋近代學術,全以科學為單位,茍中國人本其‘學人之心以習之,必若枘鑿之不相容也”。西方在學術分類上講究分科,對學術分類分得很細致,早在亞里士多德時代已經初具雛形,那時以研究對象為標準分為數學、物理、政治、經濟等科目,進而對各學科進行分門別類研究,是用天和人相分離為基礎的文化觀進行分類,以探索自然為目的實現自由的科學精神。西醫是在西方國家的學者否定并摒棄了古希臘醫學之后,以解剖生理學、組織胚胎學、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作為基礎學科所發展出來的一門全新的醫學體系,在分類上進行了細致的劃分,并且在文藝復興以后,西醫開始了由經驗醫學向實驗醫學的轉變,不再是單純地依靠經驗的綜合式治病。16世紀維薩里發表的《人體構造論》建立了人體解剖學,17世紀實驗、量度的應用,使生命科學開始步入科學軌道,從而借助量度提高精準度。西方醫學隨著實驗的興起,出現了許多科學儀器,顯微鏡就是其中之一,顯微鏡把人們帶到一個新的認識水平,使得人們在認識上從宏觀發展到微觀,為更好地分析病因創造了條件。到了18世紀,莫干尼把對疾病的認識由癥狀推到了器官,建立了病理解剖學,逐步形成了以形態、物質結構以及其他相關理論為指標對人體進行生理、病理及科研成果的評價體系,讓西方醫學可以進行更科學的推理。
綜合方法本身并無不妥,而且在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優越性,可以有效防止“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現象的產生,但如果只進行綜合而不加以深入分析,所得到的只能是籠統的、推測性的結論而不是精確的結果,也不能形成精深的理論和體系。
三、重思辨,輕實驗
中國古代十分重視思辨,當時哲理思辨思想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唯心論、樸素唯物論、形而上學以及樸素辯證法相雜糅的老莊學、易學;二是以邏輯思辨與自然哲學見長的別墨學派和惠施學派;三是以神學唯心主義作為主要表現的佛學,當時的科技發展主要受這三類思辨所制約,雖然也曾掀起過道家哲學、宋明理學、王夫之與方以智哲學等哲理思辨思想運動,但在研究對象上均將重點放在了宇宙本體、自然的探索,同時在研究方法上擺脫對歷史經驗和具體事物的陳述運用純思辨的思維方式,因而三次思辨運動只能在湮沒或變異的悲劇道路上徘徊,最終沒能走出準宗教的范圍。中國古代很多思辨性思維由于缺乏科學實驗的事實和數據的基礎, 因而其議論往往流于空乏,沒有什么實際的科學意義和價值。正是由于對科學實驗的嚴重忽視,致使在我國古代文化的典籍中關于科學實驗的記載十分缺乏,這種缺陷嚴重制約了科技在中國近代的發展。
西方的哲理思辨思想則是在初始層次的“合”、在實證科學條件下的“分”趨向更高層次的“合”,這也使得西方科技在發展的過程中既有思辨又有實驗。然而這樣的科技發展觀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古希臘的世界觀一開始也是互相關聯和整體的動態思維模式,直到中世紀成為了一個完全不變的僵化模式,在文藝復興以后、近代工業到來的前提下,由思想家兼科學家的斯賓諾莎、笛卡爾、牛頓等人從整體僵化的思維模式中脫離出來,開始著重從部分、個體、局部進行動態的分析模式,再經過康德、謝林、萊布尼茨的批判性改造加以發展,最后到黑格爾那里,其思維模式從個體局部的動態分析上升至高水平的動態以及整體綜合分析的靜態相結合,最終從宗教的狂熱之中順利走出來,為西方科技發展解放了思想。西方在發展思辨的同時,對于作為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的實驗尤為重視,比如拉瓦錫用實驗證明了空氣是由氧氣和氮氣組成的、馬德堡半球實驗證明了大氣壓的存在、密立根油滴實驗首次測量出了電子的電荷量、法拉第電磁感應實驗證明了磁生電,他們將理論與實驗結合,有效避免了以思辨為中心的科技研究。
四、重社會,輕自然
中國古代的思想文化受先秦哲學的影響比較大,這也使得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受到其影響,先秦哲學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中國哲學的萌芽、諸子前哲學和諸子哲學。然而,先秦思想的研究重點是在社會政治、倫理等這些重大問題上面。因而,中國古代哲學常常首先思考的是人類理想社會的問題,這也造成了對于自然世界認識的滯后性,以及大量科技資源的浪費,尤其是科技人才的不足,科技研究很大程度上在社會表象上面徘徊,很難把科學從哲學中抽出,注重社會政治、倫理的研究,輕視自然世界研究使得中國科技難以獨立發展。
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古希臘哲學的影響較大,在古希臘哲學中得到發展。公元前6世紀進入了自然哲學時期,哲學家們提出了世界的本原問題,反對神創論,用自然本身來解釋世界的生成,使得西方科技向自然研究方向發展。到了公元前5世紀,出于政治民主的需要出現了一批“智者”思想家,他們以教授演說的論辯術為業,將問題討論的中心集中到人類社會政治倫理方面來,但是由于這屬于帶有主觀唯心主義色彩的哲學,遭到了蘇格拉底的反對,蘇格拉底認為客觀真理是存在的,而后經歷了希臘化時期,最后發展到古羅馬哲學。可見,西方古希臘哲學的研究重點在于對自然界的普遍原理研究,最先提出的是關于自然界本質的問題,而后是對人類社會進行認識。
由此可見,在發展科技的同時對于理論的發展不能輕視,要把理論與實驗、科學與技術進行循環發展,做到技術的發展可以依托理論和實驗的進步。研究科技問題時,要在綜合的基礎上加強分析,以提高精準度;在歸納的同時提升邏輯推理的應用,不要空想科技,要把思辨與實驗進行結合,用實驗驗證思辨。要注重科技成果的分享和自然科學的發展,加強對自然規律的探索,讓科技成果惠及更多人,不斷加強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科學技術交流。
【本文系廣西科技廳軟科學研究課題“廣西協同創新機制與對策研究”(13180025-2)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廣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