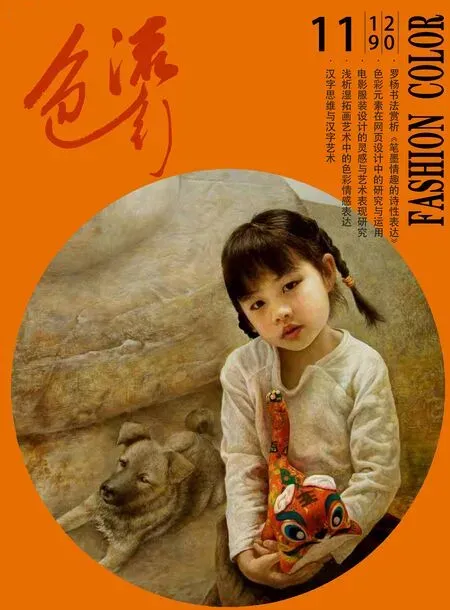“李滄東式”現實主義的探索
——以韓國電影《燃燒》為引
楊晨玉(武漢大學 藝術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在韓國影壇中,有一批創作民族化,平民化的電影人,李滄東導演就是其中代表之一。李滄東的現實主義題材電影有很多比如《詩》《密陽》《綠洲》《薄荷糖》《綠魚》以及去年戛納熱映的《燃燒》。縱觀他拍攝影片的年限和數量,可以看出他的作品是少而精的,而且無論哪一部影片,導演鏡頭下的人和事,中心視角通通是圍繞邊緣人對世界的吶喊問題,這些問題表現在社會與個體的矛盾,個體與自然的矛盾,個體與個體的矛盾,個體與自身的矛盾等等。他很善于挖掘小人物身上感人的一面,善于運用長鏡頭,充分真實的表現客觀事實,畫面體現出亞洲電影獨有的東方詩意。可以說,李滄東導演憑借其對電影語言的獨特理解和深厚的文學底蘊形成了鮮明的個人風格。
一、電影形式的探討:韓國人特有“恨”的民族情結
韓國的“恨文化”包含兩層意思:首先,對痛苦與磨難的忍受以及積累下來欲罷不能的遺憾與悲憤;其次,內心的悲而不哀以及因悲傷壓抑而愈發振奮的情感。韓國文化中確實帶有由“恨”所誘發出對殘缺、凄涼的崇拜,這與以悲劇為核心的現實主義美學不謀而合。韓國人特有的歷史背景使得國民產生極強的文化認同心理和“恨”的民族情結,因而韓國電影人基于韓國人焦慮、復雜的國民性格,同“恨”文化對現實主義電影展開探討和創作,并對韓國現實主義電影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李滄東導演的童年處于韓國戰后巨變的動蕩時代,童年受到的嚴重災難給了李滄東切身的體驗,潛移默化地在骨子中展現出來,電影當中的民族感情自然而然地流淌出來,將“恨文化”彰顯得尤為凸顯。在觀看李滄東導演的諸多電影時不難看出他電影中大多家庭都是荒頹破碎的,比如他所有電影中“父親”形象皆缺位:《綠魚》中末東喪父;《綠洲》中洪忠都無父,擔當父親形象的大哥,更是一個不負責任(讓弟弟充當車禍替罪羊)、冷漠無情的人;《密陽》中申愛剛剛喪夫;《詩》中,美子與外孫相依為命,孤寡苦撐。《燃燒》中男主人公不如意的家庭和一個可能會坐牢并不曾露臉的父親,主人公作為尋常個體在無常現實境遇中的苦苦掙扎。我們都知道電影主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定社會現象的反映,所以李滄東電影的主題往往具有對苦難的表達和對平凡人物的無限悲憫與同情。
二、以《燃燒》為引,縱觀李滄東其他現實主義影片
電影《燃燒》改編自村上春樹的《燒倉房》和福克納的《燒馬棚》,影片中聚焦著貧富矛盾,階級固化,年輕人就業困難等社會問題。電影的發力點很準,似乎有一種打到社會痛處的感覺,關注到了階層的固化問題所引發底層年輕人的憋屈心理。隨著社會就業大環境日益惡劣,失業率劇增,工作很難被找到,年輕人每天都郁郁寡歡,茫然地尋求著活下去的動力。而與之相對比的,上層社會的人總是很輕易地獲得大量的資源與機會,每天都毫不費力地賺著大把金錢,自由肆意地揮灑著時間。除了貧富矛盾階級固化,就業難等問題,現代人由于生活的節奏越來越快,但內心卻越發地躁郁和空虛,時常感覺到麻木和孤獨,似乎每個人都在喧囂中孤獨地活著。《燃燒》影片以兩個對立階級的代表本和鐘秀來分別展現各自階級人物的生活狀態,展現出韓國乃至整個世界的現實問題。通過視覺層面上的諸多象征與隱喻及聽覺層面上的近乎某些“失語”的手法,使影片敘事的中心隨著人性的起伏變化而變化,給人以震撼和反思,同時在情感上的表達也極為細致,很好地將敘事和寫實進行融合。
《綠魚》《薄荷糖》 《綠洲》《密陽》《詩》都是李滄東一人獨立完成的劇本。《薄荷糖》是一部有關時間的電影,他用韓國20年間政治、經濟、歷史巨變的7個段落,用時間講述了主人公在無情歲月中逐漸麻木直至崩潰,一步步走向自我毀滅的過程。導演李滄東很擅長用秀美的畫面去描繪小人物或者是邊緣人物的生存狀態,因而具有著強烈的個人風格。
《綠洲》將鏡頭鎖定在韓國社會底層的、不被人關注的一對年輕男女身上。男主角將軍已近而立之年,卻是一個無法適應現實生活的智力障礙者,曾替家里的大哥以暴力及強奸未遂的罪名進過監獄。女主角公主則是一個重度腦麻痹殘疾人,行動不便并伴有渾身抽搐失控癥,每天只能躺在空空的屋子里,時常看著掛在墻上的名為“綠洲”的羊毛掛毯。也許冥冥中自有天意,正是這樣兩個人物,他們在“綠洲”前相知相戀了。這樣兩個深陷殘疾、地位尷尬的人,戀愛的道路可想而知將多么曲折和不被世俗理解,留給了觀眾深深的心痛和遐思。
《詩》講述的是60歲的祖母和10歲的孫子之間的故事,祖母為孫子創作了自己的第一首詩。楊美子在現實的泥沼中苦苦掙扎,帶著想象的一腔浪漫情愫優雅地投進了詩的懷抱,最終用一紙遺書維護了純潔與尊嚴。比起李滄東的前幾部作品,《詩》似乎少了一點錐心的刻骨之痛,卻樹起一種淡然的憂傷。也許那些與生活對等的人們,注定要由她們的人生激烈地破碎才能迸裂出充滿悲劇性的美。
《密陽》采用的是一個未解的開放式結局。以密陽小城的一道陽光,定格于院內一小片陰地上,我們并不知道它將預示什么,但這恰恰代表著李滄東導演藝術的升華。李滄東影片的主題通常都通常圍繞著一些邊緣人,去表達他們的痛苦與不幸,讓我們注意到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生活還有著這樣不公的事情存在。并通過人們不曾注意的日常生活的小細節,從小人物的人生中發現生活的真諦。
縱觀李滄東電影,他的語言很傳統,很穩,有一種現實主義的復興,節奏和鏡頭的呈現精準至極。同時李滄東善于運用長鏡頭,又通過其獨特的鏡頭語言并秉承韓國電影一貫精致細膩的風格,使得鏡頭犀利真實又具有觀賞價值。
三、現實主義層面的主題探索:個體與社會的沖突,對邊緣人物的關懷
李滄東電影關注的一直都是人本身,因而電影的主題都是人生、社會以及人與社會的關系。邊緣人主要有三個方面的特點:身份處于社會底層,身體或精神患疾,絕望的同時又充滿希望。盡管這些邊緣人都保留著人性最初的美好,都懷著滿腔熱血向往單純美好的事物和未知的明天,但是他們卻始終擺脫不了社會和命運對他們的捉弄。他們也努力地抗爭過、努力地改變過,想讓這個世界看到自己的存在,找到自己的價值,但通常事與愿違,從李滄東的《密陽》《綠洲》和《燃燒》都能看出這種深深的無力感,導演希望用自己的電影語言展現出這類群體的生活現狀,表達出自己的同情與關懷,并給觀眾留下思考。
在電影《綠魚》中,黑幫男人在愛情和逃亡的選擇中絕望,在《薄荷糖》中,一開篇男主人公就迎著火車自殺,沒給這個崩潰的男人任何活下去的希望也沒給觀眾任何的溫暖。《密陽》中,女主人公在喪夫之后來到丈夫的故鄉,準備一切重頭開始。在當下的社會背景,單身母親已經是很邊緣的群體了,而偏偏又讓她失去了唯一的孩子。此時,母親的悲哀、憤怒、絕望充斥著整部影片,當母親想要通過宗教去尋找寄托的時候,整個社會看似有一股包容的力量,給予溫暖,但當母親想要去原諒兇手的時候,殘酷的社會又給她當頭棒喝。那種絕望到谷底又沒人能幫助,痛苦只能依靠自己僅存的微弱意志進行救贖,這實在是一種悲哀。《綠洲》拋棄了俊男靚女,沒有耍帥玩酷,他們甚至只是一些日常生活中你從未關注過甚至曾經無意鄙視過的殘障人群,但是從他們身上爆發出的那種對于世俗令人心碎的冷眼旁觀,那種渴望被理解的強大自尊,足以讓我心靈震撼甚至眩暈。影片結尾修剪樹枝的那場戲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高潮,李滄東運用了女孩兒的運鏡視角,與男主人公拉開距離,公主放著收音機的回應,將軍隨著音樂亂舞,表現他達成心意的滿足,讓觀眾深深為此觸動。
他為了能夠充分地表達出電影內容的主題,在電影里有很多符號化的運用,隱喻地表現韓國社會中邊緣人悲慘的處境。比如導演在《燃燒》中就有多處符號化的運用呈現給觀眾,同時運用了很多意味不明確的隱喻、象征,比如啞劇、自慰、非洲舞、不知是否存在的枯井和貓咪、燃燒的火焰以及迅速消失的反射光等。同時李滄東的戲劇沖突很是強烈,體現在個體與社會發生沖突時,個體尋求的解決方式都趨向于一種崩潰的瘋狂。無論是《燃燒》男主人公鐘秀最終奮力地用刀連捅數刀在富二代本身上,并用油將其豪車和自己的衣服一燒而盡;還是在《綠洲》中,男主人公奮力地近乎瘋狂地將嚇到女主的窗外樹砍掉的情節;抑或是《密陽》里女主多次聲嘶力竭的呼喊和呼吸急促到窒息的崩潰情節以及多處表面不動聲色其實劍拔弩張、暗潮洶涌的內心戲都能展現出強大的戲劇爆發力,令觀眾沉浸其中,感觸深刻。
結語
部部電影,部部佳作。能做到這一點正由于他認為電影的本質其實就是生活,每個電影人都該有自己對生命和人生的看法。李滄東導演的現實主義風格電影所表現的邊緣人都是在主流社會中苦苦掙扎、努力擺脫痛苦的人。李滄東從人們忽略的、遺忘的、熟視無睹的生活中找到了人生的真諦,也許在他作為一個作家的時候,他便開始尋找這種真諦。或者說,正是因為他深厚的文學功底,才造就了他導演之路的輝煌。總之,李滄東通過無懈可擊的劇本和鏡頭,通過現實主義的表現,客觀地反映人物的內心世界,為我們展示了一個哲學化的世界。無論是《燃燒》還是《綠洲》《密陽》,他的影片永遠是淡淡的,似乎所有的電影都在最激烈的地方故事轉了個彎兒,從無心的細節中透露著憂傷,又引人深思。他改變了人們對韓國電影“催淚、煽情”的一致理解,也勇敢地拋棄了韓國電影中慣有的溫暖煽情的情節,而是真正聚焦真實,聚焦生活,從而讓人們去探索并思考人生真正的意義。而這種意義才是更加觸動人們心靈的,同時也幫助我們更好闡釋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