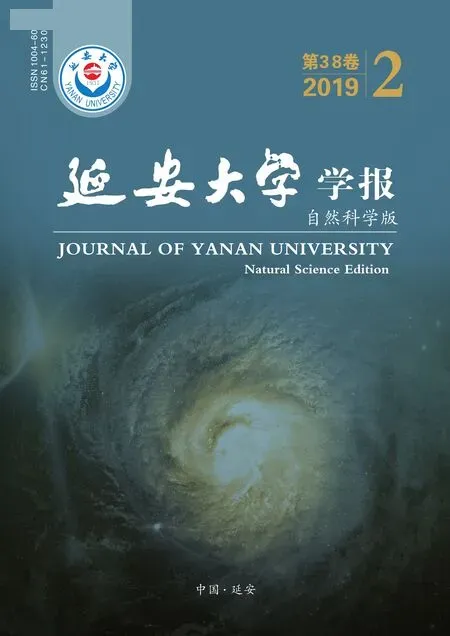內分泌干擾物對水生動物的生殖生理毒性研究進展
吳航利,王 佳,管融資,安 鵬,雷 忻*
(1.延安大學生命科學學院;2.延安市生態恢復重點實驗室,陜西延安716000)
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和人們的物質需求日益增加,一系列的環境問題繼而爆發。內分泌干擾物(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EDCs)是一類毒性較高,可與內源激素受體結合或改變內源激素合成、轉運、代謝,進而干擾生物內分泌系統的一類外源有機污染物[1,2]。EDCs可通過地表徑流等方式進入水生生態系統,在水生生物體內富集,通過食物鏈的逐級放大效應,使得魚類等高等水生動物體內富集較高濃度的EDCs,進而影響人類健康[3,4]。EDCs可作為類雌激素或類雄激素在生物體內發揮作用[5],通過誘導基因異常表達,危害細胞、組織和器官,進而對生物個體甚至種群產生威脅。本文就EDCs對水生動物生殖與生理毒性研究概況進行綜述,為進一步認識EDCs的毒害作用,有效控制EDCs污染,改善水域生態環境提供理論依據。
1 常見的EDCs種類
目前,內分泌干擾物可分為三大類:一類是為滿足人類生產生活所需要而制造出來,包括有機氯殺蟲劑(如,六六六,氯丹,滅蟻靈,滴滴涕等),工業清洗劑(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onylphenoxy poly(ethyleneoxy)ethano,NPEs)和辛基酚聚氧乙烯醚(Octaphenyl Polyoxyethyiene,OPEs)降解產生的壬基酚(Nonyl Phenol,NP)和辛基酚(Octyl phenol,OP)),以及醫藥用品(如,己烯雌酚(Diethylstilbestrol,DES)和乙炔雌二醇(Ethinylestradiol,EE2));一類是工業活動而產生的環境污染物,常見的有多環芳烴類(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PAHs),多氯聯苯類(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PCBs),雙酚A(BisphenolA,BPA)以及二噁英和相關化合物(如多氯代二苯并二噁英(Poly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s,PCDDs)和多氯代二苯并呋喃(Polychlorinateddibenzofurans,PCDFs));還有一類是天然的化學物質,包括雌激素(如,雌酮(Estrone,E1),雌二醇(17-β-estradiol,E2)和雌三醇(Estriol,E3))和雄激素(睪酮(Testosterone,T))。
2 EDCs對生殖系統的影響
有研究證明,內分泌干擾物(如BPA,PCBs,E2,NP,OP等)是水環境常見的雌/類雌激素物質[6-9]。卵黃蛋白原(Vitellogenin,VTG)是環境雌激素類化合物暴露的生物標志物,在孔雀魚(Poeciliareticulata)實驗中,PCBs和E2均能誘導雄性孔雀魚VTG的產生[8]。研究證實,VTG是卵黃蛋白的前體,為卵細胞運輸多種營養物質,與卵生動物的生殖發育密切相關;肝臟VTG的合成主要依賴于雌激素的作用,EDCs與機體內的天然雌激素結構相似,進入動物體內,可干擾VTG正常合成,進而影響生殖系統的正常功能。研究表明雄性或幼體VTG的異常表達與機體的有害病理學改變有關,主要表現為精子生長和精巢發育被抑制以及性成熟改變等[10]。雄性斑馬魚的實驗表明,EE2暴露時,斑馬魚精巢壁會變厚,生殖細胞大量丟失;氟他胺(Flutamide,FIU)處理時,精子細胞數量下降;EE2和FIU聯合處理時出現協同效應,精巢生殖細胞數量急劇下降[11]。己烯雌酚(Diethylstilbestrol,DES)可影響斑馬魚精子發生,使生殖細胞凋亡[12],這種現象在青鳉(Oryziaslatipes)和銀鯽(Carassiusauratus)的研究中也已被證實[13,14]。因此,EDCs會導致水生動物生殖腺和生殖細胞發生異常,從而對動物發育和繁殖產生影響。
3 EDCs對酶系統的影響
3.1 對Ⅰ相混合功能氧化酶系的影響
3.1.1 混合功能氧化酶的作用和分類
內分泌干擾物(如,共平面的芳香性外源有機污染物PAHs、PCBs等)進入脊椎動物體內后與肝細胞內的芳香烴受體(AhR)結合,激活AhR信號通路,Ⅰ相混合功能氧化酶(mixed-functional oxidase,MFO)系統相關酶系產生效應[15],對機體發揮解毒作用,降低外源性有機化合物的脂溶性,使其形成易排泄的代謝產物[16]。
根據MFO的催化活性,可以將其分為:7-乙氧基異吩惡唑酮脫乙基酶(7-Ethoxyresorufin-O-deethylase,EROD)、7-乙氧基香豆素脫乙基酶(7-Ethoxycoumerin-O-deethylase,ECOD)和芳烴羥化酶(Aryl hydrocarbon hydroxylase,AHH)等,它們是生理生態毒理學中廣泛研究的對象[17]。由于對多環芳烴結構和氯代聯苯結構的特異性應激反應,EROD被研究者廣泛用于檢測水生生態系統中此類環境污染物存在的酶學生物標志物。
3.1.2 EDCs對EROD的影響
EROD是細胞色素P-450依賴的MFO系統中的一員[18],生物體一旦受到脅迫,EROD活性與特定內分泌干擾物存在時間-效應和劑量-效應關系。多齒圍沙蠶(Perinereisnuntia)的實驗指出,在全氟辛烷磺酰基化合物(perfluorooctane sulfon-Ate,PFOS)的脅迫下,EROD酶活性隨時間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這與食蚊魚(Gambusiaaffinis)污水暴露實驗中,EROD酶活隨污染物濃度變化的趨勢類似[19,20]。在斑馬魚(Daniorerio)的暴露實驗中,阿特拉津毒性脅迫強度與EROD酶活存在先誘導后抑制的關系。這說明外源有機污染物對EROD酶活性的誘導是有限度的,在一定濃度與暴露時間內,EROD酶活被誘導,隨著外源有機污染物及其代謝產物在生物體內蓄積,超出機體承受的限度,肝細胞中的酶系統遭受毒性影響而失活;也可能是代謝過程中脂質過氧化物的增強導致細胞色素P-450的構型不穩定而發生變化[20,21],從而降低EROD酶活力水平。但黑鯛(Sparusmacrocephalus)實驗指出暴露在不同濃度苯并(a)芘(Benzo(a)pyrene,BaP)溶液中,肝臟EROD活性均出現了先升高后降低再升高的變化趨勢,這有可能是脅迫初期肝細胞EROD受外源有機污染物的刺激迅速被誘導,隨著脅迫濃度升高及其BaP代謝產物的積累,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脂質過氧化抑制EROD水平,脅迫后期可能是黑鯛自身的免疫防御系統發揮作用使EROD活力水平再升高,這種情況說明脅迫濃度只要不超出黑鯛自身恢復能力的范圍,機體可通過自身修復系統恢復至正常水平[22]。
3.2 對Ⅱ相解毒系統抗氧化酶系的影響
3.2.1 抗氧化防御系統發生機制
生物抗氧化防御系統可由兩大類組成:1)抗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SOD)、過氧化氫酶(CAT)以及谷胱甘肽-S-轉移酶(GST)等;2)非酶抗氧化劑:脂維生素E、維生素C、谷胱甘肽等[23]。抗氧化防御系統產生效應,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機體在代謝過程中抗氧化與氧化系統始終處于動態平衡狀態,但在環境污染物脅迫下,機體內活性氧自由基暴發,造成氧化損傷,因此,抗氧化防御系統激活,抵御機體產生的氧化應激。SOD是防御系統的第一道防線,能將超氧基陰離子轉化為H2O2,但H2O2又會反作用抑制SOD活性;因此,由CAT等組成的第二道防線催化H2O2還原生成H2O等[24];其二,GST可作為Ⅱ相解毒酶,既能催化還原性谷胱甘肽(GSH)的巰基(-SH)與外源性有毒物質形成親電子試劑對機體解毒,又能清除內源具遺傳毒性的不飽和醛從而降低污染物毒性[25]。
3.2.2 EDCs對抗氧化防御系統的影響
EDCs對抗氧化系統的影響處于一個動態變化中,在EDCs的脅迫下,抗氧化酶的含量被誘導或被抑制,這與EDCs的濃度和種類及暴露時間的長短等密不可分。由于SOD作為檢驗水生生物氧化損傷較為靈敏的酶,GST具有解毒酶和抗氧化酶雙重功能,因此這兩者在機體解毒過程的重要作用引起廣泛關注。錦鯽暴露多氟代二苯并對二噁英(PFDDs)實驗中,SOD活性在暴露3天時顯著抑制,在14天時逐漸恢復并較對照組略有增加[26],這與梭魚(Mugilsoiuy)暴露于BaP和芘的實驗中肝臟SOD活性先抑制后誘導的效應基本一致[27],這種效應發生可能是脅迫初期機體受到污染物刺激時迅速反應產生氧化應激,脅迫后期SOD活性較處理組略有誘導,這種現象符合抗氧化酶防御機制中的“自適應階段”,即抗氧化酶此時發揮維持機體生理生化平衡的作用導致SOD酶活恢復[26]。但PFOS脅迫多齒圍沙蠶實驗中,SOD活性在脅迫初期快速誘導,脅迫后期被抑制[28];翡翠貽貝(Pernaviridis)暴露四溴雙酚A(Tetrabromobisphenol A,TBBPA)的毒性實驗中,GST在暴露初期活性持續增加,暴露后期明顯抑制[29]。斑馬魚(Daniorerio)實驗中,E2、鄰苯二甲酸二甲酯(Dimethyl phthalate,DMP)、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ibutyl phthalate,DBP)、鄰苯二甲酸二辛酯(Dioctyl Phthalate,DOP)四種環境雌激素導致SOD、GST活性呈現低濃度誘導,高濃度抑制的現象[30]。其他研究也得出了SOD和GST活性在環境因子輕度脅迫下誘導、重度脅迫下抑制的結論[31-33]。說明在污染物暴露初期,SOD和GST在生物體內分別發揮抗氧化和解毒功能,而在暴露后期活性氧自由基(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以及外源有機污染物毒性蓄積過高,導致機體抗氧化防御系統異常,相關的一系列酶活受到抑制。
4 EDCs對DNA的損傷效應
4.1 EDCs對DNA損傷機制
EDCs污染可造成核酸受損,常見的DNA損傷包括生成加合物、鏈斷裂、堿基突變錯配及脫堿基位點等[34]。目前認為DNA損傷機制可能有3類:(1)外源有機污染物經體內I相酶系代謝活化所生成的中間活性產物可與機體內的生物大分子(主要為DNA)共價結合形成穩定加合物;(2)機體自發或外源性有機污染物(如PCBs、農藥等)經I相和II相酶系代謝誘導產生大量的ROS,一旦ROS產生超過機體消除能力或機體抗氧化防御能力減弱,觸發氧化應激反應,引起氧化性DNA損傷[35];(3)通過調控DNA分子自我修復系統相關因子的蛋白表達量達到抑制DNA分子修復的目的。
4.2 EDCs對DNA的損傷效應
早期有研究表明,PAHs代謝過程中產生的活性氧自由基能攻擊DNA,導致DNA單鏈斷裂或形成不穩定的無嘌呤的加合物[36]。PAHs的雙環氧類代謝產物易結合于DNA形成穩定加合物[37]。大量研究證實,BaP是間接致癌物,經I相酶代謝激活后產生7,8-二氫二羥基-9,10-環氧化苯并(a)芘(benzo[a]pyrene-trans-7,8-diol-9,10-epo-xide,BPDE),與鳥嘌呤共價結合形成DNA加合物,從而導致核苷酸的替代、缺失和染色體的重排,引起DNA分子損傷[38],若DNA自我修復系統不能及時使受損DNA分子迅速恢復正常,細胞很有可能發生癌變。褐昌鮋(sebastiscusmarmoratus)實驗表明,不同濃度的BaP與肝臟DNA單鏈斷裂損傷基本呈線性的劑量—效應關系[39]。在TBBPA暴露翡翠貽貝亞慢性毒性實驗中,TBBPA與DNA的損傷呈現良好的時間-效應和劑量-效應關系[29]。在鯉魚(Cyprinuscarpio)實驗中,濃度為25 μg/L和47 μg/L的二苯并(a,h)蒽(Dibenzo(a,h)anthracene,DbA)可使鯉魚的DNA損傷分別增加2.7倍和3.8倍[40];有研究表明暴露BaP會導致貽貝、比目魚和幼鱸魚的DNA損傷和基因毒性增加[41,42];暴露在BaP和苯并(K)熒蒽中時,隨著暴露濃度的增加,鯉魚DNA損傷隨之增強[43,44]。目前大量研究證明,內分泌干擾物會對基因水平產生脅迫,同時這也意味DNA損傷可以作為生物分子標記物來評價污染物脅迫的狀況。
5 展望
近年來,一些學者已就EDCs對水生動物生殖生理毒性進行了探討,并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是在水生生態系統中,生物多樣性復雜,EDCs種類眾多,不同的EDCs對生物體的毒性作用可能相互影響,表現出協同、拮抗、相加和獨立等不同毒性效應。如何全面了解污染物對生物體的聯合毒性作用、探討不同EDCs毒性之間的干擾機制將是未來研究的重要內容;雖然已有研究表明EDCs可對EROD酶活性產生顯著影響,但其具體的調節機制還有待于深入研究;如何從分子水平揭示EDCs對水生動物毒性作用及其調控機制也是需要我們進一步研究的熱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