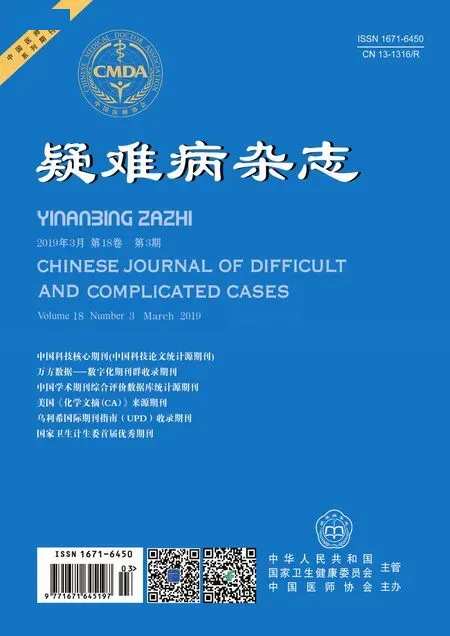結締組織病相關性假性腸梗阻的研究進展
王也綜述 聶英坤審校
假性腸梗阻(intestinal pseudo-obstruction,IPO)是指因消化道臟器平滑肌、腸道神經或消化道臟器自主神經病變引起的腸梗阻癥狀和體征,但無機械性梗阻證據和影像學特征的綜合征。按照病因分類可分為:原發性IPO及繼發性IPO,相比于繼發性IPO,原發性IPO更為罕見。結締組織病(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s,CTD),如系統性紅斑狼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LE)、系統性硬化癥(Systemic sclerosis,SSC)、炎性肌病、重疊綜合征等,以及進行性肌營養不良、淀粉樣變、彌漫性淋巴浸潤、帕金森病、黏液水腫、嗜鉻細胞瘤、阿片類藥物等常為繼發性IPO的主要原因[1]。按照臨床表現可分為急性IPO和慢性IPO。急性IPO是指在診斷前6個月以內出現≥1個及以上的IPO臨床癥狀。而慢性IPO是指從癥狀出現到診斷時間>6個月。常見癥狀包括吞咽困難、胃食管反流、胃腸道動力減退所引發的腹痛、腹脹、惡心、嘔吐、腹瀉、便秘和不明原因的體質量減輕[2]。CTD相關性IPO的診斷往往為CTD(主要為SLE和SSC)確診后的排除性診斷,首先根據有無蛋白尿、白細胞減少、皮膚改變、雷諾現象等,患者應進行抗核抗體、抗 dSDNA 抗體及補體等有關實驗室檢查以確定有無結締組織病。然后根據影像學檢查確定診斷。腹部立位 X線片檢查可見腸腔明顯擴張積氣,可見數個大小不等的液平面。腹部CT顯示腸管擴張,擴大的腸腔內積氣、積液,部分腸管管壁增厚[3]。 IPO是一種少見的并發癥,該病一般癥狀較為隱匿,臨床上容易發生誤診、延誤治療等情況。因此,本文就CTD的2個代表性疾病,系統性紅斑狼瘡、系統性硬化癥相關性IPO作一綜述。
1 系統性紅斑狼瘡(SLE)相關性IPO
SLE是一種可累及多臟器和系統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是凋亡清除受損、先天免疫和適應性免疫系統上調、補體激活、免疫復合物和組織炎性反應的復雜的相互作用的自身免疫過程,可累及人體多個器官和組織。SLE是一種世界性的疾病,發病以育齡期婦女為主。在15~44歲人群中,男女比例為1∶13,而在兒童和老年人中僅為1∶2[4]。本病存在種族特異性,非白種人發病率更高。雖然歐洲和美國的非洲人后裔的發病率較高,但SLE在非洲并不常見[5]。SLE的發病機制尚不完全清楚。現階段對SLE的研究表明其臨床發病需要遺傳易感性、環境沉淀物、免疫和激素因素的相互作用。在這種允許的環境中,伴隨著諸如1型干擾素和其他細胞因子等促炎性刺激,機體對自身抗原的免疫耐受性喪失。隨后,由凋亡廢物和免疫復合物的缺陷清除與中性粒細胞胞外陷阱、核酸傳感、淋巴細胞生物學破壞和干擾素途徑的復雜相互作用驅動自身免疫導致疾病的發生[6]。
1.1 SLE相關性IPO概述 IPO是SLE的一種罕見且目前研究較少的并發癥,國內外的一些研究表明[7-9],SLE相關IPO發生率為3.8%~5.2%。Mok等[10]的研究報道了18例SLE相關性IPO的患者,其中男性患者2例,女性患者16例,發病年齡15~47歲,中位年齡29.0歲,有12例合并雙側腎盂積水。侯勇等[11]報道了11例SLE相關IPO患者,男女比例為2∶9,發病年齡為11~42歲,中位年齡30.3歲,有10例泌尿系積水,其中2例為開始無尿路積水癥狀,隨病情的進展逐漸出現,此報道也說明了泌尿系梗阻積水。IPO可以發生于SLE活動期,亦可以發生于SLE低疾病活動期及穩定期。迄今為止的研究表明,IPO可發生在SLE的任意病程節點,而以IPO為首發癥狀的SLE更為少見。值得注意的是,除了IPO胃腸道的相應癥狀,SLE相關IPO還易出現腎盂及輸尿管積水等相關疾病。更罕見的是,在以前的病例報告中,發現膽總管擴張[12-13]。洪娜等[14]報道了10例,男女比例為2∶8,發病年齡16~69歲,中位年齡37.1歲。SLE相關性IPO的病例,其中以IPO為首發癥狀2例。
1.2 SLE相關性IPO發病機制 目前尚不清楚 , 可能與多種機制共同作用有關 : (1)免疫復合物介導的血管炎。有研究證明間質性膀胱炎的發病機制為膀胱壁的小血管炎,而SLE相關性的IPO常伴發有膀胱炎。Kim等[15]總結了19例SLE合并梗阻性腎病的病例,其中17例有間質性腎炎并有消化系統癥狀。這也可以從另外的角度證明血管炎在SLE相關IPO發病機制中的作用。有研究報道在SLE相關IPO患者腸和膀胱的血管壁上發現有免疫復合物的沉積, 免疫復合物在小血管壁的沉積導致慢性缺血, 最后導致腸道肌肉破壞和運動減慢。國內外均有報道手術切除的小腸病理顯示為血管炎改變[16];國內學者研究表明合并胃腸道癥狀的 SLE 患者合并雷諾綜合征及腎盂輸尿管擴張的概率明顯高于無胃腸道癥狀的 SLE 患者。而其他臨床表現如骨骼肌受累、腎炎、皮膚黏膜受累等,兩者間則沒有明顯差異。合并有雷諾綜合征、低補體血癥及 ANCA 陽性的 SLE 患者更容易并發胃腸道癥狀,這說明胃腸道癥狀可能是由胃腸道血管炎所致[17]。(2)內臟疾病和內臟神經病變。IPO 和輸尿管腎盂積水同時發生,提示上述改變可能與平滑肌病變有關。導致平滑肌病變的原因可能為原發于肌肉或者內臟神經的自身免疫性損害 , 如抗平滑肌自身相關抗體所致。在國內外的研究中,在伴有IPO和/或輸尿管腎盂積水的狼瘡患者中未發現特異性自身抗體;然而,少數研究報道抗SSA抗體陽性率高[13]。 Xu等[18]研究表明在伴有IPO和/或輸尿管腎盂積水的狼瘡患者中有78.7%患者具有抗SSA抗體,明顯高于無IPO和輸尿管腎盂積水SLE患者,說明抗SSA抗體可能在肌動力障礙中有病理作用。關于SLE相關性IPO更多的發病機制還在進一步研究,更多的觀點被提出,包括腸壁廣泛的肌炎、肌細胞壞死導致腸壁肌層和固有層萎縮和纖維化,小血管炎累及腸壁神經叢等[10]。
1.3 SLE 合并 IPO治療 關于SLE相關性IPO如何治療,目前尚沒有指南。應根據患者IPO是否為初發,病變是否在進展期,全身其他器官是否有活動表現等情況進行個性化治療。當然,對癥治療如禁食、胃腸減壓、靜脈高營養、糾正水電解質紊亂、控制感染等同樣重要。激素和免疫抑制劑為治療的主要藥物[19]。早期強調給予足量激素行免疫抑制治療,病情較重者每日可予甲潑尼龍1 g/次沖擊治療,連續3 d。免疫抑制劑主要為環磷酰胺、硫唑嘌呤及環孢素等,多數患者經激素及免疫抑制劑治療后病情可緩解。另外,IPO屬于功能性腸梗阻,原則上應盡量避免手術治療。有文獻報道,術后若出現腸麻痹可加重腸道運動功能障礙,并誘發 SLE 活動,使病情惡化而危及生命。但IPO繼發腸穿孔、出血或進展為腸絞窄時應立即行手術切除壞死腸管,以挽救患者生命。
2 系統性硬化癥 (SSC) 相關性IPO
SSC是一種慢性、發病率比較低的結締組織疾病,發病年齡通常在20~50歲,少數可見于10歲以下的兒童。患者以女性較多, 男女比例約為1∶3。此比例因年齡不同而異,15~44歲年齡組男女比例為1∶15,45歲以上年齡組男女比例為1∶1.8。SSC具有3個主要特征:早期微血管閉塞性改變,早期免疫系統活化伴T細胞和B細胞活化,皮膚和內臟器官廣泛纖維化。SSC患者的皮膚活組織檢查揭示T細胞和B細胞在疾病過程中的早期浸潤,但隨著疾病進展,炎性浸潤減少至消失,纖維化在組織學圖像中占主導地位[20-21]。SSC 的發病機制尚不完全清楚,但免疫激活和微血管病變可能導致纖維化的發生。
2.1 SSC相關性IPO概述 同SLE相關性IPO相似,IPO是 SSC患者住院的罕見原因,但與其他 SSC患者和繼發于其他原因的假性腸梗阻患者相比,院內病死率高[22]。Muangchan等[23]的文獻系統綜述顯示,腸道假性梗阻的合并患病率為3.9%(局限性皮膚系統性硬化癥為3.4%,彌漫性皮膚系統性硬化癥為 4.6%)。更早的一項大型 SSC患者隊列的研究顯示,IPO 患病率為 8%,預后極差,隊列中3年生存率為21%[24]。
2.2 SSC小腸受累的主要特征 其主要特征是低運動性,表現為振幅降低,慢速傳播或缺乏遷移運動復合物[25-26]。低運動發病機制涉及微血管損傷、自主神經功能紊亂、肌肉萎縮、纖維化和自身抗體產生。組織學的研究提示微血管損傷和重復性缺血可能在腸道受累的早期階段發揮重要作用[27]。然而,國外的一項SSC尸檢研究表明,血管內膜增殖與平滑肌萎縮無關,SSC中的自身抗體導致自主神經功能障礙可能為真正導致IPO的原因[28],因為它們抑制了M3- 毒蕈堿受體 (M3-R) 介導的腸道膽堿能神經傳遞[29]。這種抗體被動轉移到大鼠模型中會導致正常腸道肌電活動的破壞。Kumar 等[30]發現抗 M3-R 自身抗體最初阻斷肌間神經元的膽堿能傳遞,隨著疾病的進展,它們阻斷平滑肌細胞的運動傳遞。神經生理學的研究表明:神經源性紊亂(異常增殖的階段性收縮)先于小腸的肌源性(低運動性)紊亂[25-26]。此外,組織學研究表明,SSC患者腸道平滑肌早期結構正常,但逐漸出現萎縮、碎裂和萎縮[27]。由于上述各種原因引起了小腸的運動不足,隨后腸內細菌過度生長,進一步可導致IPO。持續的細菌生長和腔內壓力增加引起的IPO甚至可引起敗血癥或腸氣囊腫。
2.3 SSC相關性IPO治療 SSC相關性間質性肺病和肺動脈高壓的治療策略由于免疫抑制劑和血管擴張劑的出現而得到發展,但對SSC相關IPO管理的有效干預措施的指南尚未提出。與SLE相關性IPO不同,SSC相關性IPO并不主張使用大劑量糖皮質激素和免疫抑制劑,而對癥支持治療被普遍應用。急性假性腸梗阻是內科急癥,需入院治療。大多數患者采用內科保守治療,如腸道休息、鼻胃減壓、靜脈水化、糾正電解質紊亂等。如無反應,則加用抗生素和促動力藥,包括奧曲肽[31]。但值得注意的是,奧曲肽的治療也同樣存在一些缺點,包括對胃排空、胰腺分泌物、膽囊收縮的抑制作用和膽石癥發生率增加[32]。對于危重的患者,全腸外營養 (TPN) 可以挽救無法維持足夠營養狀態的患者的生命[33]。與SLE相關性IPO一樣,SSC相關性IPO同樣為全身性疾病,手術有增加腸梗阻或吻合失敗的風險,加之SSC患者本來也為手術及麻醉的高危人群,因此一般不主張外科手術治療[34]。
近些年報道的一些個案,給內科保守治療效果不佳的患者治療提供了一些新思路。Zhang[35]報道了1例系統性硬化癥—多發性肌炎重疊綜合征伴難治性假性腸梗阻的患者,經靜脈注射丙種球蛋白得以明顯臨床緩解,并表明病情的緩解可能與靜脈注射丙種球蛋白后腸道菌群的正常化有關。Nunokawa等[36]報道了1例SSC相關的IPO晚期階段通過胃造瘺術長時間安裝長管管理幾乎失去自主功能的腸道,使病情得以緩解的病例。
總之,IPO是CTD的罕見并發癥,癥狀常常比較隱匿,容易與其他胃腸道受累的疾病及服用藥物后的胃腸道不良反應相混淆,難以鑒別。治療也應根據不同的基礎疾病采取不同的方案。進一步對其發病機制研究,早期認識和及時開始治療,才能恢復腸功能,緩解癥狀,預防并發癥,早期發現也可避免不必要的侵入性手術和其他手術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