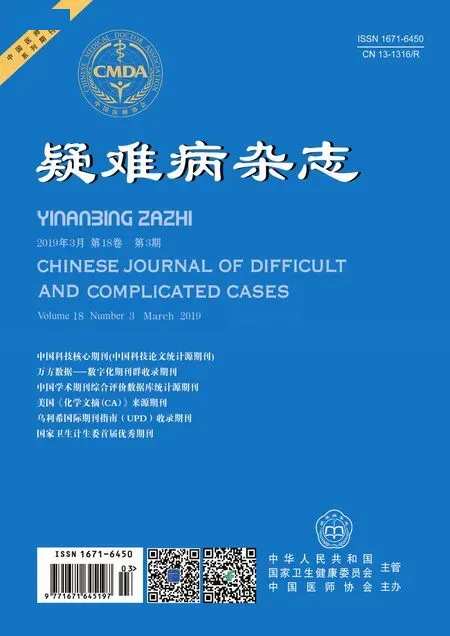直腸MR預測直腸癌新輔助放化療療效的研究進展
王尊綜述 付曠審校
結直腸癌是全球發病率和病死率較高的疾病之一[1]。我國近年結直腸癌發病率逐年升高,其中直腸癌患者占60%~70%[2]。隨著研究深入,直腸癌治療方案不斷改良,直腸癌新輔助放化療(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nCRT)等新輔助治療被廣泛應用,影像技術尤其是功能成像技術飛速發展,為直腸癌的檢出、評估及治療提供了強有力的幫助。
參考美國癌癥聯合委員會第8版TNM分期定義,直腸癌TNM分期中T分期用于評估腸管壁受侵程度:T1期為腫瘤侵犯黏膜及黏膜下層;T2期為腫瘤侵犯到固有肌層;T3期為腫瘤的漿膜下受侵;T4期為腫瘤突破漿膜, 又分為T4a和T4b期。N分期和M分期分別反映淋巴結受累情況和遠處轉移情況,其中N0期指無淋巴結轉移;M0期指無遠處轉移。我國大多直腸癌患者初診時即為局部進展期直腸癌(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LARC)[3]。nCRT作為LARC的標準治療模式可以提高直腸癌患者的手術切除率、保肛率、局部控制率,達到延長無病生存期的目的,有效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但并不是所有符合適應證的患者都可以從nCRT中獲益,有的甚至造成了不必要的損傷。所以尋找能夠區分出放化療敏感患者的指標是臨床的關注點之一。直腸MR借助其高軟組織分辨率的優勢,能更好地顯示腫瘤周圍浸潤及直腸壁改變情況,可以更直觀地為醫療工作者提供決策支撐,為直腸癌患者制定最優診療方案。本文對各直腸MR技術在治療前預測直腸癌新輔助放化療療效方面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
1 直腸影像技術概述
評估直腸癌進展的醫學手段,除了直腸指檢、腸鏡檢查和病理檢查外,主要是一些影像檢查技術。超聲技術的特點是善于判斷對腸壁的浸潤深度,但是當占位過大時對全局的顯示并不好。2018年的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絡(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直腸癌指南較上版做了些改動,對T1~T2及N0期的直腸癌患者不再首推直腸內超聲(除非患者存在MR禁忌證,如體內置入非順磁性心臟起搏器等),認可了直腸MR對浸潤深度和局部淋巴結轉移的判斷能力。CT技術也常應用于直腸癌中,其在判定直腸癌遠處轉移方面有較好的直觀性,但在腫瘤周圍浸潤及直腸壁結構方面的顯示卻有限。PET-CT/MR檢查通常不作為常規的直腸癌檢查手段,多在懷疑存在多發遠處轉移時考慮使用。直腸MR技術借助其高軟組織分辨率的優勢,更好地顯示了腫瘤周圍浸潤及直腸壁改變情況,且其無痛無創無放射性損失,隨著近年科技進展得以迅速發展,成為直腸癌臨床診治及全面評估預后最有效的影像技術。2018版NCCN直腸癌指南推薦使用MR技術作為評估直腸腫瘤的影像學標準檢查。
2 直腸MR在預測nCRT療效方面的研究價值
臨床方面,對于初診為T1~T2期的直腸癌患者是否應該行術前的新輔助治療存在爭議,但目前的臨床研究證據和NCCN臨床治療指南推薦:初診為T3~T4期和/或存在淋巴結轉移的直腸癌患者,排除治療禁忌證后,應先進行nCRT等新輔助治療。但是在診治過程中,對于是否所有符合適應證的患者都適合行nCRT這個問題并沒有滿意的答案。一方面,nCRT作為局部進展期直腸癌的標準治療模式可以提高直腸癌患者的手術切除率、保肛率、局部控制率,從而達到延長無病生存期的目的,有效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符合適應證的患者都可以從nCRT中獲益,有的患者反而因新輔助治療的不良反應遭到了不必要的損傷。所以尋找能夠區分出對放化療敏感的患者的指標是臨床的關注點之一。
2.1 常規直腸MR與高分辨率小視野MR 常規直腸MR主要利用斜軸、矢、冠狀位的T2加權像及軸位T1加權像反映直腸及盆腔情況,是目前最基礎的序列選擇。高分辨率小視野MR利用比常規直腸MR更小視野、更薄層的T2加權序列成像,獲得高分辨率的局部腸管的斜軸位圖像,有利于呈現腫瘤的浸潤深度、肛提肌與腫瘤的位置關系、括約肌復合體與腫瘤(尤其是低位直腸癌)的位置關系,為后期的手術提供更詳盡的關鍵解剖信息[4]。
有研究指出,對于腹膜反折以下的中下段直腸癌,可以通過在nCRT前的MR圖像上測量腫瘤最外側邊緣與固有肌層外緣之間的最大距離來預測nCRT后的不完全緩解,預測的最佳閾值為5.6 mm,還發現該參數與治療后的腫瘤消退情況和是否存在降期并沒有相關性[5]。
2.2 擴散加權成像 擴散加權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 技術目前臨床應用比較廣泛[6]。其參數表觀擴散系數(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 能通過反映水分子擴散,來反映組織的微觀結構特點。
Chen等[7]和Xie等[8]認為nCRT治療前的DWI可以用于預測nCRT療效,且治療前平均ADC值對病理完全緩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 pCR)的預測效果最好。多項研究還發現治療前腫瘤區域的ADC值越高,nCRT的療效越差[6,8]。這或許與對放化療不敏感的直腸癌腫瘤組織內存在較多壞死組織有關,因為壞死部位局部缺氧、灌注減低的環境不利于放化療發揮作用。
與之相反,多項研究認為治療前ADC值不能預測nCRT療效;有研究發現其與治療后病理腫瘤消退情況無顯著相關性;還有研究發現其在治療后pCR組與非pCR組之間無顯著差異[9-11]。
兩方結論不同可能與研究者不同的實驗設計方案以及參考的病理學標準存在差別有關,還有很大可能是選取的感興趣區勾畫方法不同,當然觀察者之間的差異性和入組標準的偏差更是不可避免的[3]。
2.3 體素內不相干運動擴散加權成像 體素內不相干運動擴散加權成像(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IVIM-DWI)在DWI序列基礎上利用雙指數模型進行計算,可以得出能反映微血管灌注和活體組織內水分子擴散的相關參數[12],主要參數包括擴散系數(D)、假性擴散系數(D*)和灌注分數(f)。IVIM-DWI對真假灌注的區分彌補了DWI的不足。
研究發現IVIM-DWI可以用來反映LARC患者nCRT后的組織病理學腫瘤消退分級情況[12]。治療前具有高f值的患者有良好的腫瘤消退表現(特異性100%),且聯合治療前f和腫瘤體積的比值對療效不佳有最好的預測價值,而治療前的ADC值不能反映出nCRT療效。信超等[13]發現, pCR組nCRT前腫瘤區域D*值低于非pCR組。所以治療前使用雙指數模型處理多b值DWI序列有利于提高預測療效的能力。
2.4 擴散峰度成像 擴散峰度成像(diffusional kurtosis imaging,DKI)技術是一種源于DWI又脫胎于DTI的新MRI技術。DKI需要使用更高值的擴散敏感因子(b)[9],利用當b大于1 000 s/mm2時可更好地反映活體組織內水分子的非高斯分布擴散運動的特點而成像,通過相關參數定量分析水分子擴散的運動方向及能力,更準確地反映組織結構和病理生理的變化情況。DKI主要參數包含Dapp及Kapp ,最常用的成像參數為平均峰度(mean kurtosis,MK)和平均彌散率(mean diffusivity,MD)
有研究發現用DKI在治療前預測哪些LARC患者有好的nCRT療效是可行的,且效果優于DWI。Yu等[10]發現nCRT后腫瘤消退顯著組的定量參數Dapp的第10百分位數較療效差組低,而Kapp和ADC值與病理腫瘤消退情況則無顯著相關性。這一結果可能與腫瘤組織的局部壞死或者細胞喪失完整性有關,因為這樣的組織往往血流灌注差,導致nCRT所用的化療藥物難以施展藥效;同時,這樣的組織往往局部處于缺氧的環境中,缺氧的微環境會使放療及化療產生抵制,影響療效。Hu等[9]發現,pCR組治療前測得的腫瘤區域MK顯著低于非pCR組,但是治療前2組腫瘤區域的MD和ADC值差異并不明顯。
2.5 動態增強磁共振成像 動態增強磁共振成像(dynamic contrast-enhanced MR,DCE-MR)是最常用的磁共振灌注成像技術。運用Tofts模型分析采集的圖像數據,獲得動態灌注的信號強度時間曲線,可算出反映組織結構生理特性的參數[14],如容積轉運參數Ktrans、反映回流速率參數Kep、細胞外血管外間隙容積比Ve等定量參數,及曲線下初始面積iAUC、達峰時間TTP等半定量參數。其中,Ktrans是DCE-MR反映血管通透性最常用的參數。
許多研究發現直腸癌患者nCRT治療前的DCE-MR參數可以通過反映治療后pCR的可能性來預測nCRT的療效。Tong等[15]發現, pCR組的平均治療前Ktrans明顯高于非pCR組的,且Ktrans閾值為0.66時擁有100%的區分度,還發現在同期Kep和Ve方面, pCR 組和非 pCR 組之間也存在顯著差異。De Cecco等[16]同意Ve的預測價值,推薦使用Ve≤0.311作為預測良好反映的影像學指標。這或許與DCE-MR參數能體現血流動力學及血管的通透性變化從而反映腫瘤組織灌注情況及血管結構的完整性有關。
還有研究發現,對于nCRT前的直腸癌患者,DCE-MR的定量參數與半定量參數之間有很強的相關性。因此,半定量的分析可作為定量分析的替代品[14]。
2.6 影像組學 影像組學通過對圖像信息進行自動提取與數據挖掘,綜合統計分析影像結果,為疾病診斷、治療和預后評估提供有效的數據支撐。提取放射影像特征不僅包括腫瘤的部位、大小、形態等基礎數據,也包含肉眼很難分辨的病變組織異質性數據。該技術應用于直腸癌領域的主要是紋理分析。紋理分析是量化放射影像圖像像素、組織空間結構及分布的一種技術,通過提取圖像粗細不同的紋理,軟件分析得出緊密度(compactness)、對比度(contrast)、相關性(correlation)、直方圖峰態(kurtosis)、混雜程度反應值(entropy)、能量(energy)、均勻度(homogeneity)和感興趣區內像素灰度值均值(mean)等參數。
隨著影像組學技術的推廣,許多研究發現利用影像組學技術尤其是紋理分析處理nCRT前MR的多種圖像,有利于預測治療療效。
Hsu等[17]發現在預測術前同步放化療療效方面,基于治療前T2加權像和DCE-MRI圖像進行紋理分析時,比起體積參數,腫瘤的緊密度參數是更好的選擇,更適合參與構建預測治療后pCR的模型。
還有研究發現基于治療前T2加權像的紋理分析可以用于預測直腸癌患者nCRT的療效,舒震宇等[18]發現pCR組患者治療前腫瘤區域的混雜程度反應值高于同期非pCR組;還發現在nCRT中期,混雜程度反應值>5.983 對pCR有最佳的預測效果,靈敏度為 100%,而能量<0.010對腫瘤無消退反應的預測有最佳效果。所以認為nCRT中期是進行預測的最佳時間段。De Cecco等[16]則發現pCR組的治療前直方圖峰態參數顯著低于非pCR組,區分最理想的閾值為直方圖峰態≤0.19 (100%的敏感度)。
與之相似,劉思野等[19]發現nCRT前IVIM-DWI圖像的紋理特征可用于預測pCR,特別是二級紋理特征。應用多變量分析發現DifVarncD和SumVarncD*為獨立預測因子。
Liu等[20]發現基于治療前ADC圖的紋理分析有助于識別對nCRT無反應的LARC患者。
3 小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直腸癌患者治療前直腸MR尤其是功能MR對于預測直腸癌患者nCRT療效有一定價值,可以用于篩選對nCRT敏感的直腸癌患者,在制定個體化治療方案上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雖然關于DWI和ADC的研究結論不一,但DCE-MR和DKI技術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一致性進展,只是具體的測量時間點和閾值設定仍需要進一步研究。隨著影像組學技術推廣,圖像的信息被進一步挖掘利用,在利用紋理分析技術預測療效方面也有不少新發現,可以為篩選獲益患者提供更多參考信息,經過進一步研究勢必可以為多學科團隊提供更多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