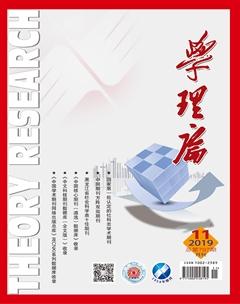關(guān)于亞里士多德的幸福的爭(zhēng)議與解決
摘 要:亞里士多德的“幸福”觀點(diǎn)到底是什么呢?學(xué)術(shù)界一直存在著爭(zhēng)議,余紀(jì)元先生認(rèn)為,這種爭(zhēng)議出現(xiàn)的根源就在于他們沒(méi)有能夠弄清楚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中究竟比較的是兩種生活還是兩種活動(dòng)。本文首先通過(guò)論述理論理性與實(shí)踐理性的關(guān)系,得出理論理性?xún)?yōu)于實(shí)踐理性的觀點(diǎn),并進(jìn)而得出通過(guò)二者獲得了兩種幸福且這兩種幸福的地位也是不同的觀點(diǎn)。其次,論述了由這兩種不同幸福觀所帶來(lái)的綜合論者和理智論者的爭(zhēng)論,并提出了自己對(duì)于亞里士多德的“幸福”的看法,最后通過(guò)引用余紀(jì)元先生對(duì)于亞里士多德的“幸福”的解釋來(lái)回應(yīng)這種爭(zhēng)論。
關(guān)鍵詞:理論理性;實(shí)踐理性;幸福
中圖分類(lèi)號(hào):B502.233?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589(2019)11-0056-02
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中將幸福理解為人的靈魂的有邏各斯的部分的實(shí)現(xiàn)活動(dòng),從這里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幸福的獲得與人的靈魂中的理性部分的作用密不可分。亞里士多德將人的靈魂劃分為有邏各斯的部分和沒(méi)有邏各斯的部分(即理性部分和非理性部分),同時(shí)又將非理性的部分分為兩種,一種是植物靈魂、另一種是包括欲望和情感在內(nèi)的非理性的部分,這個(gè)部分雖然不具有理性但是它卻能夠聽(tīng)從理性的指導(dǎo),并且具有倫理的含義而前者則不具有這種含義。理性部分分為理論理性和實(shí)踐理性?xún)蓚€(gè)部分,其中理論理性的德性是理論智慧,實(shí)踐理性的德性是實(shí)踐智慧。在前面我們提到過(guò)非理性部分中的欲望部分能夠聽(tīng)從理性部分的指導(dǎo),也就是聽(tīng)從實(shí)踐智慧的指導(dǎo),在這兩者的共同作用下我們可以獲得幸福。但是合乎于其他德性的生活是第二好的,因?yàn)檫@些德性的實(shí)現(xiàn)活動(dòng)都是人的實(shí)現(xiàn)活動(dòng),因此在《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的末卷,亞里士多德又提出了一種沉思的生活并認(rèn)為這種沉思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由此學(xué)界就對(duì)亞里士多德的“幸福”的理解存在著一些爭(zhēng)議,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當(dāng)屬綜合論和理智論的沖突,他們圍繞著自己的觀點(diǎn)各抒己見(jiàn),其觀點(diǎn)都具有合理之處,誰(shuí)也駁倒不了誰(shuí)。我國(guó)學(xué)者余紀(jì)元先生也看到了這種矛盾,但是他認(rèn)為這種矛盾之所以出現(xiàn)是因?yàn)樗麄儧](méi)能夠弄清楚亞里士多德是在何種意義上比較這兩種幸福的,如果我們從另外一個(gè)角度來(lái)理解亞里士多德的“幸福”的話(huà),這種矛盾就不會(huì)存在了。在論述余紀(jì)元先生的這種解決方案之前,筆者覺(jué)得我們有必要先來(lái)探討一下理論理性與實(shí)踐理性的關(guān)系,因?yàn)閬喞锸慷嗟滤f(shuō)的兩種不同的幸福是分別通過(guò)二者獲得的。
一、理論理性與實(shí)踐理性的關(guān)系
(一)理論理性與實(shí)踐理性的區(qū)別
理論理性與實(shí)踐理性這兩者之間既是有區(qū)別的同時(shí)又是相似的。當(dāng)談到理論理性與實(shí)踐理性這兩者的區(qū)別時(shí)人們首先想到的很可能是研究對(duì)象不同,理論理性研究的是必然的、穩(wěn)定的且不可改變的對(duì)象(如:自然真理),而實(shí)踐理性研究的則是與人相關(guān)的事物,是變動(dòng)的和不確定的,的確研究對(duì)象的不同可以成為我們區(qū)分理論理性和實(shí)踐理性的一個(gè)重要理由。由研究對(duì)象的不同人們自然而然地就推出了研究方法的不同,但是研究方法的不同并不足以成為我們區(qū)分實(shí)踐理性和理論理性的基礎(chǔ),這是因?yàn)橛袝r(shí)候它們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很可能是相似的。例如,這兩種理性都要以某種前提為基礎(chǔ)然后得出結(jié)論,在這種情況下它們都適用于同樣的邏輯推理規(guī)則,因此研究方法的不同不但沒(méi)能成為我們區(qū)分理論理性和實(shí)踐理性的理由,從另外一個(gè)角度看,對(duì)于這二者研究方法的討論還恰恰支持了我們下面將要講到的理論理性和實(shí)踐理性是相似的思想。
筆者認(rèn)為理論理性與實(shí)踐理性的真正不同之處在于:就理論理性與實(shí)踐理性的對(duì)象而言,它們所把握的“真”是不同的。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營(yíng)養(yǎng)和生長(zhǎng)能力是人的靈魂的一部分而理性也是人的靈魂的一部分,同時(shí)它還是一種生活能力、生活方式,我們將這種生活方式稱(chēng)之為“把握真”的生活方式。但是理論理性與實(shí)踐理性把握的“真”是有明顯差異的,其差異表現(xiàn)為:理論理性把握的是事物本然的真,它同實(shí)踐和制作沒(méi)有關(guān)系,理論理性的好與壞只在于它所獲得的東西是真的還是假的。實(shí)踐理性則不同,實(shí)踐的理智的活動(dòng)是獲得相應(yīng)于遵循著邏各斯的欲求的真。我們說(shuō)一個(gè)人可能有能力很好地把握理論理性中的真但是這并不能確保他也有能力很好地把握實(shí)踐理性中的真,原因就在于,人的靈魂中不僅包括理性的部分而且也包括非理性的部分,非理性部分受到理性部分的指導(dǎo),盡管非理性部分受到理性部分的指導(dǎo),但是理性部分也不能要求非理性部分的欲望絕對(duì)接受它的指導(dǎo),因此就可能出現(xiàn)不自制的現(xiàn)象,那么在這個(gè)時(shí)候人就不能很好地把握實(shí)踐理性中的真。
(二)理論理性與實(shí)踐理性的相似性
理論理性和實(shí)踐理性雖然是兩種不同的理性但是它們兩者之間存在著相似性,這種相似性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一方面是這兩種活動(dòng)的目標(biāo)(功能)是相同的,即:求真。盡管在前面我們已經(jīng)明確地提到過(guò)理論理性與實(shí)踐理性尋求的是本質(zhì)上不同的事物的“真”,但是就求“真”這種活動(dòng)的目標(biāo)來(lái)說(shuō)這兩種理性是相似的。另外一方面,這兩種理性的德性在某種意義上是相同的,在《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中亞里士多德說(shuō)過(guò)德性是由功能界定的,既然理論理性與實(shí)踐理性的功能都是求真,那么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shuō)理論理性與實(shí)踐理性的德性是一樣的。
由于合道德德性的活動(dòng)所把握的“真”是對(duì)自己和他人所要做的事情的“真”,是與人相關(guān)的,合理智德性的活動(dòng)所把握的“真”是自然界或更普遍世界的不可改變的方面的“真”,是關(guān)于最高存在物的“真”,但人并不是這個(gè)世界上最高等的存在物。因此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把握“真”這種活動(dòng)更完美地體現(xiàn)在理論智慧的實(shí)踐中,而實(shí)踐智慧則只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理論智慧完美地實(shí)現(xiàn)其理性活動(dòng)的思想,因此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理論理性?xún)?yōu)于實(shí)踐理性。既然理論理性?xún)?yōu)于實(shí)踐理性那么通過(guò)它們獲得的幸福的地位肯定也是不一樣的,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通過(guò)道德德性與實(shí)踐智慧的相互作用我們獲得了一種幸福,通過(guò)思辨我們又獲得了另外一種幸福。
二、亞里士多德的“幸福”存在的爭(zhēng)議
那么令我們困惑的問(wèn)題就出現(xiàn)了,即:亞里士多德的“幸福”的觀點(diǎn)到底是什么呢?是一個(gè)包括諸多善的“善的綜合體”呢[1]?還是一個(gè)高于其他一切善的最高善呢?在《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中亞里士多德并未給出答案,圍繞著這個(gè)問(wèn)題學(xué)術(shù)界展開(kāi)了討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綜合論和理智論的爭(zhēng)論。綜合論者認(rèn)為亞里士多德的“幸福”是一個(gè)復(fù)合體,其中包含了各種德性以及外在善,而在這種復(fù)合體中最為重要的成分就是德性;理智論者并不贊同綜合論者的觀點(diǎn),他們認(rèn)為亞里士多德的“幸福”并不是一個(gè)綜合概念,而是一個(gè)單一卻最完善的德性活動(dòng),即:思辨活動(dòng)[2]。思辨中含有最多我們所說(shuō)的完滿(mǎn)性,思辨的生活是最幸福的,其他的幸福都低于沉思的幸福且為沉思的幸福服務(wù)。筆者比較贊同綜合論者的觀點(diǎn),筆者也認(rèn)為亞里士多德所說(shuō)的幸福是一個(gè)包括諸多善的“善的綜合體”,其原因如下。
首先,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第一卷第七章中說(shuō)道:“幸福是完善的和自足的,是所有活動(dòng)的目的。”[3]“我們所說(shuō)的自足不是指一個(gè)孤獨(dú)的人過(guò)孤獨(dú)的生活,而是指他有父母、兒女、妻子,以及廣言之有朋友和同邦人,因?yàn)槿嗽诒拘陨鲜巧鐣?huì)性的。”[3]從這段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幸福是自足的,但他說(shuō)的這種自足不是一個(gè)離群索居的人所具有的自足,而是說(shuō)這個(gè)人要處在一定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中、滿(mǎn)足了各種社會(huì)關(guān)系要求之后的自足,因此一個(gè)只過(guò)沉思生活的人并不符合亞里士多德所說(shuō)的自足要求。
其次,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第六卷第十三章中說(shuō)道:“然而,明智并不優(yōu)越于智慧或理智的那個(gè)較高部分。這就像醫(yī)學(xué)不優(yōu)越于健康一樣。醫(yī)學(xué)并不主導(dǎo)健康,而是研究如何恢復(fù)健康。”[3]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明智與智慧之間存在著等級(jí)關(guān)系,明智是靈魂中理性計(jì)算部分中最高的德性,而智慧是靈魂中科學(xué)部分的德性,是最高等的德性,明智之于智慧的作用就如同醫(yī)學(xué)之于健康一樣,明智并不支配智慧而是幫助智慧得以實(shí)現(xiàn),明智是智慧的充分不必要條件。同時(shí)明智統(tǒng)攝著所有的道德德性,而一個(gè)擁有智慧的人一定又是一個(gè)擁有明智的人,那么從這個(gè)意義上講,一個(gè)過(guò)沉思生活的人必定是擁有明智以及各種道德德性的人。
最后,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第十卷第八章中說(shuō)道:“但是一個(gè)沉思的人,就他的這種實(shí)現(xiàn)活動(dòng)而言,則不需要外在的東西。而且,這些東西反倒會(huì)妨礙他的沉思。然而作為一個(gè)人并且與許多人一起生活,他也要選擇德性的行為,也需要那些外在的東西來(lái)過(guò)人的生活。”[3]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亞里士多德認(rèn)為就沉思這種活動(dòng)而言,一個(gè)人是不需要太多外在東西的,因?yàn)樗ㄙM(fèi)在處理外在東西的時(shí)間越多他就用于沉思的時(shí)間越少,外在的東西不僅不利于他的沉思而且還會(huì)阻礙他的沉思。但就他作為一個(gè)人而言,他不可能一直進(jìn)行沉思,他需要與其他人生活在一起過(guò)一種屬于人的生活,因此他必然會(huì)選擇外在的東西、選擇合德性的行為去支持他的生活,從而實(shí)現(xiàn)他作為人的屬性,即:滿(mǎn)足靈魂中欲求部分的要求。這也就是說(shuō)合德性的活動(dòng)已經(jīng)包含在沉思者的靈魂之中了,一個(gè)進(jìn)行沉思活動(dòng)的人可以隨時(shí)放下沉思而做合德性的活動(dòng)。
三、對(duì)亞里士多德的“幸福”存在的爭(zhēng)議的解決
余紀(jì)元先生認(rèn)為綜合論者和理智論者都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場(chǎng)上為自己辯駁,但他們誰(shuí)也駁不倒誰(shuí),因?yàn)樗麄兌紱](méi)能夠搞清楚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中對(duì)兩種生活進(jìn)行比較時(shí)究竟是在何種含義上進(jìn)行比較的,即:亞里士多德比較的僅僅是兩種純粹的生活呢?(一種是完全沒(méi)有思辨活動(dòng)參與的生活,另一種是完全沒(méi)有道德德性參與的生活)還是說(shuō)他其實(shí)比較的是混合了思辨活動(dòng)與道德德性這兩種成分的生活,只不過(guò)其中的一種成分占得多一些而另外一種成分占得少一些而已[2]?他認(rèn)為只有搞清了這個(gè)問(wèn)題我們才能準(zhǔn)確地理解和把握亞里士多德所說(shuō)的幸福。
余紀(jì)元先生在《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中先是區(qū)分了幸福生活與幸福活動(dòng)、思辨生活與思辨活動(dòng)的不同,然后又提出自己的觀點(diǎn),即:他認(rèn)為亞里士多德比較的不是兩種不同的生活而是比較了兩種不同的活動(dòng)(思辨活動(dòng)和體現(xiàn)道德德性的活動(dòng))。首先我們來(lái)看一下他對(duì)幸福生活與幸福活動(dòng)是如何區(qū)分的,他認(rèn)為在《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中亞里士多德既說(shuō)幸福是一種生活同時(shí)也說(shuō)幸福是一種活動(dòng),比如他在第十卷第七章中說(shuō)道:“如果幸福在于合德性的活動(dòng),我們就可以說(shuō)它合于最好的德性,即我們的最好部分的德性。”[3]在這里亞里士多德很明顯地將幸福當(dāng)成了一種活動(dòng),一種合乎最好德性的活動(dòng),這種最好德性的活動(dòng)不僅有利于我們幸福的實(shí)現(xiàn)而且其自身也是好的。而當(dāng)他說(shuō)幸福是活的好的時(shí)候,幸福就是一個(gè)包含了各種德性和外在善在內(nèi)的綜合概念,因?yàn)榛畹煤檬蔷鸵环N生活整體來(lái)說(shuō)的。從幸福生活與幸福活動(dòng)的區(qū)分中我們可以看到,綜合論者和理智論者都各自只抓住了這兩種含義中的一種,而忽略了另一種。
此外他還認(rèn)為思辨生活與思辨活動(dòng)也存在著區(qū)別。思辨活動(dòng)是靈魂的理論理性部分的活動(dòng),它是最高的和自足的,當(dāng)一個(gè)人在進(jìn)行這種思辨活動(dòng)時(shí)他不僅不需要外在的東西來(lái)支持這種活動(dòng),而且外在的東西很可能會(huì)阻礙他的這種活動(dòng)。思辨生活則不同,思辨生活是人作為肉體和靈魂的混合物的生活,當(dāng)一個(gè)人過(guò)思辨生活時(shí)他可以將思辨活動(dòng)當(dāng)成自己思辨生活的本質(zhì)特征,但是他不可能僅進(jìn)行思辨這一種活動(dòng),作為一個(gè)人、作為整個(gè)社會(huì)中的一員,他還要與人溝通交流,去做體現(xiàn)德性的事情同時(shí)還需要各種外在善的幫助等等。
在比較了幸福生活與幸福活動(dòng)、思辨生活與思辨活動(dòng)之后,余紀(jì)元先生認(rèn)為綜合論者和理智論者都是先入為主地將幸福設(shè)定為一種活動(dòng),然后從各自的立場(chǎng)展開(kāi)論述。余紀(jì)元先生認(rèn)為亞里士多德比較的并不是兩種不同的生活而是兩種不同的活動(dòng),即:思辨活動(dòng)和體現(xiàn)道德德性的活動(dòng)。他認(rèn)為亞里士多德在《尼可馬可倫理學(xué)》第十卷第八章中說(shuō)的“合于其他德性的生活只是第二好的”[3],這里的“合于其他德性”很明顯指的是道德德性與實(shí)踐智慧而不包含理論理性在內(nèi),但我們知道理論理性是屬于人的靈魂中的理性部分的、是屬于人的,如果亞里士多德在這里指的是一種生活的話(huà)必定是要包含理論理性的,但實(shí)際上卻沒(méi)有將其包含在內(nèi),因此他在這里所談的“合于其他德性的生活”必定是一種活動(dòng)而不是一種生活[2]。當(dāng)我們認(rèn)為亞里士多德比較的是兩種活動(dòng)時(shí),我們就可以很自然地認(rèn)為思辨活動(dòng)是最大的幸福而體現(xiàn)道德德性與實(shí)踐智慧的活動(dòng)是第二幸福的,因?yàn)樵谇懊嫖覀円呀?jīng)提到過(guò)理論理性研究的對(duì)象是那些始終不變的事物,而實(shí)踐理性所研究的則是與人相關(guān)的變動(dòng)的事物,理論理性高于實(shí)踐理性,因此思辨活動(dòng)優(yōu)越于體現(xiàn)道德德性與實(shí)踐智慧的活動(dòng)。
對(duì)于亞里士多德所講的“幸福”到底是什么我們每個(gè)人可能都會(huì)有自己的見(jiàn)解,但是筆者認(rèn)為通過(guò)展示余紀(jì)元先生對(duì)于亞里士多德的“幸福”的理解為我們進(jìn)一步研究亞里士多德的幸福提供了一個(gè)重要的思路。
參考文獻(xiàn):
[1]于若冰.為屬人的幸福而運(yùn)思—淺析亞里士多德的幸福觀[J].現(xiàn)代哲學(xué),2012(5).
[2]余紀(jì)元.亞里士多德倫理學(xué)[M].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1.
[3]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M].廖申白,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17.
收稿日期:2019-05-30
作者簡(jiǎn)介:吳聰敏(1994-),女,河南長(zhǎng)葛人,碩士研究生,從事外國(guó)哲學(xu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