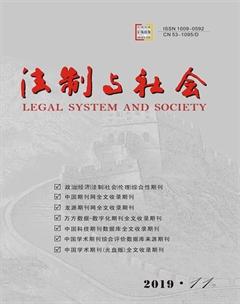反恐刑事訴訟中律師會見權
關鍵詞 恐怖活動犯罪 律師會見權 價值平衡
作者簡介:宗宣羽,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國際法學專業,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訴訟法、國際法。
中圖分類號:D9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11.163
一、反恐刑事訴訟中的律師會見權司法側供給不足
自國際反恐事件以來,恐怖主義活動進入各國的視線,國際恐怖主義已成為影響世界安全的突出因素,雖然我國的反恐刑事訴訟程序相對完善,但仍在訴訟人權保障方面還仍舊有發展的空間。就律師會見權保護來說,對司法體系一無所知的犯罪嫌疑人置身在各個國家機關的壓力之下,與律師的第一次會見就顯得尤為重要。如若我國能在嚴懲恐怖分子的基礎上全面地保障其訴訟權利,不僅對我國恐怖主義犯罪司法體系具有建設意義,同時還能提升我國在國際人權問題上的威信與地位。
但實際上,我國立法與司法方面仍然存在問題。刑事訴訟法規定,在反恐刑事訴訟程序中律師行使會見權需經過偵查機關批準,即是說偵查機關批準成了律師在提供“三證”之外的必要條件,而對于“什么時間再會見”與“能不能再會見”等相關問題并未明確規定,監督與救濟兩個方面未有提及,而由于恐怖犯罪的特殊性,對承接此類案件的律師的資格應進行相應規制,立法中也未明確說明;同時我國法律體系內洽性不足,法律中體現自由價值與安全價值無法有機協調。立法中的漏洞給司法實踐帶來了巨大壓力,律師會見難是最主要表現,現階段普通刑事案件的律師會見權都面臨困難境地,在司法實踐中,不僅辯護律師“會見難”,而且有關機關限制會見的次數和時間的做法并不鮮見。
在恐怖活動這種特殊類犯罪中,偵查機關出于國家利益和辦案效率的考慮很少在案件偵查結束前允許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 “有礙偵查”成為阻止律師會見的主要理由,如此環境下,會見權作為犯罪嫌疑人訴訟權利的基礎權利得不到保障,保護嫌疑人其他的權利也就變得十分渺茫。
二、反恐程序中的價值衡量
完善我國恐怖活動犯罪律師會權體系,明確刑事訴訟法律中價值平衡理論,是解決上述問題的重要前提。刑事訴訟法承載著我國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價值理念,刑訴中的相關條款也均體現了國家對犯罪嫌疑人刑事訴訟中的基本人權給予了肯定與保護,與此同時,不應忽略刑事訴訟法本身的基本功能,即懲罰犯罪、維護社會秩序的功能。保障人權與懲罰犯罪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前者是自由價值的體現,后者是秩序價值的縮影。各國所建立的反恐法律均是以各自利益為基點構建的,在自由價值與秩序價值的平衡與取舍問題上,各國審慎考量自身與外界因素,走出適合自己的道路。恐怖活動律師會見權就像是一組杠桿中的支點,平衡著法律的秩序價值與自由價值,在對恐怖活動犯罪律師會見權體系藍圖繪制的過程中,立法者應充分考量各方利益,借鑒司法經驗,平衡好基本價值,構建完善的恐怖活動特別訴訟程序。根據價值平衡理論可以從以下方面完善我國恐怖活動犯罪中律師會見權體系:在肯定現有立法的基礎上,從強調安全價值轉化為安全與自由價相協調的立法模式,賦予犯罪嫌疑人和辯護人救濟會見權的權利;健全恐怖活動犯罪中律師會見權體系,避免權力集中,充分貫徹以審判為中心的司法改革精神,構建完善的會見權監督體系,引入檢察院與法院在會見權中的角色與作用;充分結合恐怖活動犯罪的特殊性,考量法律價值與刑事訴訟各方價值,對律師與恐怖活動犯罪嫌疑人的會見進行適當地限制。
三、反恐程序中律師會見權的立法構思
就人權保障方面來說,美國法律一向以權利保護著稱,在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一案中聯邦最高法裁定通過審訊已經被警察機關羈押的犯罪嫌疑人獲得的自白和陳述將被裁定為不可采,除非警察機關事先給嫌疑人四項警告,即“米蘭達警告”。犯罪嫌疑人在初次被詢問前有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且有隨時與律師交流的權利,與此同時通過大量的判例,聯邦法院要求政府有保障犯罪嫌疑人與其律師交流的權利。如若警察機關違反米蘭達規則,則經過此程序獲得的證據都會被審判法官排除。“米蘭達警告”是對普通刑事犯罪中嫌疑人權利的保護,但同樣適用于恐怖活動犯罪,恐怖活動犯罪中嫌疑人的訴訟權利仍然值得被保護。
由于“北愛爾蘭共和軍”的存在,英國一直不缺乏對抗恐怖主義的經驗,尤其在應對分裂型恐怖暴力方面更是“技高一籌”,英國最早在1974年就頒布了《防止恐怖主義法》,1976年為應對愛爾蘭的恐怖組織由增加了新的立法。在《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中規定了被逮捕的人可以在任何時候與其聘請的律師進行交流,并且規定不得無正當理由得剝奪嫌疑人與律師的交流權利。
對我國來說,其一,在肯定恐怖活動犯罪律師會見權的批準主體為縣以上公安機關的負責人的基礎上,賦予會見權主體律師申請批準監督的權利。根據馬克思主義發展觀,事物在經過否定之否定后得到發展,對于相關機關的監督就是對律師會見審查的再一次“否定”,對于此種程序的啟動主體,會見律師自然享有相應的權利。其二,應賦予做出批準決定的公安機關同級人民檢察院監督會見權行使的職權,人民群眾不是制約權力的最后武器,而應當是國家機關。隨著原屬于檢察院的職務犯罪偵查權轉隸于監察委,檢察院的偵查權資產已被消耗,檢察院應盡快尋找自身價值定位,而檢察院作為我國法律監督機關,對此類監督自然可以享有監督權,同時檢察院的介入還可以形成有效的外部監督。檢察院在案件事實的基礎上,綜合考慮各方面影響因素,對偵查機關不予會見決定結果給予肯定或者是變更的決定。其三,對于偵查階段未經律師會見的案件,由于犯罪嫌疑人未獲得律師有效的幫助,此類證據應納入非法證據排除范圍,法院在綜合案情考慮下,經此程序所得到的證據可以被排除,以此起到嚇阻作用。
在保障人權的同時,恐怖活動犯罪律師會見權體系的建立更不應當忽略刑事訴訟法“懲罰犯罪”的基本功能。
盡管英美兩國對犯罪嫌疑人權利保護甚是周全,但由于恐怖活動犯罪的特殊性,訴訟程序會在懲罰犯罪方面加大力度,以求維護公共秩序與國家安全的目標。
美國在“9·11”事件引起了美國上下對反恐立法的全方位關注,2001年10月26日出臺的《愛國者法案》標志著美國反恐戰爭的開始。《愛國者法案》極大地削弱了恐怖犯罪中犯罪嫌疑人的訴訟權利,同時對公民的隱私權造成了破壞,在美國國內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對于委托人與其律師會見的限制主要通過規則“Special Adminstrative measures”來加以限制,該規則限制了委托人與外界的交流,同時限制了委托人與律師會見的權利。在同年美國政府通過的法令中,要求監管產所對委托人與其律師的會見可以進行監視與監聽。可見美國在應對恐怖活動犯罪時更加注重的是國家安全價值,不僅在是否會見問題上進行了限制,同時在會見過程中也設置了過多干預,如此嚴格的立法與其所經歷的恐怖事件有關。在將反恐視為“戰爭”的美國,以犧牲個人自由的方式來保護國家安全未免有些“反制過剩” ,其中缺乏對犯罪嫌疑人權利侵害的救濟方式,一味強調國家安全超越個人自由的價值觀,也許可以一時提高對恐怖活動犯罪的打擊力度,但并非長久之計,美國的立法著實值得商榷。
英國1976年為應對愛爾蘭的恐怖組織由增加了新的立法,該法價值觀便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優先目的,對人權的保護就相對薄弱一些,其中包括對沉默權的限制、強偵查強制主義的弱化等等。“9·11”時間與2005年倫敦地鐵爆炸案讓英國再次對恐怖犯罪感到擔憂,在2008年最新的反恐立法中又引入了更多的內容。
英國在《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中不僅賦予了嫌疑人與辯護律師交流的權利,同時也對該權利進行了限制,規定在“嚴重的可捕犯罪中”,如果犯罪嫌疑人可能毀損證據或對他人進行傷害的、可能幫助同案犯脫逃的、妨礙追回犯罪所得財產的,可以將會見推遲36小時,在此情況下如若警方認為會見可能對偵查造成不合理延遲的、未聯系上律師的或律師無法到達警察署的,則警方可以在嫌疑人接收律師幫助前對其進行訊問。“不過上訴法院早期的一個裁決清楚地表明,根據上述規定推遲會見律師的情況應該很少出現,而且實踐中根據第58條正式推遲會見的情形幾乎從未被批準過。”
我國為保證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秩序,可以適當地對律師會見權進行限制。其一,應對承接恐怖活動犯罪案件的律師資格進行審查。對承接此類案件的律師資格進行限制,事先界定辯護人的范圍,只允許特定辯護人接受委托或者機關指定,這在大多數法治國家都是認可的。這點可以與我國正在進行的律師分級制度合二為一,律師分級制度的目的是在于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更好地發揮律師在服務社會發展、保障人民群眾合法權益,提供更加專業、精準、高效的法律服務,這與恐怖活動犯罪中律師資格審查的觀點不謀而合,在刑事專業方面多開設一項針對恐怖活動犯罪的評級,選拔該專業優秀人才為國家與人民服務。由國家認證的專業律師在與嫌疑人會見的過程中不會與嫌疑人合謀破壞國家利益,同時通過資格審查的律師在經驗中也勝過普通律師,從而加強保障了嫌疑人的訴訟權利。其二,應允許恐怖活動犯罪律師會見可以派專員在場。偵查機關對律師會見的提防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方面,律師與嫌疑人串通,毀滅證據,有礙偵查。另一方面,律師會向嫌疑人傳授躲避詢問技巧,使得審訊工作難以進行。對于前者律師的行為本身就構成違法行為,派專人在場有利于杜絕此種行為的發生。對于后者,在前文中已進行陳述,由于此類案件的特殊性,刑事訴訟對于保護國家安全的功能要重于保護嫌疑人訴訟權利的功能,案件中律師所教授嫌疑人脫罪技巧的行為就可能成為破壞國家安全的毒刃,在平衡兩者價值之后,允許律師會見派專人在場也顯得具有合理性。對于派出專員的機關應當為同級的檢察機關。一方面此舉可以加強檢察院的法律監督職能,捍衛法律尊嚴;另一方面也可對偵查機關形成有效的外部監督,防止制度在偵查機關內部被消化。
四、結語
盡管恐怖活動類犯罪有其特殊性,在價值平衡的杠桿上應適當傾向于國家安全方面,為應對日趨嚴重的恐怖威脅,反恐立法的總體取向應當是以社會防衛為核心,兼顧人權保障,努力實現人權保障與社會防衛的動態平衡。”注重保護國家與社會的公共利益,但同時也應當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訴訟權利得到保護,在實現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以此促進刑事訴訟法保護懲罰犯罪、保護公共利益的最終目的。
注釋:
汪海燕.合理解釋:辯護權條款虛化和異化的防線[J].政法論壇,2012,30(6):25-33.
倪春樂.恐怖主義犯罪特別訴訟程序比較研究[D].西南政法大學,2011.
麥高偉,杰弗里·威爾遜主編.英國刑事司法程序.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頁.
趙秉志. 中國恐怖活動犯罪的防治對策[N]. 光明日報,2014-08-29(011).
參考文獻:
[1]劉志浩.中國反恐現狀調查:1年嚴打不能根除恐怖主義[J].齊魯晚報,2014-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