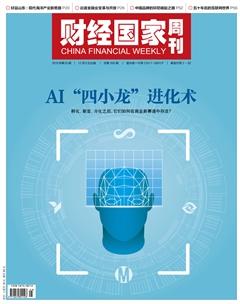鄭和艦隊“二把手”的航海傳奇
唐博
2010年6月,南京江寧區祖堂山,一家社會福利院正在擴建。
施工隊在挖土的時候,偶然發現了一座明代磚墓。于是,工地停工,考古人員介入。
令專家們激動的,不光是墓中出土的玉環、水晶串飾等明代器物,更是一塊《大明都知監太監洪公壽藏銘》。這份相當于墓志銘的東西,共有25行741個字,不僅明確了這座墓地的主人,還講述了一段明代海上絲綢之路鮮為人知的往事。
墓主人究竟是誰?到底是什么樣的往事,讓專家們如獲至寶呢?
洪保其人
《壽藏銘》里的“都知監太監洪公”,本名洪保。這不是個一般的太監,而是鄭和下西洋時艦隊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甚至成了鄭和最后幾次下西洋的艦隊二把手。
洪保究竟是什么來頭?為什么從未聽說過這個人呢?
能夠參與鄭和的航海壯舉,對于洪保來說絕非偶然。他跟鄭和是老鄉,年齡相仿,生活經歷也相似。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軍攻入云南,12歲的洪保和11歲的鄭和作為俘虜,被送到南京皇宮,當上了太監。
跑男 洪保是個善于跑腿的宦官。奉旨出使西域、跟隨鄭和下西洋這些差事,不僅讓他活脫脫成了“跑男”,還大開眼界,立身正面,成了宦官隊伍里的一股清流。
洪保是個善于做選擇題的宦官。他的人生轉折,與此有關。朱元璋死后,在朱棣和朱允炆這對叔侄之間,他選了前者。追隨燕王“靖難”,讓他不僅得了“洪保”的賜名,還官運亨通,歷任內承運庫副使、都知監右少監、都知監太監等職,長期位于宦官食物鏈的頂端。
洪保是個善于跑腿的宦官。奉旨出使西域、跟隨鄭和下西洋這些差事,不僅讓他活脫脫成了“跑男”,還大開眼界,立身正面,成了宦官隊伍里的一股清流。更重要的是,他身跨陸海,參與了明代初期陸地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擘畫寫意,一定程度上比鄭和的成就更大。
洪保是個運氣不錯的宦官。他的一生歷經洪武、建文、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六朝,直到明英宗正統六年(1441年),仍以72歲高齡擔任都知監掌印太監。而出土的《壽藏銘》,則是他65歲那年刻的。歷史上長壽且善終的宦官寥寥無幾,洪保是其中之一。
洪保是鄭和下西洋的副手,曾幫助鄭和艦隊抓后勤,買物資,但在各種歷史文獻中,洪保的名字鮮少出現。不過,洪保的《壽藏銘》,卻讓人眼前一亮,甚至備感震撼,這是怎么回事呢?
超級艦隊
明代中后期,紫禁城經歷的幾場火災,將鄭和下西洋的檔案文獻多數毀于一旦,連制造寶船的船廠也沒留下多少資料。歷史學家把尋找新資料和新線索的期待寄于出土文獻,但直到洪保墓的《壽藏銘》重見天日,才實現了這個夙愿。
《壽藏銘》里的寥寥數語,引起了歷史學家的興趣:“(洪保)充副使,統領軍士,乘大福等號五千料巨舶,赍捧詔敕使西洋各番國、撫諭遠人。”這段文字最重要的價值,就是給出了鄭和寶船的規模。
1937年,南京靜海寺出土的殘碑上,記載了這樣一段話:“永樂三年,將領官軍乘駕二千料海船,并八櫓船……永樂七年,將領官軍乘駕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櫓船。”這算是證明鄭和寶船規格大小的一條實物證據。

南京龍江寶船廠遺址公園的巨幅油畫描繪了當年鄭和下西洋的寶船。鄭和下西洋的檔案文獻大多被毀,連制造寶船的船廠也沒留下多少資料。
這里的“料”是古代計量單位。要么以一石糧食為一料,要么以兩端截面方一尺、長七尺的木材為一料。1石大致相當于60公斤。因而,按照靜海寺殘碑的說法,鄭和寶船排水量約為900~1200噸。至于它的形制,也能估算出來,大概長18丈,寬4.4丈,也就是長56米,寬13.7米,相當于兩艘037獵潛艇的大小。
千噸級的木船,在古代堪稱大船,或許更接近事實真相。可是,洪保墓出土的《壽藏銘》,再次刷新了歷史學家對鄭和寶船的認識。其中提到的旗艦“大福號”達到“五千料”,那就相當于3000噸級了。這個噸位在中國海軍,夠得上上一代主力驅逐艦了。
眾多3000噸級的木船出現在中國南海和印度洋上,這樣的規模要比想象的更大、更宏偉、更有威懾力。
經濟影響
宣德五年(1430年),鄭和開始了最后一次遠航。艦隊抵達古里(今印度西部喀拉拉邦)后,聽說有個國家叫天方(今沙特麥加),此前并沒有中國人到過那里。好奇心驅使著鄭和與洪保,想要一探究竟。于是,洪保就帶了7個人,乘船離開古里,直趨天方。
抵達天方之后,“遠人駭其猝至”。當地人對洪保等人的迅速到來感到恐慌。于是,當地國王“以親屬隨行奉貢”。貢品里有“麒麟、獅、象,與夫藏山隱海之靈物、沉沙棲陸之奇寶”。
當天方國的使臣跟著洪保來到南京,向明成祖磕頭稱臣,獻上貢品后,就會得到明朝朝更多的賞賜,甚至在官府指定的時間和地點,把帶來的剩余貢品高價賣掉,讓朝廷吃虧,讓朝貢的小國得實惠,體現所謂“厚往薄來”的“天朝胸襟”,從而換取“萬邦來朝”的政治收益。
很顯然,這種規則塑造的結果很畸形:誰稱臣朝貢,誰穩賺不賠。明王朝就用這個辦法,籠絡了一大批周邊國家,形成了以它為中心的朝貢貿易圈。鄭和艦隊,則是這個圈子賴以維系的重要紐帶。
朝貢貿易背景下,不等價交換帶來的豐厚利潤,讓外國使團總希望多帶剩余貢品,擴大貿易量。明成祖去世后,明朝方面基于財政壓力,逐步收縮貿易優惠,讓外國使團少帶剩余貢品,售價便宜些。一旦發現無利可圖,外國使團便越來越少,“朝貢”也就有名無實了。
至于鄭和艦隊,雖然船只龐大、人數眾多,但本就不是貿易團,而是炫耀武力的使團,途經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各地,也就做點貿易讓利,順便買些御用奢侈品,貿易額小,幾乎都虧本。這樣的貿易當然不可持續。
正統六年(1441年),鄭和已經去世多年,洪保取而代之,從二把手變成了一把手,獨自率領艦隊遠航。返程時遭遇臺風,險些送命。這大概也是明朝國家艦隊將觸角伸向世界的絕唱了。
洪保偃旗息鼓了,但明朝的海外私人貿易方興未艾,帶動了東南地區的經濟轉型,催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不過,洪保留下的《壽藏銘》,永遠銘記著他追尋海洋的夢想與實踐,成為“一帶一路”歷史上的一段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