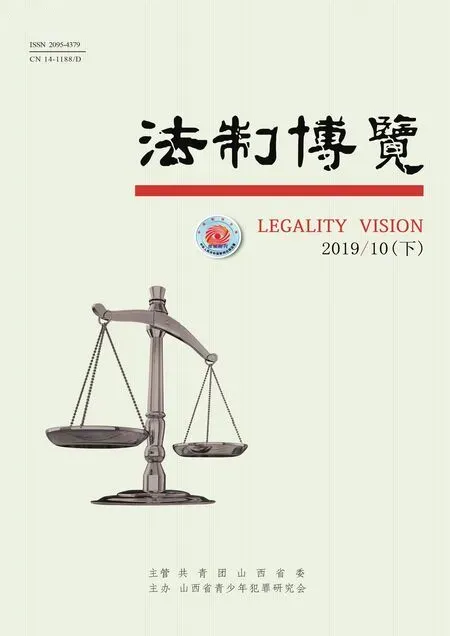從律師隊伍中公開選拔法官制度司法實踐的探析
黃彬文 葉 玫
江西師范大學,江西 南昌 330022
一、從律師中隊伍中選拔法官立法的政策背景及司法實踐
從律師中選拔法官是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改革符合十九大提出“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精神。此項司法改革的一個重要的政策是,2014年10月23日,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中提到要“建立從符合條件的律師、法學專家中招錄立法工作者、法官、檢察官制度”。2016年6月15日,中央辦公廳印發《從律師和法學專家中公開選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檢察官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將《決定》文件中的精神落實到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層面,多個地區依據《辦法》已經進行了公開選拔工作,如2017年1月,廣東省高級法院公開選拔6名法官;2018年9月江蘇省高級法院公開選拔4名法官;2019年1月浙江省高級法院公開選拔4名法官。新修訂的《法官法》新增第十五條之內容,從立法層面上確立了選拔工作制度,使得選拔工作有法可依,也符合依法治國之國家各項事業有法可依的前提要求。自《辦法》實施以來,能在互聯網上搜索到的公開選拔消息較少,除上述提到的3個省高級法院已經或正在公開選拔外,僅有北京市預計將在今年進行公開選拔。可見,雖然選拔工作有了政策和法律的依據,但落實到司法實踐的少,離政策導向要求的選拔工作常態化、制度化還存在差距。
二、從律師中隊伍中選拔法官司法實踐不佳的原因分析
根據現已公開的選拔信息來分析,選拔工作呈現選拔地區均為沿海發達省或直轄市、選拔次數少和人員規模較小、用人法院均為地市層級等現象。筆者認為,這些現象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受傳統“官本位”思想影響,對律師職業缺乏包容
有的學者指出,“從律師到法官,中國傳統古未有之,缺少文化傳承”[2]。受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文化的影響,以官為本、以官為貴、以官為尊的“官本位”思想,深入社會層層面面。在這種固化思想的影響下,老百姓認為法官比律師地位更高,法官是手握審判權力的“官”,案件判決結果的決定權在法官,律師是在法官手下辦事。甚至,有的人對律師職業存有偏見,認為律師是鉆法律空子的投機者,沒什么真本事,“無非手熟爾”。這些對律師職業缺乏包容的思想,是一把精神枷鎖,串聯起來就是一條無形的鎖鏈,無法想象能有多粗多長。另外,思想包容程度與一個地方的經濟、對外交往等因素相關聯,這一點從已經實施或正要實施公開選拔的省份地區可以看出來。經濟發達的地區思想較開放,也較能接受與借鑒英美法系法官來源于律師群體的法律文化。所以對律師缺乏包容的“官本位”思想,看似是一念之間的偏差,卻從思想根源上阻礙了選拔工作的實效開展。
(二)律師與法官之間在職業上缺少認同
律師與法官同屬法律共同體,相互業務往來密切、聯系緊密,對彼此職業的熟悉程度是非法律行業不能比擬的。部分法官和律師對彼此的職業雖然熟悉,但有時從自身職業出發去看待對方的職業,難免會出現認知偏差。有部分律師和法官認為法院特別是基層法院“案多人少”,辦案壓力大,律師屬于自由職業者,工作內容和時間自由較靈活;律師事務所是營利機構,律師業就是商業,盡管近年來實行績效考核工資,法官的收入雖有所提高,但法官與律師的工作同樣是辦理案件,但收入比律師要少很多[3]。從已公開選拔的用人法院均為地市層級法院來看,部分職務晉升緩慢縣區的法官心里難免會有落差,緣何自己沒有參與競爭的機會。總而言之,有部分律師不情愿進“體制內”任法官,而部分法官也不希望設立單獨渠道的方式選拔法官,也是造成選拔工作情況不佳的重要原因。
(三)法官“職業化”實現不徹底,對律師的吸引力不高
我國憲法明確了司法獨立原則,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干涉。人民法院要做到獨立行使審判權,就要對人、財、物有自主決定權。雖然,法院實行員額制改革后,設立法官專業化職級序列。但實踐中,我國法院的人、財、物仍未脫離地方政府掌控,難免會受制于人,如2017年,重慶市某基層人民法院仍不具有對人、財、物的自主決定權[1]。法官職級晉升受當地全區晉升總編制數量限制,脫離行政化管理,徹底實現“職業化”還有一段路要走。法官“職業化”環境的實現程度,對律師選任法官后的前途有重要影響。待法院脫離行政化管理、徹底實現“職業化”之前,部分律師仍在等待和觀望。
三、從律師隊伍中選拔法官司法實踐不佳的個人建議
選拔律師任法官是本輪司法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是為了解決“人”的問題,而選拔優秀律師任法官法選對構建法律共同體具有促進作用。針對司法實踐上述問題,提出如下建議,僅供參考。
(一)轉變思想觀念,重新認識律師職業
2016年6月13日,中辦國辦印發《關于深化律師制度改革的意見》指出,律師是社會主義法治工作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要進一步發揮律師在“四個全面”中的職能和作用。宣傳部門和司法機關,特別是律師自己要貫徹落實國家對律師定位的精神,對律師有個正確的定位,向社會各層面進行主觀思想上宣傳,逐漸改變社會上對律師的偏見與不平等的認識。固化思想與經濟發展、思想開放程度等客觀因素相關聯,這些方便要得到轉變需要有個時間過程。但隨著國家正在大力實施的中部崛起、西部振興、一帶一路等戰略,將逐步拉近我國地區間發展差距,同時地區間對律師職業的包容會更加均衡。
(二)承認客觀存在,正確對待職業轉換
上述對法官、律師職業的評價存在偏差,二者同屬法律共同體的法治目標是一致認同的,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對比。部分法官、律師應對相互職業做全面了解,糾正認識盲區。同時也要承認二者的收入差距、辦案壓力大等客觀事實。律師高收入也是律師隊伍不斷壯大的一個重要原因,選擇法官職業時考慮收入無可厚非,但更主要的動力還是來自司法職位的權威、榮譽、責任感等精神因素。這就是為什么法官隊伍總體情況穩定的原因,如近年來全國法官辭職人數一直保持在0.35%以下。法律共同體除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視為共同價值追求外,個體也有著自己對職業生涯的憧憬與追求。所以法官辭職也好,律師通過選拔任法官也罷,都是法律職業者的自由選擇。律師和法官在遵守職業道德的前提下,職業轉變應被正確看待。
(三)法官走“職業化”道路,提高法官職業的吸引力
法官員額制改革后,實行績效工資,法官群體的工資比一般公務員要高,但法官向往美好生活的經濟基礎需要依靠繼續提高工資來實現。此外,本輪司法體制改革涉及到人財物的管理,只有法院對人、財、物有了決定權,不受地方影響,法院審判工作、法官職務晉升及福利待遇等才能完全自主。所以維護好司法獨立原則,對法官走徹底“職業化”道路才更有益,才能激起人們對法官職業的崇尚和尊重。
四、結語
截至2018年年底,中國律師事務所已經發展至3萬余家,執業律師達42.3萬余人。數量龐大的律師隊伍,可視為法官的儲備力量。如果能排除選拔渠道的頑疾,將優秀人才填充到司法隊伍中去,勢必推進我國法治化建設邁向新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