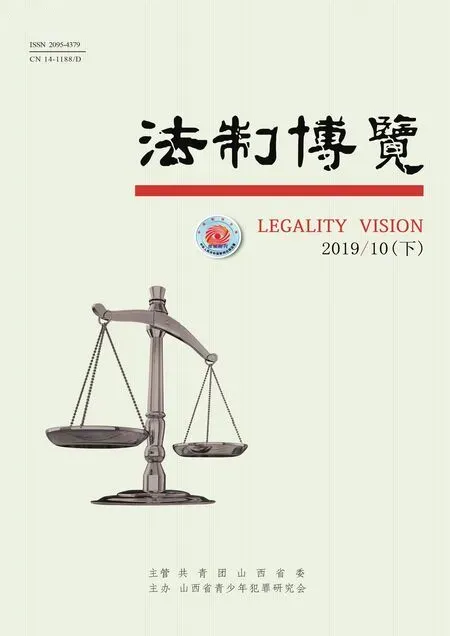試論轉繼承在公證實務中的法律困境
呂維超
廈門市同安區公證處,福建 廈門 361100
我國社會發展快速、法律制度逐漸健全,其對公證實務活動提出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因為公證本身能夠有效避免財產糾紛,有效保護個人權益,特別是轉繼承作為公證實務活動中的關鍵環節已經得到廣泛應用,它有效維護了權益的相關繼承權利。當然,由于繼承權益問題過于復雜,所以目前我國的轉繼承公證實務工作還面臨諸多法律困境亟待解決。
一、轉繼承的核心內涵
轉繼承是指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后或者在實際繼承之前死亡,由繼承人的法定繼承人代其接受繼承權的一種法律繼承制度,這其中本應接受繼承遺產但已死亡的繼承人就轉變身份成為“轉繼承人”。在轉繼承法律制度中包含了4個特點內容:第一,繼承人的死亡時間應該從繼承開始后到遺產被分割之前的時間范圍內;第二,被轉繼承人所接受的來自于轉繼承人的繼承權利是合法的;第三,轉繼承人擁有繼承權;第四,被轉繼承人沒有做出放棄或接受繼承權的相關表示權利。
二、公證實務活動中轉繼承權的法律困境
由以上定義可以看出轉繼承權相當復雜,而它在現實的公證實務實踐活動中也是存在諸多瓶頸與法律困境問題的,下文簡單介紹兩點。
(一)轉繼承問題存在與否
在公證實務活動中是否存在轉繼承問題爭議很大,目前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聲音:第一種觀點表示公證實務活動中是不存在轉繼承問題的,因為轉繼承本身涉及法律問題,其所公證的內容也是對現有事實的認定,因此需要確定轉繼承人與被轉繼承人的狀態后再開展遺產分配工作,而針對遺產的分配則要由法院認定后才可進行;第二種觀點也表示在公證實務活動中不存在轉繼承問題,但與第一種觀點不同,它認為轉繼承與財產分配二者之間聯系較大,轉繼承權限需要在公證機構的公證認定下,再結合確鑿證據與實際調查結果才能對轉繼承權進行有效認定。兩種觀點一個強調人證,一個強調物證,在公證認定方面存在較大差異,但二者都認為轉繼承問題并不存在,這也為涉及轉繼承法律問題民事案件的解決帶來了一定困擾。
(二)轉繼承人問題如何確定
基于轉繼承的公證實務活動中會涉及到多個繼承人,所以在公證活動中的重要要務就是分析和確定合法繼承人,具體到實踐工作中它應該結合以下幾點基本原則展開:
其一,要結合公序良俗這一《民法通則》重要內容展開針對繼承人的有效確定過程,確保繼承人在不違反公序良俗行為、不違反國家相關秩序的基礎之上明確其道德思想行為。
其二,要加強針對公民財產與繼承權的有效保護,基于物權法相關內容來明確公民私有權相關內容。例如在實際的轉繼承公證實務活動中一定要避免違反相關法律,且保障公民私有財產繼承權被有效繼承。
其三,要確定繼承人的先后法律繼承順序,明確他們的繼承法律關系。傳統公證實務活動中常常由于混亂了繼承法律關系而導致出現更多繼承糾紛問題,造成法律困境。
其四,要準確認定具有相互繼承關系的人,以確保在繼承人死亡后快速定位轉繼承人。在實際操作中存在繼承人死亡先后時間不明確、死亡人輩分混亂、被轉繼承人劃分不清的情況。
其五,還要明確一點即遺囑繼承中的轉繼承必須注意立遺囑時間,包括遺囑的生效時間等等。
上述有關公證實務活動中的轉繼承法律困境問題復雜且不易解決,若想清晰化這些困境問題的實質內容還需要結合實際案例展開分析[1]。
三、公證實務活動中轉繼承的案件分析
(一)案件案情背景
某老人2014年去世,去世后在農村家鄉遺留一間房,她的丈夫李某與她的父母均在老人取得房屋前死亡,生前無任何債務。老人有四女一子,分別為女兒大明、二明、三明、四明和兒子五郎。其中大女兒大明在2017年死亡,留有一女白女,大明配偶為白某。三明在2012年先于老人死亡,其配偶則在2013年死亡,三明夫妻留有兩個兒子,五郎作為老人唯一的兒子在2018年去世,留有一個兒子,五郎的妻子健在,她表示放棄上述應繼份額繼承權(希望兒子繼承)。
上述案件中就涉及到了本文所談到的本位繼承、代位繼承以及轉繼承問題,其中前兩者具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在公證實務活動中可展開操作。結合本案參考,就簡單談談轉繼承操作過程中所面臨的各種問題。
(二)本案公證實務中對轉繼承人的確定
在本案的公證實務中針對轉繼承人的確定存在3點主要觀點,以下將逐一作出分析。
1.觀點一
第一種觀點認為采用公證實務活動進行轉繼承人確定比較穩妥,但這一法律活動中就涉及到財產分割、贈與以及稅收法律相關問題。因此說該案件需要首先簡單授意老人家中某一資格適配的申請人主動出面主張權利,并成人不會違背當事人意愿自治原則。
2.觀點二
在該案中,原本擁有繼承權的大明和五郎均死亡,因此才出現了轉繼承問題,轉繼承人是大明的女兒白女和五郎的兒子,包括大明的配偶白某。根據我國《繼承法》第2條“繼承從被繼承人死亡開始”這一規定與《物權法》第29條“因繼承或者受遺贈取得物權的,自繼承或者受遺贈開始時發生效力”兩條規定,結合案情可以了解到大明在老人死亡之時已經取得了應有的遺產份額所有權,所以當第一順位的轉繼承人如果放棄繼承權,那么將由第二順位的繼承人承接享有轉繼承權。
3.觀點三
第三種觀點支持由五郎的兒子轉繼承,這其實也是本案的最終判定結果。因為由兒子繼承遺產符合繼承法立法精神與社會大眾的普遍期待認知,再結合本案例可以從以下兩個原則來最終明確轉繼承人。
首先,根據《民法通則》中的公序良俗原則確定最終轉繼承人。因為申請繼承遺產的繼承人很多,其中還有部分人放棄繼承權,這種行為不違反繼承權與社會公共利益,對他人利益也沒有損害。劉某的最終轉繼承人確立并不以損害他人繼承權為前提。
其次,結合《繼承法》立法的相關內涵,需要保護公民私有財產在家庭范圍中始終保持正常流轉狀態,合理保護并運用公民私有財產繼承權。而對于像本案中的無主財產在處理方面則要在不違背保護公民私有財產繼承權的前提下合理決定轉繼承人,同時迎合公眾期望作出判斷,這符合《繼承法》的立法本意。
總結上述兩點,劉五的兒子劉某最后成為轉繼承人符合立法基本原則與社會大眾期望,可保證申請人的法定繼承權益[2]。
四、公證實務活動中實施轉繼承的注意事項
首先必須明確轉繼承人的基本數量,在具體的公證實務活動中,必須明確這一點,因為它可保證在公證不出現遺漏的狀態下避免各種后續問題。在明確人數以后,公證人員可采用的公證實務方法更多,例如可對當事人實施直接詢問確定人數。亦或者利用走訪調查的方法對繼承人數量進行明確確定,或通過對繼承人的相關機關進行有效查詢。上述3種方法都是非常快捷且高效準確的。
其次必須明確是否需要訂立遺囑。它主要涉及到被繼承人,需要在被繼承人死亡之前對遺囑進行定理,完全遵照遺囑中的相關重要事項解決問題。如果遺囑中表明被轉繼承人不具備繼承權,則無論任何原因都需尊重被繼承人意愿,在遺囑中對轉繼承人所具備的繼承權進行相應考量,遵照相關法律對轉繼承狀況進行明確,結合實際情況依據與相關程序對轉繼承公證活動內容進行分析,思考繼承工程活動中所具備的真實性內涵,并評價它的安全可靠性與真實性。
再一點,有必要對轉繼承公證中的被繼承人意愿進行進一步明確,可考慮通過多種方式進行判斷,明確被繼承人生前是否存在放棄財產繼承權的情況,如果沒有放棄被繼承權或者沒有訂立遺囑,則允許被繼承人轉繼承自身遺產,并對轉繼承權進行綜合性公證,并凸顯公證過程的全面有效性,切實確保轉繼承人的自身權益得到有效維護與保障[3]。
五、總結
在公證實務活動中的轉繼承法律實施過程中存在法律困境問題,所以在實際操作中還要結合適用法律標準,基于實施真相進行有效結合,在擺正事實的基礎之上滿足依法辦事條例,滿足公證案件處理要求,找到正確的案件審理出發點,保護繼承人及轉繼承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