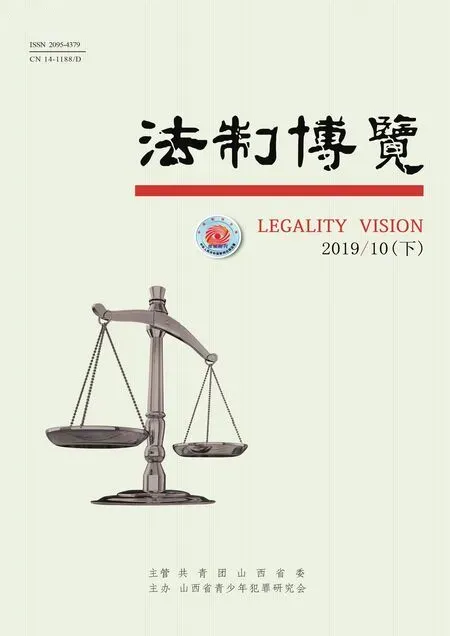非法經(jīng)營(yíng)同類(lèi)營(yíng)業(yè)罪構(gòu)成要件初探
趙怡萱
北京師范大學(xué)珠海校區(qū),廣東 珠海 519000
一、非法經(jīng)營(yíng)同類(lèi)營(yíng)業(yè)罪的淵源
改革開(kāi)放初期常有所謂國(guó)企董事、經(jīng)理有悖競(jìng)業(yè)禁止之責(zé),利用職權(quán)非法經(jīng)營(yíng)同類(lèi)營(yíng)業(yè)的行為嚴(yán)重?fù)p害了當(dāng)時(shí)公有制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在當(dāng)時(shí)的國(guó)情下,運(yùn)用民商事法律、行政管制等社會(huì)治理手段都不足以遏制這些違法行為。為了保證公有制經(jīng)濟(jì)的正常運(yùn)轉(zhuǎn),國(guó)家利益不被非法侵蝕,保護(hù)國(guó)有企業(yè)管理秩序及國(guó)有資產(chǎn)保值、增值,我國(guó)在立法時(shí)就借鑒了國(guó)外背信罪的立法例相關(guān)的原理和技術(shù)。最終,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全國(guó)人民代表大會(huì)第五次會(huì)議修訂《刑法》增設(shè)了非法經(jīng)營(yíng)同類(lèi)營(yíng)業(yè)罪。
二、非法經(jīng)營(yíng)同類(lèi)營(yíng)業(yè)罪的構(gòu)成
(一)本罪主體方面
本罪乃謂之為身份犯,對(duì)于犯罪主體方面有著嚴(yán)格的限定。根據(jù)法條原文表述為“國(guó)有公司、企業(yè)的董事、經(jīng)理”。即獨(dú)有國(guó)有公司、企業(yè)的董事、經(jīng)理身份之犯罪主體才有可能適用本罪要旨。對(duì)于“國(guó)有企業(yè)、公司”及“董事、經(jīng)理”的具體指向都應(yīng)加以明晰。
1.國(guó)有企業(yè)、公司”的界定
隨著混合所有制改革推進(jìn),一些國(guó)有獨(dú)資企業(yè)、公司改為國(guó)有資本控股公司或者非國(guó)有資本控股公司,還有一些外資、私營(yíng)企業(yè)參股國(guó)有企業(yè)、公司或國(guó)有公司、企業(yè)收購(gòu)?fù)赓Y、私營(yíng)的部分或全部股權(quán),導(dǎo)致單純的全資國(guó)有企業(yè)在逐漸減少,國(guó)有參股、控股企業(yè)類(lèi)型和數(shù)量增多,國(guó)有資產(chǎn)將無(wú)法得到保護(hù)。而對(duì)于混合所有制企業(yè)、公司本身,由于國(guó)有成分的情況復(fù)雜,認(rèn)定適用企業(yè)應(yīng)當(dāng)結(jié)合具體情況進(jìn)行討論。
國(guó)有控股、參股公司、企業(yè)一般分為以下三類(lèi):第一類(lèi)是國(guó)有資本占公司股本構(gòu)成的51%以上,絕對(duì)控股;第二類(lèi)是雖然國(guó)有資本占公司股本構(gòu)成沒(méi)有達(dá)到51%以上,但由于公司股本構(gòu)成主體較多,但國(guó)有資本占公司股本為最大達(dá)到1/3以上,形成相對(duì)控股,公司并表經(jīng)營(yíng);第三類(lèi),國(guó)有資本占公司股本最大達(dá)不到1/3以上,不能形成相對(duì)控股局面,這就是國(guó)有參股企業(yè)。對(duì)公司的控制權(quán)并不完全體現(xiàn)為股權(quán)比例的多少,對(duì)管理層尤其是董事會(huì)的成員或者決策具有絕對(duì)影響力的時(shí)候也可以視為相對(duì)控制。
追溯本罪的立法原意、刑法的基本原則及刑法的謙抑性,本罪主體構(gòu)成要件所述及的國(guó)有公司,一般情況下僅指國(guó)有資本占主體的公司,結(jié)合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5】10號(hào)《關(guān)于如何認(rèn)定國(guó)有控股、參股股份有限公司中的國(guó)有公司、企業(yè)人員的解釋》關(guān)于“國(guó)有公司、企業(yè)委派到國(guó)有控股、參股公司從事公務(wù)的人員,以國(guó)有公司、企業(yè)人員論”的解釋內(nèi)容。這些國(guó)有資本絕對(duì)控股以及相對(duì)控股的公司,由于國(guó)家專(zhuān)有資本占據(jù)主體之絕對(duì)地位,這些公司的董事、經(jīng)理毋庸置疑地劃定為本罪之犯罪主體所適用的范圍之內(nèi)。但是,對(duì)于相對(duì)控股的理解,需要同時(shí)考慮國(guó)有資本對(duì)公司治理是否具有重大影響力。如果不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國(guó)有相對(duì)控股公司的董事、經(jīng)理不應(yīng)歸屬于本罪犯罪主體的范疇。
2.董事和經(jīng)理的身份限定
雖然公司法意義上的高級(jí)管理人員包括董事、經(jīng)理、監(jiān)事、財(cái)務(wù)管理人員,但是本罪的適格主體并不包括監(jiān)事和財(cái)務(wù)管理人員,僅限于董事、經(jīng)理。盡管從《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的字面意思上看非法經(jīng)營(yíng)同類(lèi)營(yíng)業(yè)罪主要針對(duì)的是國(guó)企高管犯罪,但更確切地是針對(duì)國(guó)企負(fù)責(zé)日常經(jīng)營(yíng)的高管犯罪。不直接參與公司的日常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管理的國(guó)企高管不適用本罪,如監(jiān)事、財(cái)務(wù)管理人員、上市公司的獨(dú)立董事等。
此外,擔(dān)任副職或者下級(jí)部門(mén)經(jīng)理等職務(wù)的人員不應(yīng)當(dāng)籠統(tǒng)地適用于本罪。在一般的公司治理中,副職高管的人選及職權(quán)均不獨(dú)立于正職高管,因此一般不認(rèn)為主體適格。主管黨內(nèi)事務(wù)的領(lǐng)導(dǎo)職務(wù)可能由正職高管兼任,一般通過(guò)其經(jīng)營(yíng)管理職權(quán)來(lái)認(rèn)定主體適格。在專(zhuān)任時(shí),難以利用黨內(nèi)領(lǐng)導(dǎo)職權(quán)的影響力來(lái)獲取相應(yīng)便利,可以采取“間接正犯”等理論予以追究刑事責(zé)任。但是,其他職務(wù)人員如果由參股的國(guó)有獨(dú)資企業(yè)委派,直接向董事會(huì)匯報(bào)工作或?qū)ζ湄?fù)責(zé),且對(duì)部門(mén)內(nèi)業(yè)務(wù)經(jīng)營(yíng)的管理權(quán)獨(dú)立于總經(jīng)理時(shí),理論上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其具有實(shí)質(zhì)上的權(quán)力,可以利用職務(wù)便利,從而成為本罪的適格主體。
(二)本罪客觀(guān)方面
犯罪構(gòu)成系由主觀(guān)方面和客觀(guān)方面等多重要素耦合而統(tǒng)歸一機(jī)之體,亦為目前我國(guó)刑法立法、司法所通行的犯罪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本罪通過(guò)以上兩個(gè)層面的分析與判斷,最為關(guān)鍵的就是犯罪主體要件和犯罪客觀(guān)要件,從而把握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犯罪形態(tài)、罪輕與罪重等多個(gè)維度的認(rèn)定。非法經(jīng)營(yíng)同類(lèi)營(yíng)業(yè)罪在客觀(guān)方面表現(xiàn)為行為人利用其職務(wù)派生出的便利,自己參與經(jīng)營(yíng)或者為他人經(jīng)營(yíng)所用,謀取到數(shù)額巨大的不法利益,同時(shí)在其經(jīng)營(yíng)業(yè)務(wù)的類(lèi)屬又與行為人所在國(guó)有經(jīng)營(yíng)主體具有同一性或者關(guān)聯(lián)性。正是因?yàn)楸咀锟陀^(guān)之要件本身的復(fù)雜性和模糊性,導(dǎo)致在適用中出現(xiàn)頗多爭(zhēng)議及迷思。
1.“利用職務(wù)便利”的界定
非法經(jīng)營(yíng)同類(lèi)營(yíng)業(yè)罪要求國(guó)有經(jīng)營(yíng)主體的董事或經(jīng)理利用其職務(wù)衍生出的便利,何謂“利用職務(wù)便利”,相關(guān)的理解五花八門(mén),但總結(jié)起來(lái)主要是下列三種觀(guān)點(diǎn)。
第一種觀(guān)點(diǎn)認(rèn)為客觀(guān)方面主要體現(xiàn)為利用行為的單一性和職權(quán)與便利的強(qiáng)因果性。所謂利用行為的單一性,即這一利用行為能夠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擾影響。所謂職權(quán)與便利的強(qiáng)因果性,即便利與職權(quán)本身的因果鏈條比較直接明確,在這種情況中,便利直接地產(chǎn)生于職務(wù)范圍內(nèi)某項(xiàng)職權(quán)。如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所謂利用職務(wù)便利是指“利用自己在國(guó)有公司、企業(yè)任董事、經(jīng)理之職,掌握材料、物資、銷(xiāo)售計(jì)劃、人事等工作的便利條件。”
第二種觀(guān)點(diǎn)認(rèn)為客觀(guān)方面主要體現(xiàn)為利用行為的發(fā)散性和職權(quán)與便利的弱因果性。所謂利用行為的發(fā)散性,即這一利用行為不能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擾影響,這種利用行為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所謂職權(quán)與便利的弱因果性,即職權(quán)與便利之間的因果鏈條相對(duì)完整的同時(shí)也相對(duì)模糊,這種鏈條不是線(xiàn)狀而是網(wǎng)狀的,具體表現(xiàn)為某種便利的產(chǎn)生不是直接地來(lái)源于職務(wù)范圍內(nèi)的某項(xiàng)職權(quán),行使該特定職權(quán)并不能當(dāng)然地產(chǎn)生此種便利,此種便利的產(chǎn)生是職權(quán)的副產(chǎn)物且這種副效應(yīng)不是固定的,可能是變化的。如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利用職務(wù)便利是指“行為人主管、經(jīng)管經(jīng)營(yíng)的權(quán)力或由此產(chǎn)生的便利(如對(duì)進(jìn)貨、營(yíng)銷(xiāo)渠道的直接掌握或影響)。”
第三種觀(guān)點(diǎn)認(rèn)為客觀(guān)方面主要體現(xiàn)為利用行為的隨機(jī)性和職權(quán)與便利的無(wú)因果性。所謂利用行為的隨機(jī)性,即這一利用行為不僅不能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擾影響,甚至其自身也是作為非主要因素一種干擾因素的存在。所謂職權(quán)與便利的無(wú)因果性,即職權(quán)與便利之間的因果鏈條是斷裂的或者毫無(wú)連接的。主要表現(xiàn)為因?yàn)樽鳛槁殭?quán)所賦,其能夠相對(duì)容易地了解國(guó)有公司、企業(yè)的種種情況而形成,甚至于相對(duì)方便地結(jié)交國(guó)有公司、企業(yè)的特定崗位或職責(zé)的同事而形成。
上述三種觀(guān)點(diǎn)都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在刑事司法實(shí)踐中均被采納過(guò)。但是,從筆者依照構(gòu)成要件理論及法律解釋方法來(lái)思考,更加認(rèn)可第二種觀(guān)點(diǎn)。職務(wù)由職權(quán)和職責(zé)共同組成,職權(quán)與職責(zé)是統(tǒng)一于職務(wù)之下的,單獨(dú)從職權(quán)或職責(zé)理解職務(wù)本身都是片面的。在本罪中,如果行為人行使職權(quán)無(wú)法合理或合規(guī)解釋?zhuān)瑢?shí)際上是利用職權(quán)從事非法活動(dòng)乃至犯罪活動(dòng),則表明行為人之職責(zé)殆誤。從這種刑法上的一般意義來(lái)看,行為人錯(cuò)誤地行使職權(quán),“職務(wù)”的內(nèi)容就只體現(xiàn)出職權(quán)這一面,而“利用職務(wù)上的便利”就簡(jiǎn)化為“利用職權(quán)所衍之便利”。不諱言地說(shuō),本罪所指稱(chēng)之職務(wù)便利與適格身份主體所秉職權(quán)存在著了然的強(qiáng)因果性,這種強(qiáng)因果性可以導(dǎo)致實(shí)質(zhì)性影響的判斷成立。
因此只要行為人所利用的職務(wù)便利與行為人自身所行使的職權(quán)有一定的因果關(guān)系,不論這種因果關(guān)系是直接或間接的,就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利用了職務(wù)便利。當(dāng)然,這種因果關(guān)系不能太弱,甚至沒(méi)有因果關(guān)系,普遍意義的關(guān)聯(lián)性應(yīng)當(dāng)理解為工作上的便利而非職務(wù)上的便利。
2.“同類(lèi)營(yíng)業(yè)”的理解
同類(lèi)營(yíng)業(yè)是在客觀(guān)層面上認(rèn)定本罪成立與否的決然要件。本罪歸罪之當(dāng)然主體甚至實(shí)然主體其經(jīng)營(yíng)之營(yíng)業(yè)無(wú)論為自身抑或?yàn)樗怂\,只要該營(yíng)業(yè)與其任職的國(guó)有經(jīng)營(yíng)主體所司之營(yíng)業(yè)在屬類(lèi)上為互斥或者對(duì)立,不但本罪成立所依無(wú)存,甚至公司法所謂競(jìng)業(yè)禁止亦不相逆。但是,刑法意義上的“同類(lèi)營(yíng)業(yè)”有著其特殊性,也因此產(chǎn)生了一些爭(zhēng)議。
第一種觀(guān)點(diǎn)認(rèn)為,同類(lèi)經(jīng)營(yíng)指的是“生產(chǎn)或者銷(xiāo)售同一品種或類(lèi)似品種的營(yíng)業(yè)。”第二種觀(guān)點(diǎn)認(rèn)為“既指相同,也包括類(lèi)似,類(lèi)似的程度以達(dá)到與行為人所任職的國(guó)有公司、企業(yè)的營(yíng)業(yè)形成競(jìng)爭(zhēng)為限。”第三種觀(guān)點(diǎn)認(rèn)為,“行為人所在的國(guó)有公司、企業(yè)與自己經(jīng)營(yíng)或?yàn)樗私?jīng)營(yíng)的其他單位必須具有相同的經(jīng)營(yíng)范圍,才可以認(rèn)為是同類(lèi)營(yíng)業(yè)。”第四種觀(guān)點(diǎn)認(rèn)為,“如果行為人在其他單位自己經(jīng)營(yíng)或?yàn)樗私?jīng)營(yíng)的營(yíng)業(yè)是在自己所在的國(guó)有公司、企業(yè)的經(jīng)營(yíng)范圍之中,那就應(yīng)該將該經(jīng)營(yíng)行為認(rèn)定為是經(jīng)營(yíng)同類(lèi)營(yíng)業(yè)的行為。”筆者認(rèn)為,判斷是否屬于“同類(lèi)經(jīng)營(yíng)”應(yīng)以行為人在其他單位所經(jīng)營(yíng)的營(yíng)業(yè)與自己所在的國(guó)有公司、企業(yè)的營(yíng)業(yè)是否形成現(xiàn)實(shí)或潛在的競(jìng)爭(zhēng)關(guān)系為標(biāo)準(zhǔn)。這種競(jìng)爭(zhēng)關(guān)系可能會(huì)導(dǎo)致國(guó)有公司、企業(yè)的經(jīng)營(yíng)業(yè)績(jī)明顯惡化(如相關(guān)的營(yíng)業(yè)收入減少、利潤(rùn)降低等)或者市場(chǎng)表現(xiàn)明顯困頓(如市場(chǎng)占有率明顯下降、穩(wěn)定的客戶(hù)群體流失嚴(yán)重等)。同時(shí),這種競(jìng)爭(zhēng)關(guān)系中,其他單位形成的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不是通過(guò)正當(dāng)?shù)纳虡I(yè)競(jìng)爭(zhēng)形成而主要是因?yàn)槎隆⒔?jīng)理利用職務(wù)便利干預(yù)下的結(jié)果。在進(jìn)行著一系列的推導(dǎo)認(rèn)定中,要排除正常的市場(chǎng)影響因素,分析形成了競(jìng)爭(zhēng)關(guān)系而認(rèn)定是否屬于同類(lèi)營(yíng)業(yè)。而不應(yīng)直接刻板地套用經(jīng)營(yíng)范圍來(lái)簡(jiǎn)單認(rèn)定。只要同一經(jīng)營(yíng)范圍就認(rèn)定屬于同類(lèi)營(yíng)業(yè)也會(huì)擴(kuò)大客觀(guān)條件的認(rèn)定范圍,從而錯(cuò)誤地打擊到其他正常的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
三、結(jié)語(yǔ)
對(duì)非法經(jīng)營(yíng)同類(lèi)營(yíng)業(yè)罪的深入認(rèn)識(shí)必須要追溯本罪的淵源,了解其與公司法領(lǐng)域中競(jìng)業(yè)禁止的特殊聯(lián)系。同時(shí),在認(rèn)定非法經(jīng)營(yíng)同類(lèi)營(yíng)業(yè)罪時(shí),重點(diǎn)需要把握其主體適格方面以及客觀(guān)條件方面的種種疑難之處。主體適格層面,對(duì)于實(shí)際公司經(jīng)營(yíng)中復(fù)雜的人員安排和職權(quán)設(shè)置要有清晰的認(rèn)知,不能隨意擴(kuò)大歸罪范圍。客觀(guān)條件方面,要對(duì)經(jīng)營(yíng)同類(lèi)營(yíng)業(yè)這一核心要件進(jìn)行解構(gòu)式的判斷與認(rèn)定,在判斷是否構(gòu)成犯罪以及罪輕罪重時(shí),對(duì)非法利益的計(jì)算也應(yīng)當(dāng)要立于本罪的立法原意及真正客體指向之法益,從而對(duì)正確適用并合理完善本罪之法律規(guī)定提供一定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