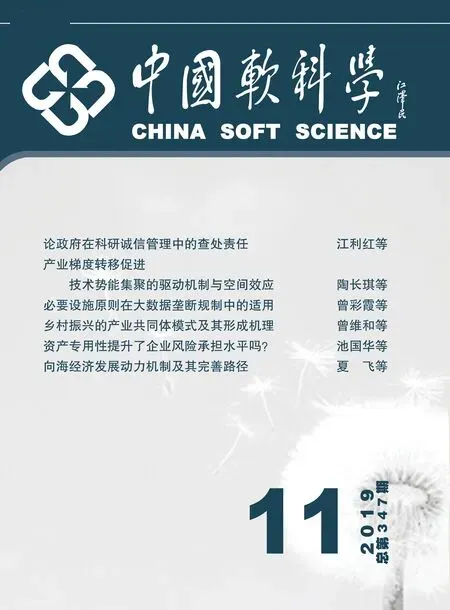企業(yè)創(chuàng)新與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和貿(mào)易自由化的調(diào)節(jié)作用
易靖韜,蔡菲瑩
(中國人民大學(xué) 商學(xué)院,北京 100872)
一、引言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對外貿(mào)易實(shí)現(xiàn)了歷史性跨越,加工貿(mào)易在穩(wěn)定就業(yè)、促進(jìn)外貿(mào)增長上做出了重大貢獻(xiàn)。20 世紀(jì)80年代中期我國對加工貿(mào)易企業(yè)進(jìn)口的中間投入品實(shí)行了免關(guān)稅的優(yōu)惠政策,推動(dòng)了加工貿(mào)易的迅猛發(fā)展。但隨著全球價(jià)值鏈分工發(fā)展,國際競爭格局深度調(diào)整,我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進(jìn)入新常態(tài),勞動(dòng)力等要素成本持續(xù)上升,資源約束日益趨緊,環(huán)境承載能力逼近上限,傳統(tǒng)競爭優(yōu)勢逐漸削弱,我國加工貿(mào)易增長質(zhì)量和效益不高,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不強(qiáng)等問題逐漸凸顯。在嚴(yán)峻復(fù)雜的國內(nèi)外環(huán)境倒逼下,我國加工貿(mào)易急需加快轉(zhuǎn)型升級,適應(yīng)新形勢的要求。“引導(dǎo)加工貿(mào)易轉(zhuǎn)型升級”是黨的十九大報(bào)告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也是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huì)以來黨中央的一項(xiàng)重要任務(wù)。轉(zhuǎn)變貿(mào)易方式是培育新的出口競爭優(yōu)勢的重要途徑之一。貿(mào)易方式不僅反映了我國出口企業(yè)在全球價(jià)值鏈中的地位[1],也影響著出口對技術(shù)進(jìn)步、產(chǎn)業(yè)升級和經(jīng)濟(jì)增長的溢出效應(yīng)[2]。近年來,我國貿(mào)易方式結(jié)構(gòu)逐步優(yōu)化,產(chǎn)業(yè)鏈更長、附加值更高,更能代表自主發(fā)展能力的一般貿(mào)易占總出口的比重由2000年的42.2%上升到2018年的57.8%。如何促進(jìn)我國出口企業(yè)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提升中國在全球價(jià)值鏈分工中的地位,是政府和學(xué)界亟須關(guān)注的重要課題。
近年來國內(nèi)外學(xué)者關(guān)于出口企業(yè)貿(mào)易方式?jīng)Q定因素的研究主要從以下幾個(gè)視角展開:生產(chǎn)效率[3-4];融資約束[1, 5-6];中間投入品貿(mào)易自由化[6-7];產(chǎn)業(yè)政策[3, 8-11],主要集中于補(bǔ)貼政策;人力資本[12-13];供應(yīng)鏈垂直整合[14-15]。而企業(yè)創(chuàng)新作為決定加工貿(mào)易轉(zhuǎn)型升級的關(guān)鍵因素[2],鮮有文獻(xiàn)進(jìn)行研究。由于缺乏創(chuàng)新驅(qū)動(dòng)的內(nèi)生動(dòng)力,關(guān)鍵技術(shù)、新產(chǎn)品開發(fā)成為難以突破的瓶頸,限制了加工貿(mào)易企業(yè)向高附加值的一般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此外,受制于企業(yè)內(nèi)部有限的創(chuàng)新能力和知識(shí)結(jié)構(gòu),企業(yè)難以整合和吸收新的外部知識(shí),削弱了合作過程中的知識(shí)擴(kuò)散和技術(shù)外溢效應(yīng)[16]。因此,創(chuàng)新能力不足的企業(yè)容易被鎖定在勞動(dòng)密集型、技術(shù)含量低、不具備戰(zhàn)略意義的價(jià)值鏈底端,形成出口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的“天花板”。為彌補(bǔ)這方面研究不足,本文試圖從企業(yè)創(chuàng)新的視角探討如何有效促進(jìn)企業(yè)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和升級。
同時(shí),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和中間投入品貿(mào)易自由化等制度環(huán)境對創(chuàng)新與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的關(guān)系具有關(guān)鍵的調(diào)節(jié)作用。首先,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通過有效控制企業(yè)創(chuàng)新研發(fā)的外部性,提高企業(yè)的研發(fā)投資回報(bào)和積極性[17];通過提高企業(yè)信息披露的意愿,減小與外部投資者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緩解企業(yè)的外部融資約束,為企業(yè)創(chuàng)新活動(dòng)提供持續(xù)性資金支持。正如習(xí)近平總書記所強(qiáng)調(diào)的,加強(qiáng)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是提高中國經(jīng)濟(jì)競爭力最大的激勵(lì)。隨著我國從貿(mào)易大國向貿(mào)易強(qiáng)國邁進(jìn),我國出口企業(yè)在“走出去”過程中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需求日益上升。健全完善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體系有助于為企業(yè)營造利于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的營商環(huán)境,激發(fā)企業(yè)的創(chuàng)造活力,促進(jìn)企業(yè)加快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其次,中間投入品貿(mào)易自由化水平的提高降低了一般貿(mào)易企業(yè)進(jìn)口中間投入品的成本,有利于企業(yè)進(jìn)口更高水準(zhǔn)的中間投入品[18-19],從而增強(qiáng)了進(jìn)口中間投入品的國際技術(shù)溢出。這有助于激勵(lì)企業(yè)加大研發(fā)投入,對進(jìn)口中間品進(jìn)行整合利用、消化吸收,進(jìn)行二次創(chuàng)新,進(jìn)而有利于加快企業(yè)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的步伐。
基于以上情境,本文利用2001—2006年中國海關(guān)進(jìn)出口數(shù)據(jù)和中國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的企業(yè)層面匹配數(shù)據(jù),探究創(chuàng)新對企業(yè)出口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的影響,并具體考察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和貿(mào)易自由化的調(diào)節(jié)作用。在當(dāng)前中美貿(mào)易戰(zhàn)撲朔迷離的局勢下,本文的研究仍具有很強(qiáng)的現(xiàn)實(shí)意義。正如國務(wù)院副總理劉鶴在2019中國國際智能產(chǎn)業(yè)博覽會(huì)上所表示,“我們愿以冷靜態(tài)度通過磋商和合作解決問題,堅(jiān)決反對貿(mào)易戰(zhàn)升級,貿(mào)易戰(zhàn)升級不利于中國、美國和全世界人民利益”。從長遠(yuǎn)來看,我國并不會(huì)因?yàn)槊绹臄嚲郑淖兩罨母锖蛿U(kuò)大開放的重大戰(zhàn)略布局,反而會(huì)將貿(mào)易戰(zhàn)的外部壓力轉(zhuǎn)變?yōu)閮?nèi)部改革與對外開放的動(dòng)力。可以看到,2018年我國舉行首屆中國國際進(jìn)口博覽會(huì),并宣布一系列擴(kuò)大開放的重大舉措,2019年第二屆進(jìn)博會(huì)如約而至,規(guī)模更大、質(zhì)量更高;在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方面,進(jìn)一步加大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執(zhí)法力度,堅(jiān)決懲處侵犯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行為,提高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審查質(zhì)量和審查效率,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因此,無論中美之間有沒有貿(mào)易摩擦、會(huì)不會(huì)升級,我國繼續(xù)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更高層次改革開放新格局的決心是不會(huì)被動(dòng)搖的。本文的研究結(jié)論為政策的制定實(shí)施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理論參考和經(jīng)驗(yàn)依據(jù)。本文的邊際貢獻(xiàn)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gè)方面:第一,聚焦企業(yè)創(chuàng)新對加工貿(mào)易轉(zhuǎn)型升級的關(guān)鍵作用,彌補(bǔ)現(xiàn)有研究之不足,為創(chuàng)新驅(qū)動(dòng)發(fā)展戰(zhàn)略提供了理論基礎(chǔ);第二,探討了創(chuàng)新促進(jìn)加工貿(mào)易轉(zhuǎn)型的邊界條件,從企業(yè)微觀層面實(shí)證檢驗(yàn)了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和中間投入品貿(mào)易自由化的重要調(diào)節(jié)作用,為政府引導(dǎo)加工貿(mào)易轉(zhuǎn)型提供了政策建議。本文剩余部分的結(jié)構(gòu)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進(jìn)行理論分析并提出假設(shè);第三部分建立計(jì)量模型,并對變量與數(shù)據(jù)進(jìn)行說明;第四部分對基準(zhǔn)實(shí)證結(jié)果進(jìn)行分析和穩(wěn)健性檢驗(yàn);最后總結(jié)全文,并提供政策建議。
二、理論與假設(shè)
(一)企業(yè)創(chuàng)新與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
創(chuàng)新驅(qū)動(dòng)發(fā)展是我國經(jīng)濟(jì)新常態(tài)下實(shí)現(xiàn)出口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升級的關(guān)鍵[2, 8]。首先,我國大多數(shù)加工貿(mào)易企業(yè)由于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較為薄弱,主要從事加工組裝和二次開發(fā),技術(shù)水平與市場領(lǐng)導(dǎo)企業(yè)存在較大差距,產(chǎn)品技術(shù)含量和附加值普遍較低。由于缺乏創(chuàng)新驅(qū)動(dòng)的自主發(fā)展能力,加工貿(mào)易企業(yè)在核心技術(shù)及產(chǎn)品上的自主研發(fā)和設(shè)計(jì)困難重重,難以向高附加值的一般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被鎖定在勞動(dòng)密集型、附加值低、不具備戰(zhàn)略意義的價(jià)值鏈底端,并形成路徑依賴。
其次,加工貿(mào)易企業(yè)較低的創(chuàng)新能力以及伴隨的有限的技術(shù)水平,不僅限定了委托企業(yè)的初始知識(shí)轉(zhuǎn)移水平,也削弱了合作過程中的知識(shí)擴(kuò)散和技術(shù)外溢效應(yīng)[20]。知識(shí)技術(shù)的轉(zhuǎn)移需要相對應(yīng)的吸收能力,尤其需要已有知識(shí)技術(shù)的相關(guān)認(rèn)知基礎(chǔ),以便有效地理解和處理新知識(shí)[21]。加工貿(mào)易企業(yè)知識(shí)儲(chǔ)備不足和內(nèi)部創(chuàng)新能力相對有限,很難對新的外部知識(shí)進(jìn)行篩選、識(shí)別、消化并利用[16]。缺乏相當(dāng)?shù)淖灾鲃?chuàng)新能力,除了很難從外部知識(shí)源充分獲益,企業(yè)也不太可能成為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22],最終導(dǎo)致企業(yè)轉(zhuǎn)型升級極為困難。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設(shè)H1:企業(yè)創(chuàng)新有助于出口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
(二)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與貿(mào)易自由化的調(diào)節(jié)作用
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通過幫助企業(yè)克服外部性問題和緩解外部融資約束,增強(qiáng)企業(yè)創(chuàng)新對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的促進(jìn)作用。首先,當(dāng)企業(yè)所在地區(qū)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較為薄弱,企業(yè)創(chuàng)新活動(dòng)獲得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會(huì)存在較強(qiáng)的外部性,即企業(yè)很難阻止外部其他企業(yè)通過技術(shù)溢出進(jìn)行的模仿或其他機(jī)會(huì)主義行為。這將損害創(chuàng)新企業(yè)的研發(fā)投資回報(bào),挫傷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積極性。而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力度的加強(qiáng),可以有效控制創(chuàng)新的外部性,有利于激勵(lì)企業(yè)持續(xù)創(chuàng)新[23],進(jìn)而加快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的步伐。其次,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水平的提高可以通過減小信息不對稱緩解企業(yè)的外部融資約束[23-24]。具體而言,當(dāng)企業(yè)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可以得到較好的法律保護(hù),企業(yè)會(huì)更愿意向外部投資者披露更多關(guān)于研發(fā)創(chuàng)新的具體信息,從而減少信息不對稱,有助于外部投資者進(jìn)一步了解和評估企業(yè),進(jìn)而提高投資意愿。而眾所周知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研發(fā)活動(dòng)需要大量而持續(xù)性的資金投入,外部融資則是企業(yè)獲取研發(fā)資金的主要渠道[25-26]。因此,更好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還可以通過幫助企業(yè)緩解外部融資約束為企業(yè)創(chuàng)新活動(dòng)的開展提供長期的支持和助力。由此,本文提出:
假設(shè)H2: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水平越高的條件下,企業(yè)創(chuàng)新對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的促進(jìn)作用越顯著。
而隨著中間投入品貿(mào)易自由化水平的提高,一般貿(mào)易企業(yè)進(jìn)口中間投入品的成本下降。這有利于企業(yè)進(jìn)口質(zhì)量更高、種類更豐富、技術(shù)含量更高的中間投入品[19]。中間投入品進(jìn)口水平的提升增強(qiáng)了“技術(shù)溢出效應(yīng)”,而這是提高企業(yè)技術(shù)創(chuàng)新能力的重要途徑之一[27]。企業(yè)不僅可以將進(jìn)口中間品投入應(yīng)用于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中以提高產(chǎn)品技術(shù)含量,還可以對進(jìn)口中間投入品中包含的技術(shù)創(chuàng)新成果加以整合利用,通過消化吸收進(jìn)行創(chuàng)新突破,擺脫核心技術(shù)受制于人的困境,獲取技術(shù)外溢的正外部性[18,28]。即中間投入品貿(mào)易自由化水平的提高不僅有助于鼓勵(lì)企業(yè)加大研發(fā)投入,加強(qiáng)內(nèi)部創(chuàng)新能力建設(shè),進(jìn)行原始創(chuàng)新,也有助于進(jìn)一步提升企業(yè)二次創(chuàng)新的水平,進(jìn)而有利于企業(yè)加快向高附加值的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因此,本文提出:
假設(shè)H3:中間投入品貿(mào)易自由化水平越高的條件下,企業(yè)創(chuàng)新對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的促進(jìn)作用越顯著。
三、數(shù)據(jù)與模型
(一)數(shù)據(jù)說明
本文的數(shù)據(jù)來源包括2001—2006年的海關(guān)進(jìn)出口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庫、中國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庫的制造業(yè)數(shù)據(jù)、《中國科技統(tǒng)計(jì)年鑒》和聯(lián)合國貿(mào)易和發(fā)展會(huì)議(UNCTAD)TRAINS數(shù)據(jù)庫。中國海關(guān)進(jìn)出口數(shù)據(jù),由國家海關(guān)總署統(tǒng)計(jì),涵括了所有HS8位碼的進(jìn)出口交易的各項(xiàng)重要信息,包括進(jìn)出口價(jià)值、貿(mào)易方式、企業(yè)信息、企業(yè)所有制類型等。鑒于中國海關(guān)進(jìn)口原始數(shù)據(jù)是月度數(shù)據(jù),本文根據(jù)研究需要將數(shù)據(jù)加總為企業(yè)層面年度數(shù)據(jù)。而中國工業(yè)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庫的統(tǒng)計(jì)對象是中國大陸地區(qū)年銷售額500萬元以上的大中型制造企業(yè),統(tǒng)計(jì)指標(biāo)包括企業(yè)工業(yè)總產(chǎn)值、新產(chǎn)品產(chǎn)值、營業(yè)利潤、應(yīng)付工資等主要技術(shù)經(jīng)濟(jì)和財(cái)務(wù)成本指標(biāo)等。遵循文獻(xiàn)的一般做法,剔除主要變量缺失或者小于0的樣本,雇員小于10人的以及不符合一般會(huì)計(jì)準(zhǔn)則的企業(yè),并對主要變量進(jìn)行價(jià)格指數(shù)平減。在匹配中國海關(guān)數(shù)據(jù)庫和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庫時(shí),先將海關(guān)數(shù)據(jù)庫中的企業(yè)名稱與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庫中的法人單位進(jìn)行匹配,若企業(yè)名稱與法人單位名稱無法對應(yīng),再采用企業(yè)電話、郵政編碼、法人代碼等多個(gè)企業(yè)特有屬性進(jìn)行匹配取其交集。各地區(qū)技術(shù)市場成交合同金額數(shù)據(jù)取自《中國科技統(tǒng)計(jì)年鑒》,按照企業(yè)所在省份進(jìn)行匹配。HS 6位碼產(chǎn)品進(jìn)口關(guān)稅取自TRAINS數(shù)據(jù)庫。
(二)變量設(shè)置

核心解釋變量企業(yè)創(chuàng)新(Innovationit)為企業(yè)i在t年的創(chuàng)新水平,參照現(xiàn)有創(chuàng)新文獻(xiàn)的一般做法[29-31],本文采用新產(chǎn)品產(chǎn)值占總銷售產(chǎn)值的比重來衡量。同時(shí),本文采用企業(yè)的專利數(shù)量進(jìn)行穩(wěn)健性檢驗(yàn)[32]。
調(diào)節(jié)變量地區(qū)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水平(IPR_protectionrt)為省份r在t年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水平,本文采用技術(shù)轉(zhuǎn)讓市場規(guī)模來衡量[24],即各省當(dāng)年技術(shù)市場成交合同金額與地區(qū)生產(chǎn)總值的比值。兩者的比值越高,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水平越高。各省當(dāng)年技術(shù)市場成交合同金額和生產(chǎn)總值分別來源于《中國科技統(tǒng)計(jì)年鑒》和《中國統(tǒng)計(jì)年鑒》。同時(shí),本文還采用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代理公司密度和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執(zhí)法力度作為穩(wěn)健性檢驗(yàn)指標(biāo)。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代理公司密度為各省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代理公司數(shù)目與技術(shù)人員的比值[33],各省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代理公司數(shù)目的數(shù)據(jù)來源于中國國家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局(SIPO)的專利代理年檢公告,各省技術(shù)人員的數(shù)據(jù)來源于《中國科技統(tǒng)計(jì)年鑒》。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執(zhí)法力度采用各省專利行政執(zhí)法的累計(jì)結(jié)案率來衡量[29],立案與結(jié)案數(shù)據(jù)來源于國家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局統(tǒng)計(jì)年報(bào),并用各省技術(shù)市場規(guī)模占全國比重加權(quán)計(jì)算獲得。

本文結(jié)合現(xiàn)有文獻(xiàn)控制了企業(yè)層面和行業(yè)層面的控制變量。企業(yè)層面控制變量包括以下變量。企業(yè)全要素生產(chǎn)率(TFP)采用OP方法[36]進(jìn)行測算,以克服聯(lián)立性問題和樣本選擇問題。融資約束(Finance)使用利息支出與固定資產(chǎn)的比值來衡量[19],如果該值越大則表明企業(yè)面臨的融資約束程度越小,加1取自然對數(shù)入模型。企業(yè)年齡(Age)即企業(yè)已生存年數(shù),取自然對數(shù)入模型。企業(yè)的補(bǔ)貼(Subsidy)取值為1當(dāng)企業(yè)存在補(bǔ)貼收入,否則為0。企業(yè)的盈利能力(Profitability)采用企業(yè)的經(jīng)營利潤與總資產(chǎn)的比值來衡量,加1取自然對數(shù)入模型。企業(yè)的平均工資(Wage)為企業(yè)應(yīng)付工資總額與員工總?cè)藬?shù)的比值,取自然對數(shù)入模型。為控制企業(yè)所有權(quán)屬性,本文設(shè)置國有企業(yè)(Soe)和外資企業(yè)(Foreign)兩個(gè)虛擬變量。行業(yè)層面控制變量包括行業(yè)集中度(HHI)和相對市場份額(Relativemarket)。行業(yè)集中度(HHI)赫芬達(dá)爾指數(shù)為企業(yè)的銷售額占行業(yè)總銷售額的比重的平方和。該指數(shù)越大,表明市場集中度越高,市場競爭程度越低;反之,市場競爭程度越高。考慮到我國規(guī)定加工貿(mào)易保稅進(jìn)口料件應(yīng)全部加工后復(fù)出口,不得在國內(nèi)銷售,國內(nèi)的市場需求可能會(huì)影響出口企業(yè)的貿(mào)易方式[7],本文控制了相對市場份額(Relativemarket),即行業(yè)(CIC-2)國內(nèi)市場與國外市場的相對規(guī)模比值,Relativemarket=(行業(yè)所有企業(yè)的銷售產(chǎn)值總和-出口+進(jìn)口)/出口。此外本文采用行業(yè)、省份、年度虛擬變量來控制行業(yè)(產(chǎn)業(yè)組織、要素密度等)、省份(市場化程度、政策差異等)、時(shí)間(宏觀經(jīng)濟(jì)、宏觀政策等)對本文研究問題的影響。
(三)計(jì)量模型設(shè)定
為檢驗(yàn)企業(yè)創(chuàng)新對出口貿(mào)易方式的影響,以及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和中間投入品貿(mào)易自由化對該影響的調(diào)節(jié)作用,本文設(shè)立如下模型:
Oshareijrt=α0+α1Innovationit+α2IPR_
protectionrt+α3IPR_protectionrt×Innovationit+α4Tariff_inputjt+α5Tariff_inputjt×Innovationit+η1Xit+η2Zjt+φj+φr+φt+εijrt(1)
其中,Oshare為一般貿(mào)易額比重,下標(biāo)i、j、r和t分別表示企業(yè)、行業(yè)、省份和年份;Innovationit為企業(yè)i在t年的創(chuàng)新水平;IPR_protectionrt為省份r在t年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水平;Tariff_inputjt為行業(yè)j在t年的中間投入品貿(mào)易自由化水平;IPR_protectionrt×Innovationit和Tariff_inputjt×Innovationit為交互項(xiàng)。Xit表示企業(yè)特征向量,包括TFP,F(xiàn)inance,Age,Subsidy,Profitability,Wage,Soe和Foreign;Zjt表示企業(yè)所在行業(yè)的控制變量,包括HHI和Relativemarket;φj為行業(yè)固定效應(yīng),φr為省份固定效應(yīng),φt為年份固定效應(yīng),εijrt為隨機(jī)擾動(dòng)項(xiàng)。
表1報(bào)告了本文計(jì)量模型所涉及變量的描述性統(tǒng)計(jì)。

表1 變量的統(tǒng)計(jì)描述
四、實(shí)證結(jié)果分析
(一)基準(zhǔn)分析結(jié)果
表2展示了計(jì)量模型(1)的逐步回歸結(jié)果。表2第(1)列為僅含控制變量的回歸結(jié)果,第(2)列為加入核心解釋變量企業(yè)創(chuàng)新(Innovation)的回歸結(jié)果,Innovation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水平與一般貿(mào)易比重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關(guān)系。第(3)列的回歸模型在第(2)列的基礎(chǔ)上加入各地區(qū)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變量(IPR_protection)以及與企業(yè)創(chuàng)新的交互項(xiàng)(Innovation×IPR_protection),可以看到企業(yè)創(chuàng)新和交互項(xiàng)都顯著為正,表明地區(qū)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對創(chuàng)新與一般貿(mào)易比重的關(guān)系起到正向調(diào)節(jié)作用,即企業(yè)所在地區(qū)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水平越高,企業(yè)創(chuàng)新對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的促進(jìn)作用越大。第(4)列的回歸模型在第(2)列的基礎(chǔ)上加入各行業(yè)中間投入品貿(mào)易自由化變量(Tariff_input)以及與企業(yè)創(chuàng)新的交互項(xiàng)(Innovation×Tariff_input),可以看到企業(yè)創(chuàng)新依舊顯著為正,交互項(xiàng)都顯著為負(fù),表明行業(yè)中間投入品進(jìn)口關(guān)稅對創(chuàng)新與一般貿(mào)易比重的關(guān)系起到負(fù)向調(diào)節(jié)作用,即企業(yè)所在行業(yè)的中間投入品進(jìn)口關(guān)稅越低,即貿(mào)易自由化水平越高,企業(yè)創(chuàng)新對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的促進(jìn)作用越顯著。第(5)列為模型(1)的最終回歸結(jié)果,各變量的系數(shù)方向和顯著性都保持不變。

表2 基準(zhǔn)回歸結(jié)果
注:***、**、*分別表示參數(shù)估計(jì)值在1% 、5% 、10% 的統(tǒng)計(jì)水平上顯著,括號(hào)內(nèi)數(shù)值為企業(yè)層面的聚類穩(wěn)健標(biāo)準(zhǔn)誤,以下各表同。
(二)穩(wěn)健性檢驗(yàn)
1.內(nèi)生性檢驗(yàn)
企業(yè)層面的變量可能由于不可觀測因素的存在或者變量測量偏誤而導(dǎo)致解釋變量的內(nèi)生性問題。參照現(xiàn)有文獻(xiàn)的一般做法,本文采用滯后一期企業(yè)創(chuàng)新水平和當(dāng)期行業(yè)平均創(chuàng)新水平作為工具變量進(jìn)行2SLS估計(jì)。表3報(bào)告了工具變量的檢驗(yàn)結(jié)果,與表2的基準(zhǔn)回歸結(jié)果基本一致,核心解釋變量Innovation和交互項(xiàng)Innovation×IPR_protection顯著為正,交互項(xiàng)Innovation×Tariff_input顯著為負(fù),說明表2的估計(jì)結(jié)果是穩(wěn)健的。兩個(gè)工具變量都分別通過了相關(guān)性LM檢驗(yàn)(P=0.00)、工具變量外生性Sargan檢驗(yàn)(P=0.00)以及弱工具變量Kleibergen-Paap Wald rk F統(tǒng)計(jì)量檢驗(yàn)。
2.核心變量測量
本文分別對因變量、自變量和調(diào)節(jié)變量進(jìn)行變量測量的穩(wěn)健性檢驗(yàn)。首先,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企業(yè)的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除了用一般貿(mào)易比重來衡量,我們還可以采用虛擬變量的定義方式,即依據(jù)企業(yè)當(dāng)年不同貿(mào)易方式的出口額占比,定義占比100%的純一般貿(mào)易企業(yè)為1,否則為0,回歸結(jié)果如表4所示。其次,我們采用企業(yè)的專利總數(shù)對核心解釋變量Innovation進(jìn)行穩(wěn)健性檢驗(yàn),回歸結(jié)果如表5所示。最后,我們采用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代理公司密度和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執(zhí)法力度作為調(diào)節(jié)變量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IPR_protection)的穩(wěn)健性檢驗(yàn)指標(biāo)。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代理公司密度為各省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代理公司數(shù)目與技術(shù)人員的比值,回歸結(jié)果為表6第(1)和第(2)列。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執(zhí)法力度采用各省技術(shù)市場規(guī)模占全國比重加權(quán)的專利行政執(zhí)法累計(jì)結(jié)案率來衡量,回歸結(jié)果如表6第(3)和第(4)列所示。可以看到采用新的變量測度方法后,表4、表5和表6的實(shí)證結(jié)果依舊穩(wěn)健,所有變量與表2結(jié)果基本一致。
3.估計(jì)方法
表7采用Tobit模型進(jìn)行估計(jì)方法的穩(wěn)健性檢驗(yàn),可以看到核心解釋變量企業(yè)創(chuàng)新(Innovation)依舊顯著為正,地方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IPR_protection)起到正向調(diào)節(jié)作用,中間投入品進(jìn)口關(guān)稅(Tariff_input)起到負(fù)向調(diào)節(jié)作用,所有變量的回歸結(jié)果與前文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估計(jì)結(jié)果是穩(wěn)健的。

表3 工具變量檢驗(yàn)

表4 被解釋變量穩(wěn)健性檢驗(yàn)

表5 解釋變量穩(wěn)健性檢驗(yàn)

表6 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調(diào)節(jié)變量穩(wěn)健性檢驗(yàn)

表7 Tobit估計(jì)方法穩(wěn)健性檢驗(yàn)
(三)進(jìn)一步分析
為了進(jìn)一步考察出口企業(yè)的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決策,本文按企業(yè)所在行業(yè)的科技水平以及企業(yè)所在地域進(jìn)行分組回歸。表8的第(1)和第(2)列匯報(bào)了高科技和低科技企業(yè)的分組回歸結(jié)果。遵循廣泛使用的OECD技術(shù)強(qiáng)度劃分標(biāo)準(zhǔn),將企業(yè)出口的核心產(chǎn)品的HS碼與ISIC(Rev. 3)進(jìn)行匹配和分組,并將高科技和中高科技兩類合并為高科技一組,將中低科技和低科技合并為低科技一組。可以看到,對于低科技企業(yè),創(chuàng)新水平的提高對其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的促進(jìn)作用更大,中間投入品進(jìn)口關(guān)稅降低、貿(mào)易自由化發(fā)揮的調(diào)節(jié)作用更為顯著。對于高科技企業(yè),所在省份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的正向調(diào)節(jié)作用更顯著。表8的第(3)、第(4)和第(5)列分別匯報(bào)了東部地區(qū)、中部地區(qū)和西部地區(qū)企業(yè)的分組回歸結(jié)果,可以看到各因素對企業(yè)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的影響存在著一定的區(qū)域差異。對于東部企業(yè),省份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和中間投入品貿(mào)易自由化都發(fā)揮了顯著的與理論預(yù)期相符的調(diào)節(jié)作用;對于中部企業(yè),省份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的正向調(diào)節(jié)作用不顯著;對于西部企業(yè),中間投入品進(jìn)口關(guān)稅的負(fù)向調(diào)節(jié)作用不顯著。

表8 按科技水平和地域分組檢驗(yàn)
五、結(jié)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基于2001—2006年中國海關(guān)數(shù)據(jù)和工業(yè)企業(yè)數(shù)據(jù),檢驗(yàn)了企業(yè)層面創(chuàng)新對企業(yè)出口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的影響,并具體考察了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和貿(mào)易自由化對創(chuàng)新與貿(mào)易方式關(guān)系的調(diào)節(jié)作用。本文的研究結(jié)果表明企業(yè)創(chuàng)新有助于一般貿(mào)易比重的提高,即促進(jìn)企業(yè)出口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地區(qū)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對創(chuàng)新與一般貿(mào)易比重的關(guān)系起到正向調(diào)節(jié)作用,即企業(yè)所在地區(qū)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水平越高,企業(yè)創(chuàng)新對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的促進(jìn)作用越大。行業(yè)中間投入品進(jìn)口關(guān)稅對創(chuàng)新與一般貿(mào)易比重的關(guān)系起到負(fù)向調(diào)節(jié)作用,即企業(yè)所在行業(yè)的中間投入品進(jìn)口關(guān)稅越低,即貿(mào)易自由化水平越高,企業(yè)創(chuàng)新對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的促進(jìn)作用越顯著。此外,中間投入品貿(mào)易自由化對低科技企業(yè)發(fā)揮的正向調(diào)節(jié)作用更為顯著,而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對高科技企業(yè)的正向調(diào)節(jié)作用更為顯著,且各因素對企業(yè)貿(mào)易方式轉(zhuǎn)型的影響還存在著一定的區(qū)域差異。
我們的研究試圖給我國企業(yè)和政府部門提供一定程度的理論參考和政策借鑒。當(dāng)前出口貿(mào)易的國際環(huán)境復(fù)雜多變,企業(yè)勤練內(nèi)功加快實(shí)現(xiàn)自身的轉(zhuǎn)型升級才是立身之本。出口企業(yè)亟需加強(qiáng)自主研發(fā)和創(chuàng)新,加強(qiáng)內(nèi)部創(chuàng)新能力的建設(shè)以及外部“產(chǎn)學(xué)研”合作,建立健全創(chuàng)新人才激勵(lì)機(jī)制,培育以技術(shù)、品牌、質(zhì)量為核心的出口競爭新優(yōu)勢,力爭參與更高層次的國際分工。對于政府,首先,應(yīng)從政策層面鼓勵(lì)企業(yè)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協(xié)同創(chuàng)新,為企業(yè)開展創(chuàng)新合作搭建平臺(tái),推動(dòng)“產(chǎn)學(xué)研”聯(lián)盟的建設(shè)。其次,加大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力度,切實(shí)落實(shí)十九大精神“強(qiáng)化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創(chuàng)造、保護(hù)、運(yùn)用”。正如習(xí)近平總書記所強(qiáng)調(diào),加強(qiáng)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是完善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制度最重要的內(nèi)容,也是提高中國經(jīng)濟(jì)競爭力最大的激勵(lì)。隨著我國從貿(mào)易大國向貿(mào)易強(qiáng)國邁進(jìn),我國出口企業(yè)在“走出去”過程中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需求日益上升。加強(qiáng)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已然成為我國參與全球貿(mào)易的制度標(biāo)配。健全完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體系,加強(qiáng)國際貿(mào)易中的海外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利益的保護(hù)與管理,為出口企業(yè)營造利于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的營商環(huán)境,激發(fā)企業(yè)的創(chuàng)造活力,促進(jìn)企業(yè)貿(mào)易方式的轉(zhuǎn)型升級。最后,正如習(xí)近平總書記在第二屆中國國際進(jìn)口博覽會(huì)上所強(qiáng)調(diào)的,進(jìn)一步促進(jìn)貿(mào)易自由化便利化,同更多國家商簽高標(biāo)準(zhǔn)自由貿(mào)易協(xié)定,建立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機(jī)制。通過高水平的雙邊或多邊貿(mào)易協(xié)定,推動(dòng)中間投入品進(jìn)口貿(mào)易自由化,進(jìn)一步降低高科技高質(zhì)量中間投入品的進(jìn)口關(guān)稅,以降低一般貿(mào)易企業(yè)的生產(chǎn)成本,引導(dǎo)加工貿(mào)易企業(yè)轉(zhuǎn)變出口貿(mào)易方式,提高出口產(chǎn)品附加值,提升中國在全球價(jià)值鏈分工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