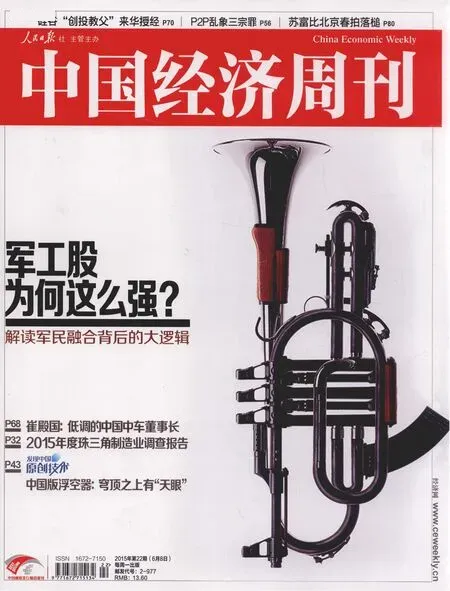解讀十九屆四中全會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創新
王紅茹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于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
10月31日晚,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全文公布,11月5日《決定》公布,其中提出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引人關注。
多年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一直作為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此基礎上,十九屆四中全會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何要增加這兩項?《決定》提出“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決定》為何首次提出土地、數據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
對于這些問題,《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日前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卓元。
首次明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包括的三方面內容
《中國經濟周刊》:此前,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剛剛召開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什么要增加這兩項內容?
張卓元: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1997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五大提出的基本經濟制度。十五大報告原文是這樣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細讀原文,十五大報告也只是說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并沒有說基本經濟制度只限于所有制結構。
一個社會的經濟體制,大體包括所有制、分配方式和運行機制等3個方面,三者之間關系密切。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是多種所有制,單一國有制不可能是市場經濟;所有制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互相配合;所有制結構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分配方式也要多樣化。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隨著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認識的進一步加深,十九屆四中全會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是順理成章、很自然的事情,在邏輯上也完全合理、符合實際。
十九屆四中全會是黨的歷史上首次用一次中央全會專門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研究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全會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審議通過《決定》,全面回答了在上述問題上,應該“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這個重大政治問題,既有理論上的新概括,又有實踐上的新要求,可以讓我們更加清晰地理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基本經濟制度,主要包括所有制結構、分配方式和運行機制這3個方面,分配就是指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運行機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這兩項跟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并列提升為基本經濟制度,可以更清晰、更準確地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從這方面看,就是一個重大理論創新。
首提土地、數據參與分配,著眼形成橄欖型收入分配結構
《中國經濟周刊》:《決定》提出“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其中,土地、知識、數據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是首次提出,這是出于什么樣的考慮?
張卓元:土地、知識、數據等生產要素之所以首次單獨提出參與分配,主要是著眼于提高人們的勞動報酬特別是熟練勞動者報酬與財產性收入,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形成橄欖型的收入分配結構,為實現高質量發展創造條件。
首先,將土地納入參與分配的生產要素,主要是著眼于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益,比如加快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農村集體土地直接入市等,都可以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其次,將知識和數據明確作為參與分配的生產要素,是基于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創新驅動發展的需要,也是與時俱進的一個生動體現。這不僅可以大大促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高科技行業、知識密集型行業的發展,產生更多的職業崗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還可以激勵人們通過不斷學習創新,提升技術和業務水平以及勞動技能,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生產效率的提高,促進高質量發展。
2020年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取得重大階段性成果
《中國經濟周刊》:從1992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到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到十九屆四中全會再一次強調“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此我們應該如何理解?
張卓元:每一次重申“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都會進一步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進一步堅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進一步明確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點任務。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336項改革舉措,目前正在按照黨中央部署的時間表、路線圖穩妥有序推進。但是,當改革進入深水區,涉及的問題會越來越多,領域越來越廣,矛盾越來越深,目前還有少量改革沒有完成,比如國資改革要從管企業到管資本為主轉變,正在擴大試點,還沒有完全完成;再比如稅制改革,尤其在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地方稅體系等方面,還有很多具體的工作需要繼續往前推進。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了200多項重大舉措,要求把制度建設和治理能力建設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繼續深化各領域各方面體制機制改革,推動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這些都有利于“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中國經濟周刊》:如何理解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性?
張卓元:按照2013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十九屆四中全會,又提出了包含三個時間點的“總目標”。
雖然第一個時間窗口是明年,但是我認為改革會一直進行下去。到2020年是要取得重大階段性成果。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生產力是不斷發展的,在發展過程中,有些管理體制、生產關系環節可能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就得進行改革。從這個意義上,并不是制度完善以后就不需要再改革了,改革沒有止境,只有進行時。但是當整個制度比較完善時,改革會呈現其階段性。總而言之,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改革也要不斷深化。
編輯:陳惟杉 chenweishan@ceweekly.cn編審: 張偉美編:孟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