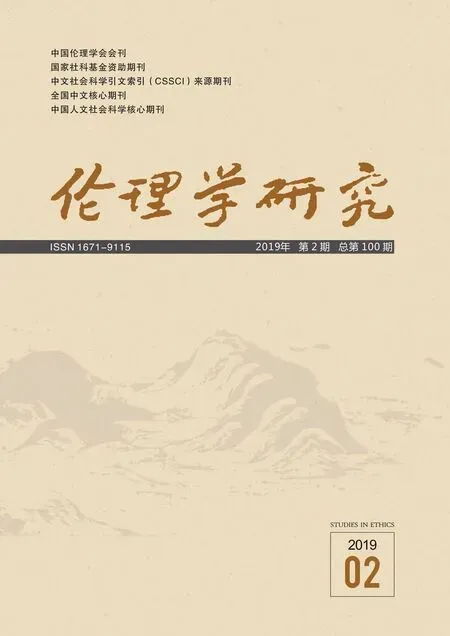論孔孟儒家倫理精神的基本特質(zhì)
劉湘溶,易學(xué)堯
引 言
倫理精神是民族倫理的深層結(jié)構(gòu),是民族倫理的內(nèi)聚力與外張力的體現(xiàn),其層面體現(xiàn)的是倫理規(guī)范的價(jià)值取向、對民族社會(huì)生活的內(nèi)在生命秩序的設(shè)計(jì)原理[1](P29)。中國傳統(tǒng)倫理精神無疑主要來自儒家。然而,儒家經(jīng)過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陽明等人的演繹發(fā)展,與最初的孔孟儒家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差別,孔孟儒家倫理精神隨著儒家理論的發(fā)展而變得斑駁不清。因此,對孔孟儒家倫理精神進(jìn)行準(zhǔn)確地辨析,就成為當(dāng)代儒家研究中的一個(gè)不容忽視的問題。準(zhǔn)確把握儒家倫理精神則必須理解孔孟儒家理論的內(nèi)在邏輯。而孔孟儒家的核心關(guān)切恰恰是孔孟儒家展開其理論演繹的邏輯起點(diǎn),是理解孔孟儒家的內(nèi)在邏輯的關(guān)鍵。因此,本文從厘清孔孟儒家的核心關(guān)切著手,辨析并總結(jié)了孔孟儒家倫理精神的基本特質(zhì),希冀通過這一邏輯理路而達(dá)到對孔孟儒家倫理精神的準(zhǔn)確理解與解釋。
一、孔孟儒家的核心關(guān)切及其倫理精神
在中國古代,普遍的觀念是認(rèn)為社會(huì)整體道德水平是趨于下降的。所以中文語言中有“人心不古”“大有古風(fēng)”等等說法。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正因?yàn)榇嬖凇安蝗什涣x”,所以才需要提倡“仁義”;從“大道通行”的理想狀況往下墮落,才有“仁義”之說。而從“大同社會(huì)”到“家天下”,孔子無疑也認(rèn)為社會(huì)整體道德水平是往下墮落的。佛教將佛法興衰分為“正法”“像法”“末法”三個(gè)時(shí)代,從“正法”到“末法”也是往下墮落的。
不幸的是,缺乏量化指標(biāo)來衡量社會(huì)整體道德水平高低,當(dāng)然也不存在相關(guān)的歷史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因此,它是上升還是下降是說不清的,學(xué)術(shù)界也從未有過嚴(yán)肅的討論。但是這個(gè)問題很重要,可以從兩個(gè)方面來講:
第一,這涉及到學(xué)術(shù)發(fā)展的最終目的。與中國不同,古代西方并不存在社會(huì)墮落的普遍觀念,也沒有孔子的這種危機(jī)感。因此,與中國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相反,西方倫理哲學(xué)的發(fā)展重邏輯與思辨。雖然西方倫理哲學(xué)也涉及到道德實(shí)踐,但總體來說,學(xué)者們專注于其理論體系構(gòu)建,而普遍并不關(guān)心它如何影響大眾。如果比較西方倫理學(xué)術(shù)對西方社會(huì)的影響,可以斷言,儒家思想對于中國社會(huì)的影響時(shí)間之久、程度之深與范圍之廣是任何一種西方倫理理論望塵莫及的。不能否認(rèn)西方倫理學(xué)對人類文明的巨大貢獻(xiàn),但是總體來說,其發(fā)展對于社會(huì)道德水平的影響有限是無可置疑的。尤其是近半個(gè)世紀(jì)以來,倫理學(xué)術(shù)發(fā)展對于民眾的直接影響更是日趨式微。這就引出一個(gè)問題:倫理學(xué)的發(fā)展最終目的是什么?科技發(fā)展可以用于指導(dǎo)生產(chǎn)實(shí)踐,倫理學(xué)的發(fā)展是否應(yīng)當(dāng)以提升社會(huì)道德水平為最終目的?如果是,那么什么樣的倫理精神才能夠提升社會(huì)道德水平?如何實(shí)現(xiàn)提升?
第二,這涉及對中國傳統(tǒng)倫理精神的準(zhǔn)確理解,尤其是孔孟儒家倫理精神。倫理精神是倫理實(shí)體的內(nèi)在邏輯及設(shè)計(jì)原理所體現(xiàn)出的價(jià)值導(dǎo)向與價(jià)值追求,因此對孔孟儒家倫理精神的準(zhǔn)確理解必須以對其理論內(nèi)在邏輯的全面認(rèn)知為基礎(chǔ)。孔子說“仁”孟子說“義”,他們講仁義正是希望挽救社會(huì)的墮落,希望提升社會(huì)道德水平,恢復(fù)到大同社會(huì)。然而,孔子卻“罕言仁”,因?yàn)樗匾暋吧斫獭保J(rèn)為道德是要踐行的。光說不做是“巧言令色鮮矣仁”,是無法感化別人,從而實(shí)現(xiàn)前述理想的。這奠定了后世儒家學(xué)術(shù)發(fā)展重實(shí)踐、輕邏輯與思辨的傳統(tǒng),包括后來的理學(xué)和心學(xué),都重視知行合一的。但是這一傳統(tǒng)也使得學(xué)術(shù)界長期以來對孔孟儒家理論建構(gòu)的內(nèi)在邏輯缺乏全面認(rèn)知,由此導(dǎo)致對孔孟儒家倫理精神的誤解與片面解讀。
孔孟儒家的核心關(guān)切正是社會(huì)道德水平的提升,其理論建構(gòu)圍繞這一基本目標(biāo)而展開——這是理解孔孟儒家理論的內(nèi)在邏輯及其倫理精神的關(guān)鍵。孔孟所追求的大同社會(huì),其本質(zhì)特征就是社會(huì)整體道德水平達(dá)到至高的水平。在孔孟的設(shè)想中,“社會(huì)大同”的實(shí)現(xiàn)途徑是:通過統(tǒng)治階層的道德自律,以“德治”持續(xù)地教化民眾以提升其道德水平,最終達(dá)到“大道通行”的境界。因此,儒家從一開始就注意到個(gè)人道德對他人的感化作用——“君子之德風(fēng),小人之德草”,重視個(gè)人道德追求對整個(gè)社會(huì)道德水平的提升,乃至社會(huì)的和諧穩(wěn)定的積極意義。具體到理論的建構(gòu)則遵循了如下三個(gè)原則:道德超越利益、“人皆有向善之心”和道德是自律的。其中,第一個(gè)原則是確立社會(huì)道德共識的必要條件,第二個(gè)原則是道德力量發(fā)揮作用的機(jī)制,第三個(gè)原則則為道德秩序的自我恢復(fù)提供基礎(chǔ)。很顯然,這種內(nèi)在邏輯結(jié)構(gòu)正是為了確保社會(huì)道德水平的提升。
根據(jù)孔孟儒家的內(nèi)在邏輯及其理論的目標(biāo)指向,可以將孔孟儒家倫理精神的基本特質(zhì)總結(jié)為三點(diǎn):“志道據(jù)德”“為仁由己”與“慎終追遠(yuǎn)”,其中,志道據(jù)德是孔孟儒家倫理的整體價(jià)值導(dǎo)向,對應(yīng)的外在倫理規(guī)范是“仁”和“義”;為仁由己是其倫理實(shí)踐的執(zhí)行關(guān)鍵,對應(yīng)的倫理規(guī)范是“禮”;而慎終追遠(yuǎn)則為為仁由己提供內(nèi)在動(dòng)力,包涵了孝道精神和造福子孫的價(jià)值導(dǎo)向。
二、“志道據(jù)德”
《論語·述而》中孔子說“志于道,據(jù)于德,依于仁,游于藝。”本文將“志于道”和“據(jù)于德”合稱“志道據(jù)德”,用作對孔孟儒家倫理精神的概括。朱熹如此解釋“志于道,據(jù)于德”:“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dāng)行者是也。如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據(jù)者,執(zhí)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2](P90)“志”是“一心向慕”,“據(jù)”指“堅(jiān)守”,簡言之,“志道據(jù)德”是指“堅(jiān)守對道德的追求”,其實(shí)質(zhì)就是“崇德尚賢”。
如果說“社會(huì)道德水平的提升”是孔孟儒家的核心關(guān)切,那么“崇德”作為孔孟儒家倫理精神基本特征便是順理成章的。“崇德”的倫理精神體現(xiàn)為孔孟儒家將“仁”本身視為最高目的,也即體現(xiàn)儒家道德的超越性——這一點(diǎn)可以從大量的孔孟言論中得到佐證,例如:孔子說過“求仁得仁又何怨”,“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等語。孟子服膺于孔子,但崇德思想?yún)s有其自身特點(diǎn)。第一,較之孔子更激進(jìn)——表現(xiàn)為孟子對于湯武革命的態(tài)度。在《孟子.梁惠王》中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wù)D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認(rèn)為統(tǒng)治者無德,則推翻其統(tǒng)治是正義的。這實(shí)際上是一種更激烈的崇德精神。第二,孟子進(jìn)一步將統(tǒng)治者的德與民生聯(lián)系起來,從而發(fā)展出了民本思想。他明確地說“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統(tǒng)治者的德最終要體現(xiàn)為為民眾謀利益。
孔子將“仁智勇”稱之為“三達(dá)德”,后來又將“仁義禮”并稱。從“仁智勇”到“仁義禮”是道德與倫理的關(guān)系,即前者理想人格的理論闡釋,而后者是其實(shí)踐規(guī)范。孔子對“義”的解釋是:“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賢”是有德之人,“尊賢”即“崇德”精神表現(xiàn)為外在的倫理規(guī)范。這一點(diǎn)應(yīng)從孔孟的政治倫理角度去理解。孔孟明確提出“舉賢才”治天下的思想,孔子政治理想是從民眾中推舉出的賢能統(tǒng)治者(“選賢與能”),并且居上位者率先踐行“仁”,以其德行感化民眾。賢德之人被推舉出來,正是由于社會(huì)崇德的倫理精神。因此,在民眾中樹立崇尚道德的風(fēng)氣至關(guān)重要,所以孔子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尊賢”即崇尚道德。而“禮”則是對仁和義的具體規(guī)定:“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焉。”
儒家“安貧樂道”主張正是源于“志道據(jù)德”精神。《論語·里仁》“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安貧樂道”反映在中國傳統(tǒng)教育中,“讀圣賢書”不是為了升官發(fā)財(cái),而是為了“成圣成賢”,即成就自身道德。儒家對人生的成敗也是以道德境界為評判。典型的如顏淵,終其一生社會(huì)地位不高,貧困潦倒,而且沒有什么驚人的事跡。若以世俗功利眼光評價(jià),顏?zhàn)拥娜松鸁o疑是非常失敗的;然而孔子卻對其大加贊揚(yáng),視為自己最得意的弟子,后世儒家更是將顏淵列為亞圣。
值得注意的是,墨家同樣也有“尚賢”思想,例如,墨子提出“尚賢為政之本也”。但是墨家認(rèn)為物質(zhì)功利是人的根本屬性,把“義”定義為“義、利也”,認(rèn)為倫理的實(shí)質(zhì)就是物質(zhì)功利。“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3]與墨家不同的是,孔孟儒家的“志道據(jù)德”精神并非基于物質(zhì)利益,而是超越利益的,如孔子所說“求仁得仁又何怨”。與墨家類似,西方倫理學(xué)也是通過利益得失的合理性來判斷公平與正義——這無形中就將利益當(dāng)作了目的,使得西方倫理學(xué)墮落為一種利益分析的學(xué)術(shù)。基于利益的道德必然走向道德的反面。由于利益分析這一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的影響,在西方社會(huì)不主張謙讓,而是普遍信奉:“如果不捍衛(wèi)自己的利益,別人一定會(huì)侵害它”。堅(jiān)持自己的利益或許沒錯(cuò),問題是現(xiàn)實(shí)中很難把握這個(gè)“度”,社會(huì)矛盾由此而不斷產(chǎn)生和積累。試想一下,如果“從利益的角度來判斷是非”成為普遍思維方式,社會(huì)各階層之間、民眾之間的利益爭斗將日益激烈,社會(huì)道德水平無疑會(huì)日趨下降。而道德是制度的基礎(chǔ),社會(huì)道德水平越低,制度的執(zhí)行成本就越高。當(dāng)制度開始失效時(shí),為了堵住原制度漏洞就需要更復(fù)雜的制度。如此一來,社會(huì)將陷入一個(gè)惡性循環(huán),制度成本越來越高,最終結(jié)果是社會(huì)秩序的全面崩潰。反觀孔孟儒家,其道德理論中很少涉及“公正”命題,它實(shí)際上是以謙讓、以德服人代替了西方倫理學(xué)中的“公正”,從而避免了道德上的邏輯悖論。
三、“為仁由己”
“為仁由己”出自《論語》:“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孟儒家“為仁由己”的倫理精神即是個(gè)人的道德?lián)?dāng)精神①。“社會(huì)道德水平的提升”需要每個(gè)人從自身做起—,正因?yàn)椤暗赖聯(lián)?dāng)”是社會(huì)道德水平提升的關(guān)鍵,孔孟儒家極為重視個(gè)人的“道德?lián)?dāng)”,《論語》和《孟子》中的大部分均可視為對個(gè)人“道德?lián)?dāng)”或與此有關(guān)的論述。例如《論語》中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jìn),吾往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而《孟子》中則有“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自返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等等。
為仁由己精神是孔孟儒家倫理實(shí)踐的執(zhí)行關(guān)鍵,對應(yīng)的倫理規(guī)范是“禮”。《論語·顏淵》中,孔子說:“克己復(fù)禮為仁。一日克己復(fù)禮,天下歸仁焉!”“克己”是個(gè)人的道德?lián)?dāng),社會(huì)道德水平的提升是“天下歸仁”,而銜接這二者的正是“禮”。孔孟儒家的“禮”是由為仁由己精神轉(zhuǎn)化而來的外在倫理規(guī)范。在孔孟看來,“政治”即是“禮治”,“禮”是對居上位者的約束,要求居上位者作出道德表率——“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正因?yàn)椤盀槿视杉骸迸c政治的密切關(guān)系,“為仁由己”便不再僅僅是個(gè)人修養(yǎng)問題,而是關(guān)乎天下社稷。因此,孔孟儒家的為仁由己精神便很自然地?cái)U(kuò)展為以天下為己任的擔(dān)當(dāng)精神。
道德修養(yǎng)(即所謂“修身”)最終主要體現(xiàn)為個(gè)人的道德?lián)?dāng),即“為仁由己”。《大學(xué)》中開宗明義地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這就把“修身”(或者說個(gè)人的道德?lián)?dāng))與社會(huì)治亂興衰緊密聯(lián)系起來,將“修身”視為天下之“本”。圍繞“修身”的實(shí)踐路徑,孔孟儒家的“為仁由己”精神被繼承發(fā)揚(yáng),在后世儒學(xué)中便發(fā)展出理學(xué)和心學(xué)兩大支流。理學(xué)的格物致知和心學(xué)的“致良知”均是系統(tǒng)的“修身”(即個(gè)人道德修養(yǎng))理論,是“為仁由己”的實(shí)踐理論。
孔孟儒家倫理精神的“為仁由己”本質(zhì)上類同于西方倫理中的“自由意志”。但“自由意志”由于缺乏現(xiàn)實(shí)動(dòng)力而在實(shí)踐中淪為空洞的說教——這是西方倫理思想對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影響有限的主要原因。與此不同的是,孔孟儒家的“為仁由己”以“世界大同”為目標(biāo),以“慎終追遠(yuǎn)”為動(dòng)力,從而使儒家理論具備了極大的實(shí)踐可行性和頑強(qiáng)的生命力。這也造就了二千年來儒家思想對于中國社會(huì)的巨大影響。
在西方倫理思想中,自由意志的基礎(chǔ)是理性;與之類似的是,孔孟儒家極其強(qiáng)調(diào)內(nèi)省。孟子說:“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發(fā)。發(fā)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后世的程朱理學(xué)和陸王心學(xué)繼承發(fā)揚(yáng)了自我反省的精神,因之內(nèi)省精神成為東方文化的一種鮮明特質(zhì)。內(nèi)省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西方倫理學(xué)中的“理性”,但較之“理性”更具積極意義。總結(jié)來說,孔孟儒家“為仁由己”的倫理精神包括個(gè)人道德的擔(dān)當(dāng)精神以及以天下為己任的擔(dān)當(dāng)精神。由于“擔(dān)當(dāng)”必然要求“內(nèi)省”,因此可以認(rèn)為“為仁由己”的倫理精神已經(jīng)涵蓋了內(nèi)省精神;故在此對孔孟儒家倫理精神的總結(jié)中不再單獨(dú)列出內(nèi)省精神。
四、“慎終追遠(yuǎn)”
對于社會(huì)中的個(gè)人而言,其自覺“道德?lián)?dāng)”(即“為仁由己”)的意義和動(dòng)力何在?孔孟儒家要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道德水平的提升”的這一理論目標(biāo),就必須解決個(gè)人“為仁由己”的內(nèi)在動(dòng)力問題。在當(dāng)時(shí)的歷史文化環(huán)境下,孔孟儒家很自然地選擇了“慎終追遠(yuǎn)”作為這一問題答案。因之,“慎終追遠(yuǎn)”與“志道據(jù)德”、“為仁由己”一起構(gòu)成了孔孟儒家的倫理精神體系。
“慎終追遠(yuǎn)”出自《論語》所載:“曾子曰:慎終追遠(yuǎn),民德歸厚矣”。孔安國注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yuǎn)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于厚也[4]。朱熹《論語集注》注曰:“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yuǎn)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于厚。”[2]以孔安國與朱熹為代表的傳統(tǒng)解釋把“慎終”和“追遠(yuǎn)”理解為“治喪”和“祭祀”某種態(tài)度——這是“慎終追遠(yuǎn)”的字面意義。而據(jù)周遠(yuǎn)斌考證,“慎終”應(yīng)指“孝、悌”等德行善舉,自始至終,一而貫之,不但有始,而且還要能終;而“追遠(yuǎn)”應(yīng)指行仁之道,“死而后已”[5]。在古代的技術(shù)條件下,文字記錄與流傳的成本極高,因而古人論述問題時(shí)只能言簡意賅,往往在字面之下隱藏了更深遠(yuǎn)的意義。周的解釋可以看作從慎終追遠(yuǎn)的字面意義的引申,這無疑是正確的方向。但本文認(rèn)為,這一解釋仍不夠準(zhǔn)確,“慎終追遠(yuǎn)”的引申意義必須在理解孔孟儒家的核心關(guān)切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詮釋。
“追遠(yuǎn)”是指追思祖先之德,孔孟儒家繼承了周代“德”“得”相通的傳統(tǒng),認(rèn)為祖先之德能蔭庇后人。孔孟儒家由此認(rèn)為,后人有德是先人的榮耀,是為“光宗耀祖”;而后人無德則是辱沒了先人。孔子說“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先人的事業(yè)與美德后繼無人是為“無后”,“無后”是對祖先的不孝。可見,“追遠(yuǎn)(追思祖先之德)”的倫理精神不僅僅體現(xiàn)為重視對祖先的祭祀,更重要的是繼承和發(fā)揚(yáng)祖先的美德。
“追遠(yuǎn)”的外在表現(xiàn)之一就是重視對祖先的祭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本人對鬼神的態(tài)度是存而不論,也曾說過“敬鬼神而遠(yuǎn)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語,然而他對祭祀一事卻非常重視。孔孟儒家為何強(qiáng)調(diào)祭祀的重要性,甚至將其置于軍國大事之上?學(xué)術(shù)界將儒家對祭祀的重視簡單地歸因于中國古代先民的祖先崇拜,這至少是不準(zhǔn)確的。這一問題與孔孟儒家的社會(huì)理想的建構(gòu)邏輯有關(guān)。“建國君民,教學(xué)為先”,孔孟儒家極其重視對民眾的道德教化。但是現(xiàn)實(shí)中可以作為“道德楷模”的人物很少而且不完美——可以說,這是一種稀缺資源。這一現(xiàn)實(shí)困難迫使儒家另辟蹊徑,將祖先視為道德楷模。而事實(shí)上,以祖先為道德楷模具有很大的優(yōu)勢:首先,將祖先神圣化、道德楷模化符合人類的普遍心理;其次,相對于在世的人物,已逝的人不會(huì)再犯錯(cuò)誤,因而其作為道德楷模的風(fēng)險(xiǎn)較小。在儒家看來,祭祀的意義在于“慎終追遠(yuǎn)”,“追遠(yuǎn)”即追思祖先之德。可見,儒家重視祭祀的根本原因并非祖先崇拜,而是出于道德教化的需要。
而將“慎終”解釋為“慎重辦理死者的喪事”是不對的。“民德歸厚”即是“社會(huì)道德水平的提升”,這正是孔孟儒家的核心關(guān)切所在。很顯然,“妥善處理喪事”是無法承載如此宏大的主題的,這種解釋在邏輯上說不通。“慎終”與“追遠(yuǎn)”對應(yīng)。如上文所述,“追遠(yuǎn)”是指追思祖先之德;那么“慎終”則是指“謹(jǐn)慎自己的言行,因?yàn)檠孕惺У乱矔?huì)禍及子孫”。西方歷史上有句話:“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慎終”的意思恰恰與之相反,大致可以理解為“造福子孫”或“為子孫謀”。但孔孟儒家的“慎終”精神卻不能僅僅理解為“為子孫謀”,而是已經(jīng)升華為“為萬世開太平”。舉例來說,有權(quán)勢的父母利用自己的特權(quán)為子女開后門,這對別人是不公正的——這不是真正地為子孫謀,更不是“慎終”——因?yàn)槟悴⒉荒鼙WC你的子孫世代都有這種特權(quán),終有一天,他們也會(huì)受到類似的不公正的對待。因此,真正的“為子孫謀”應(yīng)當(dāng)是(從自身做起)提升社會(huì)道德水平,努力創(chuàng)造一個(gè)公正、友善和諧的社會(huì)環(huán)境。惟其如此,子孫才能世世代代受益。“始作俑者,其無后乎”,孔子的這句話說的正是“慎終”。
如果缺乏內(nèi)在動(dòng)力,“為仁由己”在實(shí)踐中就會(huì)淪為空談。慎終追遠(yuǎn)精神將個(gè)人道德修養(yǎng)與家族、民族乃至國家的傳承緊密聯(lián)系起來,從而為個(gè)人的道德追求提供了內(nèi)在動(dòng)力。一個(gè)人為什么要做一個(gè)好人?為什么要提升自身的道德修養(yǎng)?在孔孟儒家看來,這既是感恩祖先的蔭庇,又是造福后世子孫;而作惡不僅辱沒了祖先,且對子孫后世起了一個(gè)壞的示范作用。
結(jié) 語
習(xí)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95周年大會(huì)上的講話提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依本文理解,“不忘初心”是“追遠(yuǎn)”,“牢記使命”則是“慎終”——這正是孔孟儒家“慎終追遠(yuǎn)”倫理精神的體現(xiàn)。社會(huì)道德水平直接關(guān)系到后世子孫的福祉,社會(huì)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shè)必須重視社會(huì)道德水平的提升。那么如何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道德水平的提升?孔孟儒家指明的途徑即“志道據(jù)德”(即“崇德尚賢”)和“為仁由己”;而“慎終追遠(yuǎn)”則為“志道據(jù)德”和“為仁由己”提供了內(nèi)在動(dòng)力。
當(dāng)前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領(lǐng)域言必稱制度而普遍忽視社會(huì)道德的基礎(chǔ)作用;而道德是制度執(zhí)行的基礎(chǔ),當(dāng)整體社會(huì)道德水平低下時(shí),絕大多數(shù)制度都會(huì)失效。不可否認(rèn),重視制度的西方倫理思想有其普世意義,但是其弊端也十分明顯,而孔孟儒家恰恰是補(bǔ)救這種弊端的良藥。可以說,恢復(fù)和重建孔孟儒家的倫理精神是擺脫當(dāng)代社會(huì)道德困境的重要途徑。
[注 釋]
①需要注意的是,作為倫理精神的“道德?lián)?dāng)”是指個(gè)人的“道德?lián)?dāng)”,與“社會(huì)道德?lián)?dāng)”是兩個(gè)不同的概念。“社會(huì)道德?lián)?dāng)”是指“社會(huì)道德”產(chǎn)生作用的機(jī)制。其內(nèi)容包括:第一,社會(huì)道德價(jià)值、原則、規(guī)范來自于何方即由誰提供、制定的;第二,社會(huì)道德內(nèi)容的合法性是由誰、通過什么方式來論證的;第三,社會(huì)道德教化是由誰來主導(dǎo)的;第四,誰、及其如何在對社會(huì)道德進(jìn)行這些作業(yè),從而使某一社會(huì)的道德呈現(xiàn)為如此的狀貌,哪些力量應(yīng)對社會(huì)道德負(fù)怎樣的責(zé)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