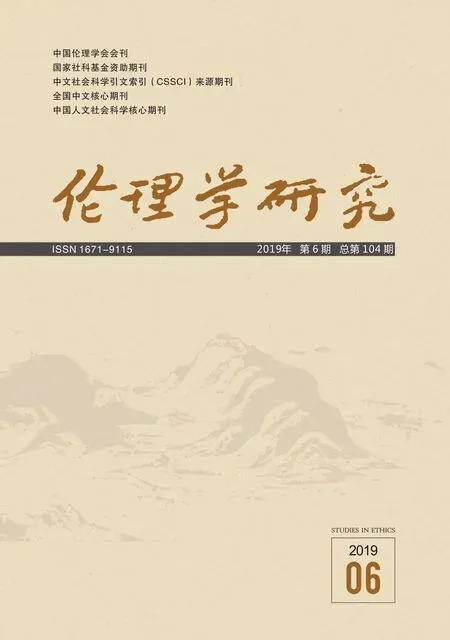論君子人格的精神特質
陳詩師,鄧名瑛
有關君子人格的論述,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內容,那么,儒家所謂的君子人格具有什么樣的精神特質呢?近些年來,隨著君子文化研究熱的出現,學者們從不同方面對君子人格的內涵、特點等進行了分析,有人認為,君子的特點是,在價值追求上成己、成人、成物、治國平天下;在價值選擇上重義、重公;在工夫落實上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心憂天下、敢于擔當;也有人認為,君子是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之人,是胸懷天下、濟世化民之人,是自強不息、勇于進取之人;還有人認為,君子是和而不同、德才兼備,內以成己、外以成物之人;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應該說,上述概括有重疊之處,也有不同之處,而且每一種概括都是合理的,然而,盡管如此,筆者仍然以為這些概括偏于零亂化和碎片化,不利于我們從總體上把握君子人格的精神特質。有見于此,本文將從人格構成的四個要素即知、情、意、行出發,對君子人格的精神特質進行系統性的分析與綜合相統一的研究,并期待通過這種研究,既能將學者們對君子人格精神特質的各種概括納入一個有邏輯演進關系的系統中,又能使君子人格的精神特質呈現出相應的層次性,從而使我們更加準確地把握君子人格的精神特質。
大體來說,筆者認為,君子人格的精神特質包含了相互關聯且層層推進的四個層次,即志道信念、仁愛情懷、責任意識和擔當精神,這四個層次大體上對應于人格構成的四個要素。
一、志道信念
“君子”一詞,在中國古代文化中,開始并不具有道德意義。“君”,從“尹”,從“口”,“尹”表示治理事務,“口”表示發號施令,所以,“君”就是指發號施令治理事務的人,這是一種政治的視角,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春秋左傳·襄公九年》),這里所謂“君子”“小人”就是指政治地位上的。后來,“君子”一詞逐漸獲得了道德的意義,如《周易·象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又如《論語·憲問》“君子之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再如《論語·顏淵》“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等等,類似的材料很多,不一一列舉。從上述引用的材料中,可以明顯地看出,這里的“君子”已經具有濃厚的道德意味了。在往后的歷史發展中,由于受德治主義思維方式的強烈影響,“君子”一詞的政治地位意涵越來越受制于其道德意義,故而,“君子”一詞的道德意義被大大彰顯。
“君子人格”是儒家人格精神的道德化體現,是儒家理想人格中現實性與理想性的統一。作為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君子人格的精神特質,首先表現在對儒家所倡揚之“道”的執著而堅定的追求,即一種強烈的志道信念。關于這一點,儒家的創始人孔子有大量的論述,《論語·述而》(下引《論語》只注篇名):“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篤行好學,守死善道”(《泰伯》);“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為了追求“道”甚至可以“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等等。此外,孔孟儒者認為,道德的重要或主要表現形式就是仁義,強調君子對仁義的追求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里仁》)儒家經典《中庸》也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慎其獨也。”這里的“道”是理想、目標,仁義則是道的最為重要的內容。由此可見,儒家對道的追求是何等的堅定執著!
儒家之所以把對“道”的追求看作是人生的重要目標,是因為在儒家看來,天人合一,天道與人道合一,人的存在的依據和價值都來源于天道。“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儒家早期經典《尚書·泰誓》中的這句話,已經初步表達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子對天道談的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但是儒家思孟學派中的兩位代表人物子思和孟子卻非常自覺地表達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經典《中庸》相傳為子思所作,《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孟子則認為,人性本善,而這種本善的人性即是來源于天道的,他引用《詩·大雅·烝民》說,“‘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懿,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懿也,故好是懿德。’”(《孟子·告子上》)孟子在這里的意思是說,人的美好的德性是來源于天道的,這種美好德性也就是孟子所謂的“四端之心”即仁、義、禮、智,所以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盡心上》)孟子還認為“萬物皆備于我”,通過存心、養性的工夫,就能達到“上下與天地同流”的境界,而這也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思孟學派的這一思想為后世大多數儒家學者所繼承。
君子志道,必然要將其體現在自己的生活中,為此就要知“道”、踐“道”,即要明了“道”的內涵并將之作為自己的生活指南,通過自己的生命實踐在生活中呈現出來。那么,儒家所講的“道”,其內涵是什么?在先秦儒家典籍中,關于“道”的內容有不同表述,如《周易》“一陰一陽之謂道”;《論語》“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中庸》“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等等,這些不同的表述,內容其實是相通的。這是因為,儒家所講的“道”都是圍繞人類生命甚至萬物生命的存在來展開的。以“群經之首”的《周易》而言,“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它的主題,用現代哲學語言來說,它是探討生命真相的學問。“生生之謂易”是其基本命題;“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其對生命存在和發展的內在動力的基本概括;“日生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則是對天地運化以化生萬物之美德的褒贊。這個“生生之德”就是“仁”,《康熙字典》引程顥“心如谷種,生之性,便是仁”作注,又引《六書正譌》“元,從二從人。仁則從人從二。在天為元,在人為仁”。“元”是生命的開端,《周易·乾卦·彖》“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坤卦·彖》“至哉!萬物資生”,乾、坤兩卦是《周易》中的基本卦,乾元、坤元表示生命的起點,“在天為元,在人為仁”,天道人道相通,所以,生和仁也是相通的。《論語·季氏》“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雖然談的是政治上不上正軌的問題,但其背后隱藏的實質則是孔子憂慮社會秩序的破壞而引起人的生命危淺的社會現狀,他強調人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與自己身份和地位相稱的權利和義務邊界內活動,權利和義務邊界的表現形式就是“禮”,而“禮”的實質則是仁,“禮之用,和為貴”,“禮”雖然是講“分”的,但作為社會生活中的規范形式,其追求的最高目的則是“和”,即穩定和諧的社會秩序,只有在和諧的秩序中,人和萬物才能更好地生存和發展,這種能使人和萬物更好地生存和發展的“和”,正是仁的要求和體現。《中庸》作者講的“中庸之道”,實際上講的也是中正和諧之道,“不偏之謂中”,“不偏”之“中”即是“正”,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人和萬物正常、健康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內在平衡,如果人和萬物的內在要素不能保持一種“中”即平衡,那么,就會窒息自己的生機和活力,“和”則是中的外在表現形態,也是“中”外化為人和萬物生存和發展必須遵循的規律——道,所以“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有達到中和的狀態,天地才能有自己正常的位置,萬物才能生長發育。由此可見,《中庸》的著眼點還是“生生”亦即是“仁”。為實現以“中”為本而達至“和”的狀態,萬物之間就不能相互侵害,不同的意見可以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但不能強制劃一,所謂“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這樣,才能“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綜上所述,盡管先秦時期不同的儒家學者對儒家之道有不同的表述,但其旨趣都指向儒家特別強調的核心價值——“仁”。正因為如此,君子對道的追求,說到底,是對儒家核心價值“仁”的追求,話句話說,知“道”、踐“道”,在君子的生活實踐中,必然體現為知“仁”、踐“仁”,從而仁愛情懷就必然成為儒家君子人格精神特質的題中應有之意。
二、仁愛情懷
在儒家的價值系統中,因為仁實際上是道的另一種表達,因而是一個可以涵蓋其他德目的范疇,被稱為德之首,所以,要成為君子,首先就要把抽象的對道的執著追求化為具體的對仁的執著追求,這就是仁愛情懷。那么,什么是仁愛情懷呢?要回答這一問題,就必須從儒家仁范疇的含義入手。
什么是仁?在先秦儒家學者中,孔子談仁最多,《論語》記載談論仁的次數達109 次,可見,仁在孔子思想中的地位。但是,盡管如此,我們卻難以從中找到關于仁的一般性概括,究其原因,正是我們上面提到的仁為德之首,可以涵蓋其他德目導致的。所以,孔子總是針對不同的弟子和不同的情境來闡釋其對仁的理解,最典型的莫過于弟子樊遲的三次問仁,孔子給出了三個不同的回答(參見《論語》《子路》《雍也》《顏淵》)。在三次回答中,孔子有一次提到了“仁者,愛人”的命題,這也成為后世儒者對仁的普遍性理解。先秦時期另一位儒家學者孟子直接把人的惻隱之心看作是仁或仁的開端,“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相較于孔子而言,孟子以“惻隱之心”來概括“仁”,非常明確地把“仁”規定為“同情心”和“愛心”,這和孔子的“仁者,愛人”的思想是相吻合的。基于以上分析,把儒家的“仁”理解為“愛”是有依據的。
儒者所講君子的仁愛情懷,是由孟子的惻隱之心開顯出來的由近及遠的愛親、愛人、愛眾、愛生命的系統,是對親人、與自己關系相對親近(不同于親人)的他人、大眾以及其他生命存在的同情心、愛心,是一種源于自身而又經過不斷的道德修養而形成的“沛然莫之能御”(《孟子·盡心上》)的情感,以這種情感投射并體現生活世界,就是君子的仁愛情懷。這種仁愛情懷又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
一是內在的情感層次。孟子認為,作為仁愛源頭的惻隱之心是人所固有而不假外求的。“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孟子·告子上》)這就是說,仁義禮智這些道德品性,是與生俱來的,人們之所以把它們看作是外在的東西,是因為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前已提及,孟子認為仁義禮智的源頭就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這“四端”之心。在孟子看來,四端之心,乃是人之為人的依據,“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同上)孟子之所以把四端之心看作是人之為人的依據,其理由正是它們是人內心中存在的不可泯滅的道德情感,這些道德情感的流露是純粹的、不帶有任何功利目的的,“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同上)
人具有四端之心,只是具備了成為君子的可能性,要成為真正的君子,則需要在生活中時時保持并不斷擴充四端之心,這既是一個人逐步成為君子過程,也是一個人的仁愛情懷在生活實踐中不斷普及于人和天地萬物的過程,它首先表現為“仁者,愛人”:對親人的愛,所謂“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論語·學而》)”;對他人的愛,所謂“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同上《雍也》)”“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同上)”;它也是一種悲天憫人同時努力改變他人生活處境而達至大同的情懷,“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禮記·禮運》)。其次,這種仁愛情懷還表現為對非人類生命的尊重和關切。孟子聽說梁惠王不忍看將要牽去祭鐘的牛瑟瑟發抖的樣子,提出用羊來代替牛,孟子問梁惠王,牛和樣同樣是動物生命,為何不忍牛被殺而忍羊被殺?梁惠王無法解釋,而孟子認為這是梁惠王有仁術的表現,“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梁惠王上》)①。這種尊重非人類生命的思想還體現在儒家的其他典籍中,如《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安萌芽,養幼少”;“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孟夏之月)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眾,毋發大樹”。這里講的是人類對自然物的取用要因時而動,春天要保護幼小的生物生命,夏天正是生物生長的旺盛其,要任其自由生長。孔子的弟子曾參也說:“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禮記·祭義》);“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麝、毋卵。”(《禮記·月令》)“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即使尊貴如天子,只要是懷胎的動物,是不能使用和用于祭祀的。由此可見,儒家基于天人合一的理念,君子人格的意識飽含了對天地的敬畏之情以及仁民愛物的情懷。
二是價值理念層次。仁愛之心上升為理念層面,最突出的就是民本主義思想的提出。民本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尚書·泰誓》“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這是說上天所聽到的和看到的,都是民眾所聽到的和看到的,言下之意,既然君主受命于天,那么君主就必須保持對天的敬畏,而天意來自民意,所以對天的敬畏就必然落實于對民的敬畏。《尚書·五子之歌》“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已具備了民本主義思想的雛形,到了戰國時期,儒家學者孟子提出著名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的思想,是古代民本思想較為完整的形態。孟子以后,歷代儒者對民本思想多有發明,漢代賈誼在《過秦論》中,總結秦亡教訓,認為秦亡的根本原因在于統治者以嚴刑峻法盤剝民眾,從而導致失去民心,所以他提出“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宋代儒家學者石介為宋仁宗上《論根本策》,指出“善為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孰為天下?孰為國家?民而已矣。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虛矣,國家名號矣。空虛不可居,名號不足守”。明清之際的王船山、顧炎武、黃宗羲都有豐富的民本思想,特別是黃宗羲提出了振聾發聵的“天下為主,君為客”(《明夷待訪錄·原君》)的思想,對晚清的思想啟蒙起了積極作用。
民本思想包含的畏民、重民、憂民、利民、安民、富民、教民等內涵,使君子的仁愛情懷得到了理性升華。
三是制度設計層次。仁愛情懷在理性思考中凝結為民本思想,這是君子仁愛情懷的升華,但僅此還不夠,還必須通過制度設計落實于現實政治生活中。在這方面,孟子是儒家學者的典型代表,孟子把孔子德治思想推進了一步,他以民本主義和性善論為基礎,提出了系統完整的仁政學說,其中就包含實行仁政的制度設計,盡管在歷史上,這一設計從未真正施行過。
在孟子的思想中,實行仁政的制度機制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制民之產”,要讓民眾有恒定的財產能夠維持家庭穩定的生活需要,民眾才能認可君主的統治,生活才會安寧有序。“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孟子·梁惠王上》)”;“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同上)”。二是省刑罰,薄賦斂。孟子認為,君主賦稅重,民眾生活貧困,社會就不能長治久安,為避免這種情況,統治者就必須省刑罰,薄賦斂。”易其田疇,薄其稅收,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孟子·盡心上》)“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不愿藏其于市矣。關,饑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愿出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愿耕于其野矣。”(《孟子·公孫丑上》)三是謹癢序之教,讓民眾懂得孝悌的道理。“謹癢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就是要認真辦好教育,提高民眾的道德素質,這樣才能達到如《禮運》篇所講的幼有所養,老有所依、所歸的社會氛圍。
總之,儒家所講的君子的仁愛情懷是一個系統整體。然而仁愛情懷畢竟還只屬于情感或是情感升華為理性的思想領域,還不是一種現實的力量,它要化為一種現實的力量,還必須進一步轉化,這就是君子人格精神特質中的責任意識。
三、責任意識
責任,在漢語系統中,有兩個基本含義,一是指份內之事;二是指因未做好份內之事產生的不利后果。根據對責任內涵的這種理解,所謂責任意識,就是人在意識和自我意識的基礎上,對自己應做的份內之事以及自己未能做(好)份內之事將會產生的相關后果的一種自覺意識,與此相應,君子的責任意識,就是君子對自己應做的份內之事以及對未能做(好)份內之事的一種自覺意識。那么,在儒家看來,君子的份內之事有哪些呢?以下,我們對此作些分析。
責任是一個關系范疇,是在人與自身以及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中發生的,這就是說,人在生活世界中,有多少重關系,就有多少重責任,相應地,一個意識和自我意識健全的人就會產生與相關責任相對的責任意識。儒家認為,人的最基本的關系有五種,“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中庸》)”,這五種關系有三種是屬于家庭關系的,因而,它不足以概括儒家所講的責任范圍。
梁啟超先生認為“儒家哲學,范圍廣闊。……其學問最高目的,可以《莊子》‘內圣外王’一語括之。”(《儒家哲學》)“內圣外王”雖非儒家首創,但在儒家經典《大學》中卻非常明顯地體現了這一思想。《大學》的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前五者被視為內圣之業,后三者被視為外王之業。由此看來,儒家所講的君子的責任意識,主要包含如下四個方面,即對自身的責任意識,對家庭的責任意識,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意識,對宇宙萬物的責任意識。
自我責任意識。對自身的責任意識,指的是人應怎樣對待自己的生命存在的問題,回答的是如何對自身生命進行價值定位的問題。這里又有兩個方面,一是人如何對待自己的自然生命的問題。儒家認為,對待自己的自然生命的基本原則是“珍生”,自然生命雖然具有個體性,但個體卻不能隨意支配自己的生命,“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孝經·開宗明義》)”,身體發膚是父母給的,孝順父母是從愛惜自己的生命開始的。二是人如何對待自己的社會生命的問題。儒家認為,作為社會的人,人應該“務義”,即人應該成為那些正當、崇高價值的承擔者和化身。如孔子認為,一個人如果沒有仁德,不講禮義,就不配稱為真正的人,“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荀子說認為,人比其他物存在高貴的地方在于人有“義”,“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智,禽獸有智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智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荀子·王制》)。一般來說,“珍生”與“務義”是可以并存的,但不排除兩者相互沖突、只能二者擇一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儒家強調“舍生取義”,“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總之,在自身責任意識問題上,儒家強調珍生與務義的統一,在兩者發生沖突,則要舍生取義。
家庭責任意識。所謂家庭責任意識,是指一個人對自己在家庭關系中應做的份內之事以及未做(好)份內之事的后果的一種自覺認識。儒家認為,人類的道德生活是從家庭開始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大學》講“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齊家”②,是外王的第一步。每個人在家庭、家族關系中的身份和地位不同,其權利和義務也不同,如夫妻和諧(《詩經·小雅·棠棣》“妻子好和,如鼓瑟琴”)、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每個成員明確自己的權利和義務,這是具有自覺家庭責任意識的表現,這種自覺的家庭責任意識,是建設和諧家庭、營造良好家風的保障,反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會出現“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史記·太史公自序》)”的結局,家不和,國不穩。
國家、民族責任意識。應該指出,這里所謂國家、民族責任意識,并不十分準確,這是因為,在先秦時期,家、國、天下概念各有所指。“家”,如前所述,是諸侯家臣的領地,“國”是指諸侯各自的領地,由“家”構成,而所有的“國”則構成天子領地,即所謂的“天下”,這是分封制下的產物。秦以后,廢封建,立郡縣,“家”的范圍縮小,“國”與“天下”始同一。至于民族概念,更是近代民族國家興起以后才出現的,中國古代有“華夷之辨”和“夷夏之防”的說法,這里的“夷”“夏”都不是近代意義上的民族概念。由此可見,儒家所講的國、族指的是由華夏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的國。正因為如此,所謂國家、民族責任意識,是指一個人對由華夏族建立的國和華夏族本身應做的份內之事以及未能做自己的份內之事所導致的后果的自覺認識。這種責任意識最集中的表現,就是對國和族的“忠”,“為國之本,何莫由忠……夫忠興于身,著于家,成于國,其行一焉。是故一于其身,忠之始也;一于其家,忠之中也;一于其國,忠之終也。”(《忠經·天地神明章》)“忠”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精忠報國,為國、族的利益竭盡所能,甚至不惜犧牲生命。“一身報國有萬死”“茍利社稷,死生以之”(《左傳·昭公四年》)。二是公忠體國,即秉持公正之心,為國、族辦事。“忠者,中也,至公無私。”(《忠經·天地神明章》),公正不偏,才能一心為國,進而達到“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漢書·賈誼傳》)。當然,在儒家德治主義的視野中,國與天下并不能完全等同,儒家主張“以德配位”,“君權神(天)授”,有德者之國才是與天下合一的,無德者之國與天下是分離的,在這種情況下,君子的立場是“從道不從君”,所以,明清之際的思想家顧炎武才振聾發聵地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觀點,“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日知錄·正始》)”。
宇宙萬物責任意識。人是宇宙萬物中的一員,所謂人的宇宙萬物責任意識,是指人從自己與宇宙萬物的關系以及自身在這種關系中的地位出發,對自己應做的份內之事包括未能做份內之事而產生的后果的自覺認識。在這種責任意識表現為,首先,與仁民并稱的愛物,儒家認為萬物和人一樣,都是陰陽五行氣化而成,所以,人和萬物是一體的,即所謂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如張載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西銘》),就把萬物看成是人的朋友。其次,贊天地之化育。“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中庸》)。當然,這需要人盡己之性為前提。再次,使萬物各歸其正。王陽明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人有未盡處”(《傳習錄上》),就是這個意思。
以上,儒家關于君子人格責任意識的思想,也構成由近及遠的系統結構,一個人能否成為君子、有無責任意識,是其中重要的一環,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基于儒家君子人格仁愛情懷的責任意識,仍然不是成就君子之道的終點,要成就真正的君子,必須把這種責任意識轉化為成自覺的實踐行動,勇于承擔,敢于負責。這種勇于承擔,敢于負責的精神,就是君子人格特質中的勇于擔當精神。
四、擔當精神
“擔”“當”二字,在漢語系統中,并不是一開始就連用的,而是分開使用的。擔,《正韻》釋為“背曰負,肩曰擔”,《釋名》“擔,任也,任力所勝也”。當,主要義項也有三,《玉篇》釋當“任也”,《晉語》“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雍”,對當的解釋是“當,猶任也”,這是把“當”解釋為“任”,這和擔的意思是一樣的。當,還有“遇見”“機遇”的意思,《左傳·昭公七年》“圣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后必有達人”,這里的“當”即是“遇見”,成語中的“正當其時”的當也是這個意思。“適可”,也是當的一個意涵,《左傳·哀公元年》“逢滑當公而進”中的“當”,《康熙字典》釋為“不左不右”。當的含義還有不少,但與本文相關的僅為第一義項即“任”。擔、當二字連用,文獻顯示自宋代始,以“擔當”二字檢索《四庫全書》,可以發現它最早出現在《二程遺書》中,“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③,要得人擔當了”(《二程遺書》卷二上),此后,“擔當”一詞在宋明儒者中被廣泛使用。程顥使用“擔當”一詞,其含義和現代漢語“擔當”的含義已經沒有區別了,都是擔負、承當的意思。
所謂擔當精神,是指在責任意識的基礎上形成的把自己應做的份內之事,堅決付諸行動并承擔其后果的心理意識,它是君子行為持續不斷的內在驅動力。人們常常把擔當精神與責任意識混為一談,其實,兩者雖然有聯系,但也有區別,如果說,責任意識是人們對自己應做的份內之事的自覺意識,那么,擔當精神則是對責任意識的實踐落實,沒有責任意識,不可能形成擔當精神,而有了責任意識,也不必然地形成擔當精神,這是因為把責任付諸實踐,需要更多的前提條件,如堅定不移的意志、責任主體的素質、敢于承擔行為后果的勇氣,用儒家的話說,就是要具備智、仁、勇“三達德”,而責任意識的形成僅僅是一個對自身角色身份所內含的權利與義務的認知過程,事實上,大多數人都明白自己的責任,但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把這種責任意識轉化為一種切實的擔當。可見,儒家所講的君子人格的形成,最終要落實到具有強烈實踐品格的擔當精神上來。那么,君子的擔當精神體現在哪些方面呢?筆者認為,君子的擔當精神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勇于把自己的職責負于背、擔在肩并付諸行動的積極主動精神。
儒家特別強調“任事”,所謂“任事”,就是要把自己的職責勇敢擔當起來并付諸行動。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一個士人,一個君子,把實現仁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要有恢弘的氣度和堅毅的品格,因為責任重大,路途遙遠,要有死而后已的準備,孔子為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論語·憲問》),他有感于魯君昏庸無能,于是離開魯國,開始了長達十幾年周游列國、宣傳推廣自己政治理想的行程,盡管始終不被重用,卻仍然無怨無悔;孟子目睹當時社會秩序的崩潰,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南宋理學家胡宏在“道學衰微、風教大頹”的嚴峻形勢下,憤然而起,宣稱“吾徒當以死自擔”(《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面對明中葉“天理愈明,而人欲愈滋”的士風和社會風氣,王陽明疾呼“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傳習錄·答顧東橋書》),等等。當然,儒家強調的“任事”的“事”是指當做之事,即是與儒家價值觀相適應之事,在這里,“義”是“事”的標準,“義者,宜也”,宜即合適、恰當,而是否合適、恰當,則是以儒家價值觀作為判斷標準的。正因為如此,儒者強調君子應有所為,有所不為,“所為”要受“當不當為”的制約。總之,以義為基礎、動力和保障的任事精神,是君子人格擔當精神重要體現。也正是這種積極主動的任事精神,滋養著中國文化的血脈,護持著中國文化的生機,使中華文明生命歷數千年而不墜。
二是自強不息,仁智雙修,不斷完善和提升自身素質,為積極主動“任事”提供堅實基礎的進取精神。
把所當為之事負于背、擔在肩,是需要以主體的相關素質為基礎的。正因為如此,真正的儒者特別強調君子必須仁智雙修,即不斷進行內在的道德修養和知識修養,完善并不斷提升個人素質。仁的修養凝成君子之德,而智的修養則凝成君子之才,德才兼備,是為君子④,把“德才全盡”者稱為“圣人”,可看作是司馬光的一家之言。
在先秦儒家代表人物中,孟子對德性修養特別重視,而對知識技能的培育很少涉及,這和其他儒家學者不同,如孔子很重視學生知識、技能的培養,他借鑒周代貴族教育的內容,把當時稱為“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的內容融于教學過程中,培養了一批身通“六藝”的學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中庸》提出了“尊德性而道問學”的原則,要求學者把內在的心性修養和外在的學問追求結合起來,提倡“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其中的“博學之”就包含了廣泛學習各種知識的意思。《大學》講“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格物到修身,就包含了知識學習和德性養成兩個方面的內容。《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辭上》)”,怎樣“繼善成性”?《周易》提出君子“修業進德”的命題,所謂“修業”,在《周易》看來,就是“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系辭上》),“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系辭下》),這是以“觀”的方式去把握宇宙萬物真理的過程,也是知識的獲得和積累的過程。從“進德”而言,《周易》提出君子應“慎言行”和“開物成務”的思想。關于“慎言行”,《易傳》引孔子的話說,“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系辭上》)關于“開物成務”,《易傳》說,“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易”即生生之理,但這種生生之理的實現卻不是純自然的過程,其中包含了人的主體性因素的參與,“擬之而后言,議之而后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所以,“天地設位,圣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系辭上》),這里的“圣人成能”,就是開物成務,人文化成。可見,先秦儒者是主張人的完善尤其是要成為君子,必須在知識技能和德性養成上齊頭并進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無論是“德”的養成,還是“才”的培育,都需要一種自強不息、不斷進取的精神。這種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既表現為對責任的堅守,如孔子贊美顏回“其心三月不違仁”(《論語·雍也》),肯定顏回對仁德的堅守;又表現為為達目的而克服困難的勇氣,“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論語·里仁》);“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中庸》),沒有這種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是不可能成就君子人格的。
三是勇于承擔自身行為后果的勇氣。人的任何行為都必然導致一定后果,這些后果對于行為主體來說,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對于常人來說,積極的結果自然是樂觀其成,而對于消極的結果,則未必會坦然接受。君子之所以為君子,是因為他的行為“配義與道”,所以能不同于流俗,不論遇到何種結果,都能做到“不動心”,達到一種“無入而不自得焉”的境界。孔子說,一個君子,只要“唯義所適”,而不要在乎他人對自己的不解甚至誤解,“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論語·學而》)。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孟子甚至把行仁、踐仁過程中所遭受的磨難,看作是人格完善之借資,“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為也,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正因為如此,對于義之所在,孟子才有“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公孫丑上》)的果決。先秦儒家強調的這種君子氣概,為歷史上真正的儒者所信奉,宋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于謙“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等,都是其真實寫照。這種為了道義而甘愿承擔一切后果的精神,是君子之所以能成為君子的終極保障,沒有這種擔當,則前述君子人格的種種精神特質都將化為烏有。
小 結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志道信念、仁愛情懷、責任意識、擔當精神,構成君子人格精神特質的四個層面,它們層層遞進,相互支持,成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學界有關君子人格精神特質的其他闡釋諸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和而不同、憂患意識、仁民愛物等等,都可以在這個體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從哲學反思的意義上看,從任何一種對君子人格精神特質的具體闡釋(如自強不息)出發,經過哲學上不斷地“第二次提問”,最終都要回到“志道信念”這一點上來,因此“志道信念”是君子人格養成的起點,也是君子人格精神特質不斷孕育的起點,而擔當精神則是志道信念的最終落實。如此,方能真正體現出“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哲學方法論原則。
關于君子人格精神特質的思想,起源于先秦,又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生活實踐中不斷豐富、發展,已經深深植根于中華文化的血脈中,成為中華文明歷久不墜并不斷發揚光大的寶貴基因,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深層文化土壤,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動力之源。
[注 釋]
①人和自然生態處在物質與能量的交換系統中,無論是牛還是羊,從人的角度看既具目的價值,也具工具價值。在“釁鐘”的過程中,牛或羊實現其對人類而言的工具價值是必然的,但孟子認為身臨其境的君子會有“不忍之心”,“君子遠庖廚”,則可以消除這種不自適的心理狀態。
②此處的“家”不是指現代意義上的家庭,古代天子分封諸侯,諸侯分封家臣,家臣的領地就是“家”,但儒家既然認為“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那么,處理好家庭、家族的關系,自然也是齊家的題中應有之義。
③介甫即王安石,其時王安石施新政,行青苗法,朝中多爭議,程顥受皇帝意了當此事。
④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卷一中說:“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是故才德全盡謂之圣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