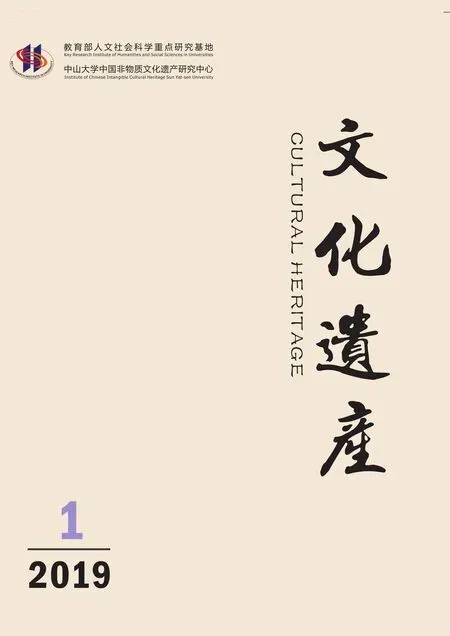漢晉文人琴的地域文化特色及其成因*
王 娜
古琴發展至東漢,不僅出現了桓譚《新論·琴道》、蔡邕《琴操》等琴論著作,還出現了三篇專門以琴命名的賦*漢代四篇以琴命名的賦,分別為劉向《雅琴賦》、傅毅《琴賦》、馬融《琴賦》、蔡邕《彈琴賦》,除劉向《雅琴賦》為西漢賦之外,余三篇皆作于東漢。。這固然與東漢古琴的質地結構和時代政局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但除時間上的歷史趨同之外,還表現為空間上的地域趨同。遺憾的是,在地域分布方面,學界多從古琴流派討論不同地域演奏風格*《琴史》載趙耶利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延徐逝,有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之俊。”見(宋)朱長文:《琴史》卷四,見《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八,第16頁;《琴旨錄要》稱:“中州派高古端嚴、寬宏蒼老……浙派清和善俗……金陵派之參序有節、抑揚有紀,可謂得古韻之遺……虞山派,嚴氏之學,必體認清微澹遠四字,得中和之用,應妙合之機”,見《自遠堂琴譜 琴旨錄要下》,載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 北京古琴研究會《琴曲集成》(第十七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282頁。,但對于古琴所具備的超乎其他樂器的獨特文化品格的形成,鮮有探討。事實上,漢晉時期,以桓譚、嵇康、戴逵為代表的相铚文人琴家,以蔡邕、阮瑀、阮籍為代表的陳留文人琴家,以傅毅、梁鴻、馬融為代表的扶風文人琴家,分別以其獨立不懼、隱忍沉潛和逸氣達生的地域文化特色,奠定了古琴在中國文化史和樂器史上獨具特色的文化品格。
一、相铚文人琴家與古琴孤清高潔的文化品格
東漢至魏晉時期,相、铚二地(今屬安徽省淮北市)先后出現了桓譚、嵇康和戴逵三位著名文人琴家。這三位既博學多才,又特立獨行,并且都有自己獨特的哲學思想和人生追求,在他們身上,“獨立不懼”成為突出的人格特征,成為相铚文人琴家一脈相承的地域文化特色,奠定了古琴孤清高潔的文化品格。
桓譚,沛國相人,“好音律,善鼓琴”,著有《新論·琴道》。他堅定獨立、不媚世俗,旗幟鮮明地反對讖緯迷信。《后漢書》載“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南朝宋)范曄:《后漢書》卷二十八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956頁。桓譚的自守、默然,體現出一代“儒宗”的品行操守。錢鐘書評價桓譚“識超行輩”[注]錢鐘書:《管錐編》,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第196頁。,在風云際會的兩漢之際,不僅天下之士紛紛獻符命以求榮,就連西漢皇族后裔劉歆也用“讖諱”學說附會王莽新朝,一代大儒揚雄效《封禪書》作《劇秦美新》。唯桓譚獨自堅守,堅決反對讖緯神學,并振聾發聵地提出無神論觀點,體現出“識超行輩”的遠見卓識和“獨立不懼”的人格特征。光武帝一朝,桓譚在光武“信讖,多以決定嫌疑”的情況下,上疏直言“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惹光武帝不悅。又在光武帝當面問“吾欲讖決之,何如?”時,明知不順從的回答會觸怒龍顏,依然選擇“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并“極言讖之非經”[注](南朝宋)范曄:《后漢書》卷二十八上,第959-961頁。,觸怒光武帝,被遷六安郡丞,不幸病卒于途中。在桓譚身上體現出堅守底線、不畏權貴的獨立精神。
桓譚之后的铚人嵇康[注]關于嵇康的出生地,《晉書》載“譙國铚人”,今一種說法認為是譙郡铚人(今安徽宿縣西南),見童強《嵇康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62頁;另一種說法認為是沛國铚人(今安徽宿縣西),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中國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209頁。《輿地廣記》載宿州“漢屬沛郡。東漢、晉屬沛國”,臨渙縣“本铚縣,漢屬沛郡。東漢屬沛國。晉屬譙郡”。可見,以上說法大同小異,皆因歷代行政區劃變革而略有區別。漢晉的铚地,在今安徽省淮北市,因此本文省略“譙”或“相”,直接稱嵇康為铚人。,“有奇才,遠邁不群”[注](唐)房玄齡等:《晉書》卷第四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369頁。,著有《聲無哀樂論》、《琴賦》和琴曲《嵇氏四弄》,因特立獨行,堅決不與司馬氏合作而被殺。嵇康之死,對中國歷史及思想史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尤其在兩晉,對于嵇康之懷念心祭,竟成為當時重要文化現象,成為一大批知名人士一個難以化解的情結。”[注]徐公持:《理極滯其必宣——論兩晉人士的嵇康情結》,《文學遺產》1998年第4期。從某種意義上說,嵇康代表了中國思想史上最“獨立不懼”的理想人格,達到了中國古代“士”風范的最高境界。對于嵇康的命運悲劇,大致有兩種觀點,一種歸結于性格原因:《晉書》載時人孫登言“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注](唐)房玄齡等:《晉書》卷第四十九,第1370頁。《高僧傳》中言“帛祖釁起于管蕃,中散禍作于鐘會。二賢并以俊邁之氣,昧其圖身之慮”[注](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27頁。。《顏氏家訓》認為“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注](北朝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65頁。,將嵇康之死歸因于性烈、俊邁之氣和不世俗的精神追求;另一種歸結于政治原因:《石林詩話》載“康乃魏宗室女婿,審如此,雖不忤鐘會,亦安能免死邪!”[注](宋)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下,見(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34頁。認為嵇康之死是與曹魏聯姻的政治必然;魯迅也認為“嵇康的送命,并非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為他是曹家的女婿。”[注]魯迅:《再論“文人相輕”》,載《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第166頁。在嵇康之死問題上,當然不能否認與當世政治局勢和自身性格有很大關系,漢晉之際波譎云詭的政局對士人心態造成了巨大影響,“竹林七賢”“正始之音”等群體的出現,無一不是特殊時代的產物。但政治的原因是否最主要的?傳統考察多以時代背景下的政治考量為主,的確,中國古代文人與政治的關系極為密切,脫離開具體的政治歷史背景談文人命運和士人心態,基本上是無根游談,但這種歷史背景可以放到同時代很多人物身上,而嵇康不同于同時代任何一個文人,他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行為異常激進決絕。在血雨腥風的時局之下,即便不愿和光同塵,也完全可以選擇明哲保身,但他不顧一切地寫下《管蔡論》《與山巨源絕交書》這樣鋒芒畢露的文章,嵇康這種峻切執拗、獨立不懼的性格特征,與桓譚隔世呼應,是相铚文人琴家獨立不懼品格操守的直接顯現。嵇康瀟灑從容赴刑場,臨刑前索琴奏《廣陵散》的泰然風神,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生死,成為一種具有象征意義的文化符號,也使古琴超越了一般樂器的音質特色,具備了孤清高潔的品格特征。
從桓譚不懼死非讖到嵇康慷慨赴刑,體現出相铚文人琴家的凜然風骨。桓譚在中國文化史上首創“琴道”,稱“八音廣博,琴德最優”(《新論·琴道》)。嵇康深而化之,稱“眾器之中,琴德最優”(《琴賦》),成為古琴發展史上的不移之論,并由此奠定了古琴與眾不同的文化品格。后世論琴,多稱其不肯俯首娛人、不與眾和,這種品格的形成,正是從東漢桓譚時起,將琴的地位由形而下的“器”上升為形而上的“道”,并浸潤了不畏世俗、獨立自守的文人風骨,至嵇康將“目送歸鴻,手揮五弦”的瀟灑風神演繹為不畏生死血染刑場,泰然自若奏絕響,從而用氣血生命和凜然風骨澆鑄出古琴遺世獨立的特質。
不僅桓譚、嵇康,東晉時铚人戴逵,也用“摔琴”行為詮釋了相铚文人琴家不畏權貴的傲岸品格。戴逵,字安道,博學多才,《晉書》載其“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戴逵終生不仕,“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在太宰武陵王司馬晞因其善鼓琴派人征召時,當著使者的面將琴摔碎,并言“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注](唐)房玄齡等:《晉書》卷第九十四,第2457頁。相铚文人琴家獨立不懼的凜然風骨,在戴逵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其“摔琴”行為亦成為琴史上的佳話,更加深化了古琴孤傲自持、不媚世俗的高貴品格。時人謝玄、王珣等分別上疏贊其“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注](唐)房玄齡等:《晉書》卷第九十四,第2458頁。,可見戴逵守操篤志之風。《世說新語·雅量》篇載謝安親見戴逵,避而不談經國之大事,而與之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注]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73頁。戴逵在晉宰相見賓客先談政事,見伶人樂工才談技藝的禮俗之下,不僅毫無不悅之色,所論還愈發精妙,其不卑不亢之態,深為謝安所賞識。戴逵之子戴勃、戴颙亦善琴,父子三人均以隱逸顯名,被稱為 “一門隱遁,高聲振于晉、宋”[注](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年,第125頁。。
從桓譚、嵇康到戴逵,相铚文人琴家身上獨立不懼、凜然難犯的風骨一脈相承,都超越了時代局限性,成為文人琴家所特有的精神境界,也成為縱跨近四百年的一種文化現象。之所以這樣說,還因為從橫向上來看,桓譚的時代幾乎僅其一人不言讖;嵇康的時代,其兄嵇喜、其子嵇紹均依附司馬氏;戴逵之同胞兄弟戴逯[注]關于戴逵與戴祿孰長孰幼問題,《世說新語·棲逸篇》載戴逯為兄,《晉書》載戴逵為長。以武功官至大司農,二者的不同人生選擇被時人感嘆“何其太殊”。桓譚、嵇康和戴逵三人,都不同于同時代的同宗人選擇,在大是大非面前,都表現出強烈的斗爭性,寧折不彎、臨危不懼。并且,三人個性張揚的程度隨時代依次遞進,桓譚以言非讖,嵇康以文明志,戴逵則當面摔琴,都體現出“士”之骨和“士”之氣。究其原因,單以巧合論顯然難以說通。當三人共同的地域歸屬、共同的文人琴家身份被聯系到一起時,漢晉時期相铚文人琴家身上獨立不懼的品格,以及由此所鑄就的古琴卓爾不群、清高孤傲的文化屬性便橫見側出。
二、陳留文人琴家與古琴含蓄深沉的文化品格
朱長文《琴史》載“晉宋之間,縉紳猶多解音律,蓋承漢魏嵇蔡之余,風流未遠,故能度曲變聲,可施后世。”[注](宋)朱長文:《琴史》卷四,見《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八,第6頁。指出嵇康和蔡邕對于魏晉南北朝琴風的影響。如果說以桓譚為發端、以嵇康為代表的相铚文人琴家獨立不懼的風骨,奠定了古琴孤清高潔文化品格的話,那么,以蔡邕和與其有直接師承關系的阮瑀、阮籍為代表的陳留文人琴家隱忍沉潛的性格特征,則奠定了古琴的含蓄深沉之風。
蔡邕,陳留圉人(今河南省開封市)。善鼓琴,著有琴論著作《琴操》《彈琴賦》和琴曲《蔡氏五弄》等。蔡邕的一生時乖命蹇,憂怨隱忍卻難逃被殺的命運悲劇。《后漢書》載桓帝時宦官徐磺、左悺等當權,聞蔡邕善鼓琴,遂稟天子召蔡邕,“邕不得已,行到堰師,稱疾而歸”[注](南朝宋)范曄:《后漢書》卷六十下,第1980頁。,其《述行賦》序中也記敘“磺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救陳留太守發遣。余到堰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托所過,述而成賦。”可見,早年的蔡邕自視清流,自覺以士人身份與宦官劃清界限,不愿以琴藝覲見,故“心憤”,選擇稱病不前。董卓當權時,強辟蔡邕,以“力能族人”相威脅,蔡邕不得已應召,后受左中郎將職。董卓頗為器重蔡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宴,輒令邕鼓琴贊事”[注](南朝宋)范曄:《后漢書》卷六十下,第2006頁。,蔡邕亦出于濟世之志,常匡正補益董卓。但蔡邕對董卓“性剛而遂非”的行為多有不滿,欲遁逃不得,最終受董卓之死的牽連,被王允所殺。觀蔡邕一生,仕董卓時既不愿茍同又不敢開罪,選擇隱忍;被流放時愿“肝腦流離,白骨剖破”(蔡邕《戍邊上章》)以修史,又選擇隱忍;被王允治罪時,愿受“黥首刖足”之辱以“繼成漢史”,亦選擇隱忍。雖有曠世逸才,“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注](南朝宋)范曄:《后漢書》卷六十下,第1980頁。,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通才式大家,縱橫馳騁于文學、經學、音樂、書法、繪畫等各個領域,但終其一生,都在動亂的時局和當權者的強壓下隱忍沉潛,僅有的一次情感外露,便因“意氣”一嘆而“名澆身毀”。在亡命江海、浪跡吳會的流亡避禍期間,蔡邕創作了著名的琴曲《蔡氏五弄》——《游春》《淥水》《幽思》《坐愁》《秋思》,從曲名來看,大抵為蔡邕因“幽”“愁”“思”而作,朱長文《琴史》即言“伯喈所以寓其哀思者,蓋在此五曲,特假物以名之耳。”[注](宋)朱長文:《琴史》卷三,見《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八,第13頁。蔡邕的隱忍幽思,開創了古琴含蓄深沉的風格,并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袁桷曾指出“其客永嘉,郭楚望獨得之。復別為調曲,然大抵皆依蔡氏聲為之者”[注](元)袁桷:《清容居士集·琴述贈黃依然》卷第四十四,《四部叢刊》影印元刻本,第12頁。,可見蔡邕對郭楚望影響之深。郭楚望即南宋后期著名琴人郭沔,其代表作《瀟湘水云》從表面上看多用泛音營造出飄渺淡遠的意境,但實際上借九嶷山為“瀟湘云水所蔽”的景象,寄寓作者的憂愁悲憤之情,深刻詮釋了古琴含蓄深沉的品格。今人論琴曲風格多以“清微淡遠”一言以蔽之,實為對琴曲的謬解。殊不知,自東漢末蔡邕起,“含蓄深沉”成為古琴有別于箏、琵琶等彈撥樂器的特質。不惟琴曲,蔡邕還在其編撰的《琴操》中收錄了很多抒發“遭遇異時”的“操”曲,通過“琴曲題解”這一古琴曲所特有的形式,突出古琴深厚的文化內涵。顧炎武稱蔡邕為“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注](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011頁。,從蔡邕對漢末文學與藝術觀念的影響方面講頗有道理。古琴含蓄深沉之風,蓋由蔡邕始。
阮瑀,陳留尉氏人(今河南省開封市)。善解音,能鼓琴,《三國志》和《琴史》均載其少受學于蔡邕,被蔡邕譽為“奇才”。《魏書》載曹操聞其名,辟之不應,被逼逃入山中,曹操仿晉文公燒山求賢之舉,亦使人放火焚山,阮瑀沒有像介子推那樣抱樹而死,而是選擇隱忍出山,受司空軍謀祭酒一職。此后,他與陳琳一道為曹操起草章表書記,因才思敏捷,深為曹操所賞識,常從曹操出征,最負盛名的是馬上草書,曹操欲修改竟不能增損一字。在阮瑀身上,傳承了其師蔡邕隱忍的性格特征,面對當權者的強征,選擇龍蛇伸屈之道,從而能夠保全性命,并被曹操“數加厚賜”。
阮瑀之子阮籍,往往與嵇康一道被認為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斗士,但實際上他的生命體驗和生活態度均與嵇康有很大不同。嵇康獨立不懼,并為之付出生命代價。阮籍隱忍沉潛,在血腥殺戮中保全身家性命。司馬昭稱其“至慎”,《晉書》載其借酒避世:“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注](唐)房玄齡等:《晉書》卷第四十九,第1360頁。最有名的是在司馬氏欲與阮籍聯姻時,他大醉六十日,最終以“不得言而止”。在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時,作奏記推辭,蔣濟大怒,阮籍遂在鄉黨親屬勸說下,勉強出仕,不久“謝病歸”;后被辟為尚書郎,不久又“以病免”;在曹爽輔政召為參軍時,又“以疾辭”。四十歲之后,被迫出仕,但選擇醉酒不羈的消極合作方式,游走在權力核心邊緣,《晉書》載“鐘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注](唐)房玄齡等:《晉書》卷第四十九,第1360頁。阮籍之所以選擇醉酒避世,一方面為時局所迫,另一方面作為陳留文人琴家,蔡邕因對董卓“意氣”一嘆而獲罪的沉痛現實,對直接受學于蔡的阮氏父子造成了巨大影響。阮籍延續了蔡邕和阮瑀隱忍的處世方式,以終生“口不臧否人物”逃過司馬氏的殺戮。阮籍一生苦悶壓抑,以隱忍調和現實與理想的巨大反差,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注](唐)房玄齡等:《晉書》卷第四十九,第1361頁。其《詠懷詩》多處反映出這種痛苦和壓抑,如第三十一和第三十四首: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一日復一朝,一昏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飄淪。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時人。對酒不能言,凄愴懷酸辛。愿耕東皋陽,誰與守其真。愁苦在一時,高行傷微身。曲直何所為。龍蛇為我鄰。[注]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卷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503頁。
這兩首詩風格非常接近,上一首用“一日”“一夕”“一朝”“終身”等時間概念突出痛苦之久,用“火”與“冰”等意象突出痛苦之深,透露出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痛苦和焦慮。《一瓢詩話》評價:“阮步兵詠懷,寄愁天上,埋憂地下”[注](清)薛雪:《一瓢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121頁。。下一首同樣用“一日”“一朝”“一昏”“一晨”等時間概念來表痛苦之久,所不同之處是,上一首的愁苦,下一首給出了解脫的途徑,即耕種守真的隱逸。阮籍深刻意識到高潔行為傷身的道理,以“曲直”本無界限的哲學思考解決現實的矛盾。“龍蛇為我鄰”之“龍蛇”無論是用《左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非常之人的自由自在來理解,還是揚雄“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的龍蛇之道來理解,都體現出阮籍遁世沉潛的人生選擇。在阮籍醉于酒、隱于狂的一生中,內心其實時刻保持著清醒,他自稱“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明《神奇秘譜》載琴曲《酒狂》,為阮籍所作,從今人姚丙炎以《神奇秘譜》為底本打譜的《酒狂》來看,此曲不同于舒緩清微的琴曲曲風,多使用琴曲不常用的三拍表現醉酒形態,但促而不亂、醉而不顛,曲風含蓄深沉,傳達出內心抑郁不平之氣。
從東漢末蔡邕“幽”“愁”“思”的琴曲到阮籍的“狂”曲,體現出漢晉陳留文人琴家作為一個生命個體在動蕩時代的隱忍、矛盾與痛苦。對于阮籍“畏法而至”的被迫出仕,《魏氏春秋》指出“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注]《三國志》卷二十一注引《魏氏春秋》。見(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605頁。。陳寅恪也指出:“阮籍雖不及嵇康之始終不屈身于司馬氏,然所為不過‘祿仕’而已,依舊保持其放蕩不羈之行為,所以符合老莊自然之旨。”[注]陳寅恪:《金明館遺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86頁。阮籍最大的一次隱忍,是不得已作《為鄭沖勸晉王箋》,這也成為后人詬病他的一個污點。《石林詩話》稱“今《文選》載蔣濟‘勸進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亦何所不可為!籍著論鄙世俗之士,以為猶虱處乎裩中。籍委身于司馬氏,獨非裩中乎?”[注](宋)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下,見(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34頁。葉氏之語,雖不免偏激,但他指出阮籍之所以作勸進箋,是“忍至此,亦何所不可為”的結果,可謂中的之論。在漢晉陳留文人琴家身上,儒家的理想人格自始至終都存在,蔡邕對董卓之嘆和阮籍放浪形骸背后的慟哭,都是隱藏沉積于內心底層的儒家之志。后世論琴,多以含蓄深沉為重要特征之一,然其究竟肇始于何時?漢晉文人琴的興盛,使古琴不可避免地浸潤了琴家的個性特征,從而超越了普通樂器的“技”層面的特色,具備了古琴所特有的文化品格。因此,我們說“含蓄深沉”之風蓋由漢晉陳留蔡邕、阮瑀、阮籍等文人琴家始。
三、扶風文人琴家與古琴自然虛靜的文化品格
兩漢時期,關中地區一直是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關中文人一度占據東漢文壇。其中,扶風傅毅、梁鴻、馬融等還以彈琴或琴賦見長,扶風成為東漢文人琴家的又一重要分布區域。從傅毅的逸氣、梁鴻的尚隱到馬融的達生任性,扶風文人琴家的道家旨趣,奠定了古琴自然虛靜的文化品格。
傅毅,扶風茂陵人。少博學,作有《琴賦》,《文選·舞賦》注稱其“少逸氣,亦與班固為竇憲府司馬。早卒。”[注](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246頁。因傅毅早卒,史籍記載較少,但從《琴賦》殘篇可以看出傅毅超脫世俗的氣度。在從漢至晉的十余篇琴賦、琴贊中,傅毅《琴賦》最早開始突出“梧桐”意象:“歷嵩岑而將降,睹鴻梧于幽阻。高百仞而不枉,對修條以持處。蹈通涯而將圖,游茲梧之所宜。蓋雅琴之麗樸,乃升伐其孫枝。”梧桐作為俊逸高潔的象征,自先秦時已經開始,《詩經·大雅·卷阿》言“鳳凰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注](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179頁。可見,梧桐和鳳凰在士人心中具有超拔同類的獨特地位。《莊子·秋水》言南方之鳥鹓雛,從南海飛往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自此之后,使“鳳鳴梧桐成為高潔之士得其所在的同義語,梧桐也就成了擺脫世俗混濁之世的孤高不群之士的象征”[注][日]中西進、王曉平:《智水仁山——中日詩歌自然意象對談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164頁。。以梧桐作為琴材,《詩經》和枚乘《七發》都有記載,但以梧桐象征俊逸高潔,繼而象征琴的超凡脫俗特質,傅毅的《琴賦》首開其端。自此之后,梧桐成為琴賦描寫的重要內容,馬融、蔡邕之琴賦無一例外,至嵇康則更凸顯梧桐作為琴材之孤傲高貴,對梧桐的詠嘆成為士人對古琴品格和自身品格的維護。從這個意義上說,傅毅《琴賦》奠定了古琴超脫世俗的品格。
與傅毅同時代稍晚的扶風平陵人梁鴻,是兩漢隱士的突出代表。《后漢書》載其“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為章句”,與其妻孟光偕隱于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注](南朝宋)范曄:《后漢書》卷八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766頁。。東漢隱逸現象突出,隱士作為此時期社會重要階層為史家所重視,《后漢書》于《漢書》體例之外專設《逸民列傳》,錄梁鴻、野王二老、向長、逢萌、周黨、王霸、嚴光等近二十位“絕塵不反”之士。這類逸民多淡泊名利,安貧樂道,超然絕俗,生活如晉陸云《逸民賦》所言“相荒土以卜居,度山河而考室……揮天籟以興音,假樂之于神造,詠幽人于鳴琴”[注](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三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646頁。,彈琴成為隱士生活中與耕作同等重要的內容。這種生活旨趣在張衡的《歸田賦》也有描述:“彈五弦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自漢之后,“七弦”、“五音”成為反映隱居生活的固定意象。最有名的當屬陶淵明,他稱自己平生“欣以素牘,和以七弦”(《自祭文》),將彈琴視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多次在詩文中抒發彈琴之樂:“息交游閑業,臥起弄書琴”(《和郭主薄》)、“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歸去來兮辭》)、“衡門之下,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答龐參軍》)[注]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97、 60、161、22頁。,并且他還別出新裁地“蓄無弦琴一張”,體現出道家“大音希聲”的審美追求。余嘉錫曾精辟論斷:“蓋魏、晉人一切風氣,無不自后漢開之。”[注]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1頁。以梁鴻為代表的彈琴詠詩隱逸之風,不僅引領了當時的社會風尚,還經由馬融等漢晉之際思想變遷關鍵性人物的發揮[注]余英時稱馬融、孔融與何晏為漢晉之際思想變遷的關鍵性人物。見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0頁。,成為魏晉風度的前奏。
《后漢書》載馬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注](南朝宋)范曄:《后漢書》卷六十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972頁。。范曄為馬融立傳,不列在《儒林傳》中,也不附在其祖馬援之后,而是將其與蔡邕并傳,是頗有深意的。一方面與二者皆保性惜命有很大關系,蔡邕一生怯懦隱忍,馬融先是為避饑困應鄧騭召,后黨附梁冀,飛章奏李固;另一方面,與二者對漢末士風的影響不無關系。葛兆光謂“在二世紀中葉尤其是知識階層漸漸疏遠了那種以群體認同價值為標準的人格理想,轉向了追求個人精神的獨立與自由。”[注]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40頁。這一時期即馬融與蔡邕所生活的東漢后期,此時期士風開始轉向追求個體精神自由。馬融便是轉移天下風氣的此類人物之一。有學者指出:“論清談之淵源,融蓋為一啟蒙之人物,當宜深究者也。……漢末魏晉時代之史傳,稱當時人言論豐采之美者,以馬融傳為最早。……東漢史籍中,在馬融之前,未見有特標莊子達生任性之旨者,亦未見有以老、莊并舉者,以老、莊并舉,亦馬融開其端。……東京之末,節義漸衰而浮華漸盛,蓋始于馬融之倡老、莊也。”[注]賀昌群:《魏晉清談思想初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9-22頁。這一論斷認為始于馬融之倡老莊,將馬融作為“老莊并舉”的始作俑者,注意到馬融在漢晉士風轉變過程中的特殊作用,可謂深刻。相比較而言,魏晉任誕通脫之風更接近于馬融的“達生任性”。馬融激詭任誕的行為方式,把握住了漢晉之際歷史變革的關鍵,引領了時代風尚。
馬融最負盛名的是其在經學史上的地位,然而,他作為當世通儒,雖遍注儒家群經,卻不拘儒者之節,并率先突破經學藩籬,轉向老莊之學。侯外廬曾評價:“兩漢經學的結束的顯明的表現,就是經今古文學的合流。而時代思想的主流,則已經開始向著玄學方面潛行了。在這一點上,馬融恰是這一時代思潮轉捩的體現者。”[注]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28頁。葛兆光也曾評價馬融的去世,“象征了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注]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38頁。。《后漢書》載馬融“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后列女樂”[注](南朝宋)范曄:《后漢書》卷六十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972頁。,與正統儒者風范背道而馳,他所結交的也多是信奉黃老道家之士。竇章《移書勸葛龔》言:“過矯仲彥,論升仙之道;從蘇博文,談超世之高;適馬季常,講墳典之妙;所謂喬、松可也馳騖,何細疾之足患邪?”[注](清)嚴可均:《全后漢文》卷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557頁。將馬融與矯慎、蘇章、王子喬、赤松子等超脫世俗之士相提并論,可見其道家之旨趣。道家審美思想的核心是“自然”,老莊“致虛極、守靜篤”、“心齋”、“坐忘”的哲學思想要求審美主體達到虛靜自然的精神狀態,超越物象時空,馬融的“達生任性”即是老莊思想影響的產物。他在《琴賦》中塑造的“遨閑公子”形象,象征了入世與出世思想沖突之下的中國傳統文人的矛盾糾結。在這種糾結之下,才會有“前授生徒,后列女樂”的驚世駭俗之舉和由憤世嫉俗到毀棄禮法的率性行為,可以說,馬融身上最早體現出了中國古代具有典型意義的文人風范。
后世論琴常謂虛靜自然,究其根源,乃文人琴家躬身浸潤所致。馬融之達生,上承莊子“達生”理念,即摒除外欲、放空思想、心神寧寂,下啟魏晉通脫任誕之風。從傅毅、梁鴻到馬融,扶風文人琴家超脫現實、追求靜潔幽古的行為,使古琴與歷代遁世之士所向往的“塵外之趣”桴鼓相應,從而鑄就了古琴虛靜自然的文化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