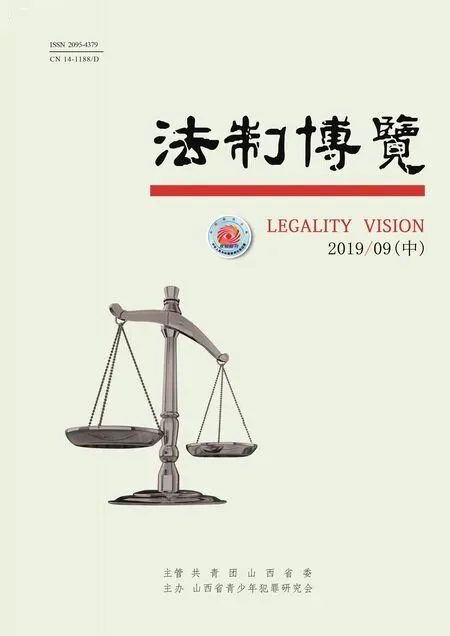大學生實習期間的法律身份研究
趙小溪
白銀礦冶職業技術學院,甘肅 白銀 730900
一直以來,大學生實習期間是否屬于勞動法真正意義上的勞動者倍受爭議,大學生實習期間的法律身份較為繁瑣,如何有效界定其法律身份也將直接影響到實習期間的大學生是否可受到勞動法的保護。受此影響,很多大學生在實習期間的權益受到侵害,尤其是在報酬方面體現較為明顯,報酬體系不合理,實習期間大學生所拿到的報酬與付出不成正比,甚至有一些實習大學生拿不到報酬。此外,實習協議簽訂環節也經常出現一些問題,尤其是對實習協議簽訂不夠仔細,協議上并沒有明確各方的權益,從而造成大學生的合法權益經常受到侵害。對此,本文在分析大學生實習期間法律身份的基礎上,提出以下大學生實習期間勞動法保護機制重構策略。
一、大學生實習期間的法律身份認定
大學生實習期間從法律的角度上剖析并不屬于勞動者,其身份仍是學生,如果是這樣的一個認定,從理論上大學生實習期間的身份與勞動者的身份是有沖突的,這就需要考慮大學生在實習期間能否真正意義上稱為勞動法上的勞動者,這也是當前對實習生與勞動者之間矛盾研究較多的話題[1]。在大學生實習期間法律身份認定方面,已經有很多學者對其展開研究,也都發表不同的見解,總結來說一種觀點認為大學生實習期間并不屬于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者,持這個觀點的學者認為關于勞動者只有在用人單位以及勞動者同時符合法律規定,才能納入到勞動法的保護范圍內,而大學生實習期間根據《意見》的第12條規定,在校生在利用業余時間勤工儉學的情況下,并不將其視為就業,而大學生實習期間則可歸入此類,并沒有與雇主建立勞動關系,可以不簽訂勞動合同。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講,實習期間的大學生還處在學校管理下,這種特殊的身份并不能納入社會保險范圍,從這幾方面因素的分析認為大學生實習期間并不能夠成為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者。
另一種觀點則正與前一種觀點相反,認為實習期間的大學生屬于勞動者,持這一觀點的很多學者認為實習期間的大學生雖然是在學校的管理下,但卻并不排除實習生所具有的勞動者身份。從憲法方面分析,對勞動者的認定是所有具備勞動權利能力以及勞動行為能力的人群均可稱為勞動者,因此說大學生實習期間可成為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者,在實習期間應受到勞動法的保護。
筆者認為,大學生實習期間雖然在學校的管理下,但這種身份與勞動者的身份并沒有沖突,雖然實習生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勞動者,但單純的從勞動者角度上分析,實習期間的大學生符合勞動者的實質,可稱為“勞動者”,在實習期間被納入到勞動法的保護范圍內,當然,在社會保險方面則與其他的正式員工有著一定的差別,實習期間的大學生是屬于勞動者范疇內的一種特殊群體[2]。另外,筆者認為,大學生在實習期間應明確其法律身份,與不同主體所形成的法律關系,可以說實習期間的大學生法律關系具有多重性,例如,實習大學生與用人單位之間所形成的法律關系,與學校之間形成的法律關系,這是以實習生為基礎所呈現的直觀法律關系,除此之外,還衍生出學校與用人單位之間的法律關系。尤其是學校與用人單位都具有獨立法人,并沒有直接的法律關系,而在大學生實習期間,學校與用人單位之間所簽訂的實習協議,則是對學生實習期間雙方的權利義務作出規定,在此過程中學校和用人單位屬于平等的合同關系,根據學校的委托,用人單位接收參與實習的實習生。
二、大學生實習期間勞動法保護機制重構
(一)重新界定勞動者
通過以上分析,對大學生實習期間是否真正屬于勞動法意義上的勞動者還依舊存有很大的爭議,這將直接影響到大學生實習期間的勞動保護。因此,應在勞動法上重新界定勞動者,并給予勞動者明確的定義[3]。在此過程中,應從用人單位方面考慮,對勞動者的定義應將是否能夠與用人單位之間建立勞動關系因素界定其是勞動者還是非勞動者。同時,還應考慮到勞動法的保護范圍,應不斷擴大勞動法上的勞動者范圍,尤其是針對實習的大學生,應通過合理的界定,實現對實習大學生的勞動保護,當然,這需要建立在符合勞動者實質的基礎上,才會將其納入到勞動法保護范圍。
(二)健全實習生報酬體系
在大量的實踐研究中發現,大學生在實習期間普遍存在薪酬水平偏低的現象,更有甚者大學生在實習期間沒有工資,喪失勞動報酬權益。從法律意義的角度上分析,雖然帶薪實習的工資標準偏低,但卻不能將實習期大學生報酬無限低,不合理的報酬對實習期大學生不公平[4]。不管從企業責任角度還是從公平的角度上分析,作為一個用人單位都應根據大學生實習期間的情況給予合理的報酬,如果這方面僅僅依靠用人單位自覺完成的話,效率會非常低,而且也很難保證實習期大學生獲取相應的勞動報酬。因此,筆者建議,針對實習期間的大學生報酬體系,應通過健全相關立法來實現,以保證實習期間大學生報酬體系建立的合理性。
(三)落實并簽訂實習協議
當今的大學生實習期間經常會因實習薪資待遇的問題發生爭議,從某個角度上分析,實習期間的大學生更像是勞動者中的弱勢群體,在實習期間得不到合法權益的保護,相關法律規定的不健全、不完善,很難為實習期間的大學生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因此,在新時期發展中,可通過落實并簽訂實習協議,為實習期間的大學生提供一定的保障,用法律保護勞動者中的弱勢群體。從實踐的角度上分析,實習期間的大學生在實習過程中會涉及到不同的法律主體并簽訂相關的實習協議,而在協議上卻并沒有明晰各方的權利義務以及在實習過程中可能發生爭執的解決方式等,會為大學生實習留下一定的隱患。一旦大學生在實習期間的權益受到侵害,因所簽署的實習協議相關法律規定不明確,很難將其作為實習生維權的法律依據,很難幫助大學生維護合法權益。因此,實習期間大學生在簽署實習協議時,應先考慮自身的法律身份,尤其是大學生本身實習期間處于弱勢群體,更應認真簽訂實習協議。同樣,用人單位也應嚴格按照相關法律規定認真簽訂實習協議,并在實習協議上明確大學生實習期間各方的權利義務以及可能出現爭議的情況,并針對可能發生的爭議提出相關的約定,通過法律保護大學生實習期間的身份權益。
三、總結
綜上所述,在新時期發展中,大學生數量也越來越多,大學生在剛踏入到社會時需要進行一定的實習期,而在實習期間大學生可以說是勞動者中的弱勢群體,自身的合法權益經常受到侵害,卻因實習期間實習協議以及相關法律的不健全而無法進行維權。另外,大學生實習期間法律身份也依舊存在很大的爭議,更有一些用人單位以此做文章,并沒有給實習期間大學生合理的報酬,這對實習生很不公平。在本文的研究中,主要針對大學生實習期間法律身份展開研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幾方面大學生實習期間勞動法保護機制重構策略,以其為剛踏入實習期間的大學生提供更全面的法律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