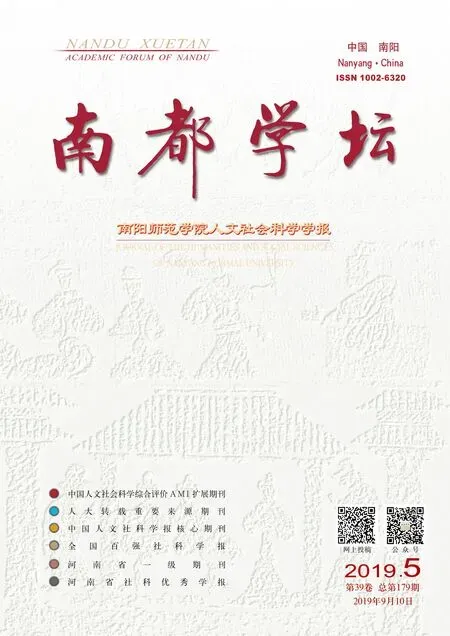新貿易壁壘下外資企業退出我國市場的問題研究
呂靖燁, 胡美艷, 文啟湘
(1、2.西安科技大學 a.管理學院; b.能源經濟與管理研究中心,陜西 西安 710054; 3.西安交通大學 經濟與金融學院,陜西 西安 710049)
近年來,隨著跨國生產經營活動不斷發展,外資企業進入中國規模不斷擴大。然而,隨著歐美發達國家為了振興實體經濟提出的“再工業化”戰略,以及2017年席卷全球的稅收改革,美國特朗普政府和英國特里莎·梅政府紛紛宣布新的稅改政策,法、德、日、韓等發達國家與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國家開始加入這股浪潮中,加之全球貿易戰的升級,這些關稅和非關稅措施所形成的新的貿易壁壘,必將加劇我國國際資本外流的壓力,使得外企退出的活動越來越頻繁,對我國的宏觀經濟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眾多學者研究了外企撤資以及稅制改革等政策對我國經濟造成的影響。李偉(2015)[1]、劉洪儒(2015)[2]、尚運生(2017)[3]等分別從外商撤資的模式選擇,實物期權角度以及勞動力成本、稅收優惠等方面研究了在華外企撤資的現象,提出了對外企撤資的問題應理性應對;李玉梅(2016)[4]、劉振林(2016)[5]、趙平(2017)[6]等從外企撤資的動因與影響機理方面進行了分析,提出應加快產業升級的推進,在提升價值鏈水平的同時,與“一帶一路”相配合,積極引導外資的有序轉移;傅鈞文(2015)等從“再工業化”的視角,對在華日資撤資的制造業回流現象作了分析,以期找出其背后更本質的原因[7];李文浩(2017)等從陜西省裝備制造業的角度出發,研究應對歐美“再工業化”的對策,提出了培育發展創新型先進制造業[8];賈康(2018)[9]、李東松(2018)[10]、吳瀚(2018)[11]、邱慧芳(2018)[12]等從減稅政策入手,分析其對我國經濟以及部分省區的影響,提出相關建議;孫繼山(2017)[13]、柯建飛(2017)[14]等對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貿易戰進行分析,提出在當前的大環境下結合中國實際,在提升自身綜合實力的基礎上,不斷完善現有的制度積極應對。
國內外關于外企退出的相關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當前全球宏觀形勢發生了轉變,再工業化、全球減稅、貿易壁壘等問題越來越突出,如果能夠結合這幾個方面,在新的背景下,深入研究外國企業退出我國的問題,對于提升我國宏觀經濟穩定性,解決國內經濟發展動力等問題,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目前,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正是向高質量發展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15]在這一階段,如何應對大環境下外資企業退出我國市場所帶來的沖擊,是我國急需解決的問題。因此,研究外資企業退出我國市場的原因以及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影響,并提出相關的應對策略具有重要意義。
一、新貿易壁壘下外資企業退出我國市場的動因
最近幾年,隨著全球范圍內減稅風潮的掀起,新貿易壁壘的影響愈演愈烈,眾多跨國公司在中國不同程度的關店、撤離。2016年3月,諾基亞通信在上海金橋的分公司將工廠轉讓給上海捷普,計劃關廠進行裁員;2016年5月,富士康開始在印度建起規模相當可觀的工廠,慢慢撤離中國大陸;同月,飛利浦燈飾制造——飛利浦全資子公司遣散員工,停止生產,而后在荷蘭證交所上市,一躍成為全球獨立照明的最大生產商;也是在這一個月內,珠海及成通訊宣布關閉,退出中國大陸;2017年1月,甲骨文北京研發團隊整合各研發中心資源,在中國裁員,部分工作崗位調整到美國和印度。這些企業共同的特點是在進行戰略轉移,退出中國市場之后,選擇其他國家作為新的經營地點。
另外,2016年8月,艾迪斯電子科技——位于深圳的三星主要供應商停產;9月初,中國人壽購入花旗銀行持有的廣發銀行的全部股份,以197億元成交;11月初,瑪莎百貨將在中國的所有店鋪關閉,全球范圍內總共關閉53家門店,裁員2100余人;2017年1月,希捷——全球最大硬盤制造商,關閉蘇州工廠;同月,麥當勞在中國的餐廳經營權被中信和凱雷購入,成交價為161億港元;3月,FPGA原廠美高森美(Microsemi)基于集團公司戰略發展方向調整的原因,關閉上海工廠……這些外資企業的退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歐美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戰略、全球減稅風潮以及貿易戰升級的影響。而新貿易壁壘下外資企業退出我國市場的動因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一)外資企業水土不服而難以適應東道國市場
歐美等發達國家紛紛施行減稅政策和貿易保護政策希望吸引資本回流,而此時中國的經濟發展動力強勁,成為全球的一個亮點。當然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對外資企業仍然具有無窮的誘惑力,很多外國企業因為難以適應中國市場和消費文化,在經營過程中忽視地區消費差異性;同時,一些外國企業不適應東道國的法律法規,盲目地進入中國市場卻沒有明朗的戰略和管理措施,在全球范圍內的減稅浪潮和新貿易壁壘下,最終因“水土不服”而黯然退出。
(二)外資企業發展戰略轉移而形成的企業合理流動
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國家開始嘗試改革其宏觀政策,從“再工業化”戰略的實施,推動出口和制造業的增長,使得經濟轉入可持續增長模式,吸引國家實體經濟回歸本土,到全球減稅狂潮的帷幕拉開,再到各國最近愈演愈烈的貿易戰升級,新的貿易壁壘不斷限制跨國企業的經營,這就要求一些外企調整戰略,尋求新的發展途徑。
另一方面,在跨國企業的發展歷程上曾一度掀起過多元化經營的浪潮,企業并購的現象屢見不鮮,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企業的核心競爭優勢降低,以多元化經營實現企業資源的最優配置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多元化折價效應日益顯現,所以,許多跨國公司為了保持自身的核心競爭優勢,開始收縮戰線、調整業務板塊,具體表現為對部分國家的部分行業進行業務剝離并撤資。外資企業在我國的部分業務撤離屬于企業戰略管理中歸核戰略,當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各種關稅和非關稅政策所形成的新貿易壁壘,無論如何,這種撤離行為都是企業發展和戰略布局的合理調整。
(三)外資企業受成本驅動而企業轉移陣地
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其自身龐大的市場規模、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和外資企業稅收優惠,吸引了一大批外資企業。然而隨著全球經濟摩擦的不斷加劇,歐美等發達國家紛紛宣布施行減稅政策,新的貿易壁壘正在逐步形成,我國勞動力紅利漸漸消失,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成本逐年上升,有些外資企業甚至是我國的企業,都有向東南亞地區轉移以尋求更低的人工成本的趨勢。
再加上隨著環保觀念逐漸深入人心,我國的環境保護標準不斷提升,原有的外資企業一味掠取利潤的手段顯然已經不再適用,在內外因素的共同影響下最終不得不離開中國市場。
二、新貿易壁壘下外資企業退出我國市場的形式
隨著我國經濟向高質量階段發展,西方國家的稅收政策明顯朝著企業利好的方向轉變,外資企業在我國的發展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影響,特別是那些產能過剩的跨國企業,正在面臨著更大的威脅。面對這樣的市場形勢,有些外資企業不愿意放棄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積極尋求應對策略;而另外一些外企則選擇退出我國市場。新貿易壁壘下外資企業的退出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完全退出、兼并重組、轉移退出。
(一)新貿易壁壘下完全退出我國市場
新貿易壁壘下的完全退出也可以稱為無條件式退出。外資企業完全退出市場的典型代表是珠海及成通訊。早在2014年末,珠海及成通訊的昆山工廠關閉,開始轉移到珠海的工廠,然而隨著成本的不斷增長和訂單的減少,整個企業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最后公司決定宣告倒閉,無條件全面退出中國市場。
選擇完全退出的外資企業歸根究底還是因為在東道主國“水土不服”,許多外國企業不考慮地區消費差異,盲目進入中國市場,與中國愈來愈強大的本土領軍企業展開競爭,最終被斬于馬下,不得不退出中國市場,當然也少不了新貿易壁壘的推動。
(二)戰略規劃變遷后的兼并重組
新貿易壁壘下的兼并重組也可以稱為創造條件式退出。外資企業進行兼并重組退出中國市場的典型代表是希捷集團。2017年1月12日,知名硬盤制造商希捷集團率先關閉了在蘇州的工廠,進行全球范圍內的業務重組,進一步增加在全球僅有的兩家生產基地之一——無錫工廠的投資,集中優化業務板塊來滿足市場的需求。
選擇這種退出方式的外資企業并未完全退出中國市場,有很大部分的外資企業認為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對于其在全球的發展戰略相當重要,但是如果不能隨時調整步調以適應中國的市場環境,最終將會被激烈的市場競爭所淘汰。所以,一些外資企業對產品結構進行優化,將低端產品升級,研發轉變為高端產品,積極適應當前的市場環境。
(三)雁型模式下的轉移退出
新貿易壁壘下的轉移退出也可以稱為雁型模式退出。外資企業轉移退出的典型代表是飛利浦照明。2016年5月31日起,飛利浦全資子公司,位于深圳的燈飾制造公司開始將員工遣散,停止生產與運營。而后在荷蘭證交所上市,一躍成了全球最大的獨立照明生產商,成功實現戰略轉型。
選擇轉移退出的外資企業絕大多數都是勞動密集型的低端制造業,主要搬遷到東南亞等地,純粹是為了追求更低的人工成本,獲取最大的利潤。在當前全球都在減稅吸引資本的大環境下,我國施行原有的稅收政策和更加嚴格的勞動標準,無疑會壓縮外資企業的利潤空間。
三、新貿易壁壘下外資企業退出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外資企業在我國進行跨國生產經營活動,一方面,給中國提供了一定的就業崗位,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先進的西方管理理念,某種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從側面反映了我國投資環境、市場制度的不斷優化。但是,這些都是以我國付出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向外資企業提供眾多的稅收優惠政策甚至是犧牲我國生態環境為代價的,而外資企業退出我國市場對中國的就業形勢、整個宏觀經濟市場、創新等方面都會造成一定影響。所以,新貿易壁壘下外企退出給我國帶來的效應既有消極的一面,也有積極的一面。
(一)新貿易壁壘下外資退出的消極效應
新貿易壁壘下外資企業退出帶來的消極效應從短期來看,有以下幾個方面。
1.外企退出導致我國就業壓力增加
在全球貿易戰升級的當前,外資企業的退出以及我國資本的外流會給目前的就業形勢帶來一定的影響,就業市場上機會大量減少。外資企業進入我國市場的初衷是通過廉價勞動力和土地等生產要素以及我國給予的稅收優惠政策來掠奪利潤,有相當比例的外資企業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當外企退出我國市場時,同時也會波及下游相關產業鏈企業,造成大量受雇于相關企業的員工失業,最終導致我國就業壓力增加。
2.外企退出對我國經濟造成了某些不利影響
一方面,外資企業的存在給我國稅收做了很大的貢獻,外資企業的退出在一定程度上會減少我國的稅收收入。另一方面,外資企業的退出意味著資本的流出加劇,同時,在歐美發達國家引導實體經濟回歸本土的“再工業化”戰略,各國施行的減稅計劃以及最近貿易戰升級等各種關稅和非關稅政策形成的新貿易壁壘的影響下,我國經濟或多或少都會受到波及,不利于大環境下我國應對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速下行壓力。
3.外企退出掣肘我國技術創新升級
創新是一個國家不斷發展的動力源泉,也是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核心支柱。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明確了創新在引領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標志著創新驅動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在新時代中國發展的行程上,將發揮越來越顯著的戰略支撐作用。我國正在努力將“中國制造”逐漸發展為“中國創造”,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目前我國的創新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依然存在。發達國家對我國技術輸入管制一貫嚴厲,壁壘森嚴,加上全球減稅風潮和新貿易壁壘下外資企業核心技術的退出,會一定程度上制約我國短期內技術創新水平提升。
(二)新貿易壁壘下外資退出的積極效應
長遠來看,新貿易壁壘下外資企業的退出給我國帶來的積極效應有以下幾個方面。
1.有利于我國發展高水平就業
現階段,大量低端制造業帶來的是低水平的就業,密集型企業中大多數的勞動者只是通過機械、枯燥的工作來獲取生存資本,這樣的就業同時也是低質量的就業。在新貿易壁壘下,當低端制造業由于成本原因轉移出去之后,可以集中發展中高端產業,在實現產業的轉型升級的長期過程中可以提升我國的就業水平,完成從低水平向高水平就業的轉變過程。
2.有利于內生性經濟的發展
過去的一些年里,我國持續利用大規模的外資發展經濟從而推動本土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但新貿易壁壘下外資企業的退出不可避免地對我國的宏觀經濟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在當前現代化經濟體系中,內生力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推動內生性經濟的發展能夠使得我國的綜合國力不斷提升,所以當前外資企業的退出有利于倒逼我國長期內生性經濟的發展。
3.有利于長期自主創新式發展
“堅定轉型升級、堅持創新驅動,以新的發展理念引領新的發展之路。始終保持轉型發展的高度自覺和戰略定力,堅決走好產業優、質量高、效益好、可持續的發展新路。”[16]黨的十九大以來,中國制造被重新論述。過去,中國制造更多的是跟在國外的先進技術后面,是低質低價的代名詞,而當前在國家創新政策的引領下,我國在一些領域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一大批擁有高端核心技術的產品開始涌現,從低附加值的中國制造正在逐漸向高附加值的中國創造發生轉變,新貿易壁壘下外資企業的退出有利于我國長期自主創新的發展。
四、新貿易壁壘下我國應對外資企業退出的策略
(一)加快產業升級,提高就業水平
低成本吸引進來的終歸是只依賴低成本獲取利潤的產業,低成本產業帶來的也是低水平的就業。在新貿易壁壘的推動下,一些勞動密集型外資企業的退出導致部分人員的失業。面對這一問題,我國應該以市場為導向,注重資源配置和產業結構調整,注重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應,加快實現產業升級,將低質量低水平的就業提升為高水平的就業。
(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在過去的一些年里,中國經濟一直保持著中高速增長,GDP增長速度與經濟發展取得的成績讓世界矚目。但是與此同時,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使得各方面的問題層出不窮,不可再生的資源與污染日益嚴重的環境要求我國迫切重視經濟發展的方式,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17]。在當前面臨的新貿易壁壘下,加大第三產業在經濟社會中所占的比例,變外向式經濟為內涵式增長和發展,把主要依靠資源等要素投入推動經濟增長和規模擴張的粗放型發展方式,轉變為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推動產業結構加快由中低端向中高端邁進,加快形成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動源。
(三)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在當今知識經濟飛速發展的時代,創新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成為至關重要的支撐點。不論是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水平抑或是綜合國力的競爭,歸根究底還是創新力的競爭。外企在中國的投資的原因是逐利,新貿易壁壘驅動的外企的進入與退出并未給我國留下核心技術,我國的經濟要發展還要依賴于自身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在當前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的新階段,新貿易壁壘下,創新就是第一生產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成為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路徑。
學者們對外資企業是否退出中國、退出的規模有多大依然是有爭議的。對于這一現象,我們也要正確對待,企業進入和退出行為是企業發展中的自身問題,雖然存在個別企業出于某些政治利益,退出市場,但是大多數企業的退出行為都是合理的市場行為。跨國公司選擇在哪里投資經營,如何選擇合作伙伴,都會根據企業利益、發展戰略和市場機會作出商業決策,不能因為部分企業退出就過度夸大這種退出行為的不利影響。
事實表明,外資企業退出中國,特別是那些低端制造業的轉移退出,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轉型階段不可避免的現象。隨著我國經濟發展不斷升級,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高端外資企業進入中國。世界銀行《2019年營商環境報告》顯示出中國營商環境排名大幅提升了32位。2018年中國新設外資企業超過6萬家,增長69.8%。即使在中美貿易戰不斷升級的背景下,全球知名的埃克森美孚、特斯拉、巴斯夫、寶馬等企業加大了來華投資。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0)發布的《2018年日本企業海外業務調整報告》指出日本企業對外出口、投資、跨境電商戰略中,中國市場均排名第一。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宣布,中國將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開放舉措,促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這必將為世界各國企業在中國投資提供新機遇,也必將為維護自由貿易體制,推動世界貿易增長作出新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