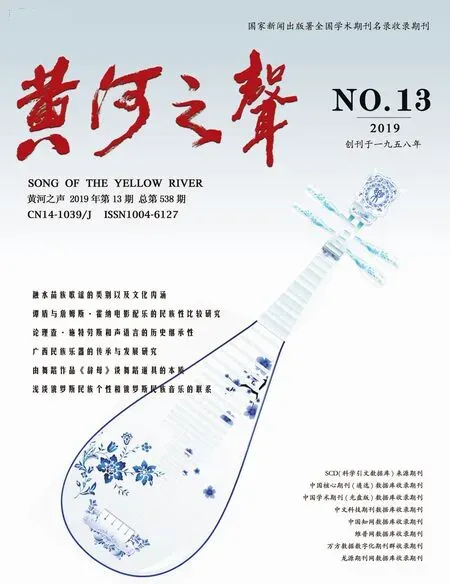文化視域下的內蒙古二人臺的音樂田野調查之探微
高志民
(河南大學音樂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二人臺,俗稱“二人班”,又叫“雙玩意兒”,建國前期才統稱為二人臺,其演出形式經發展后采用一丑一旦二人演唱的形式,故稱“二人臺”,產生的年代至今沒有非常明確的考究,眾說不一。清朝光緒年間,由于連年大旱,山西河曲、保德、偏關以及和陜西府谷周圍一帶的農民,過上了食不果腹的生活,為求生存到口外落腳謀生。隨著內蒙古地區的經濟文化水平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人通過西口,即殺虎口,走到內蒙古中西部的呼和浩特市、包頭市、烏蘭察布市、巴彥淖爾市以及鄂爾多斯一帶落腳定居。據統計,民國元年,內蒙古有240.32萬人,民國三十八年608.10萬人。至21世紀初,內蒙古自治區有2375萬人,其中蒙古族386萬,漢族1833萬人,余為其他民族人口[1]。發展至清朝末年,內蒙古中西部的土默川一帶,在經歷了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后,促進了蒙漢文化的大交融,生活方式、興趣愛好等在相互影響下潛移默化的發生著改變。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地域的文化背景下,二人臺的形成及發展也有了明確的方向。
內蒙古二人臺作為內蒙古的地方歌舞小戲,經過長期發展,逐漸形成不同的藝術風格的內蒙古二人臺,以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為界,分為東路和西路二人臺。從地域和時間上劃分的話,西路二人臺是最早出現的二人臺,產生于人口遷移后的蒙漢文化交融時期,流行于內蒙古中西部的呼和浩特、包頭以及晉陜冀寧部分地區,其中以包頭市的薩拉齊縣流行范圍最廣。東路二人臺則出現時間較晚,是由西路二人臺逐漸發展到烏蘭察布市、晉北、冀北,并以烏蘭察布區域為中心形成東路二人臺。東、西路二人臺經過長期發展,覆蓋蒙、晉、冀、陜、寧五省區90多個旗縣,群眾基礎深厚,流行范圍較為深遠。
田野調查源于最早的人類學研究方法,也是公認的科研基本方法,其明顯的特點就是“直觀性”,它是獲得原始資料的重要步驟。音樂田野調查無疑也是音樂研究是非常關鍵的方法,是我們獲得研究對象資料的重要途徑。內蒙古二人臺作為地方戲,經國務院批準于2006年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自然有大批學者對二人臺音樂進行田野調查,并得出豐碩的研究內容和結果。如邢野在《有關內蒙古地方戲二人臺的田野調查》一文中就寫到,他三次到實地考察,歷時45天,將二人臺的起因、發展,歷史背景做了詳細的研究調查,總結了寶貴的二人臺資料。筆者出生在內蒙古,祖籍是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商都縣,正是如今二人臺音樂發展的活躍之地,因此以區域視角及歷史背景對二人臺音樂藝術特征做如下總結。
前文中曾提到,在經歷“走西口”等大規模的人口遷移,蒙漢文化交流甚密,二人臺音樂就是在這樣厚重的歷史淵源下產生的。從藝術形態方面來看,最顯著特征在于其通俗性,二人臺的藝術形態由“打坐腔”到“打玩藝兒”再到“曲牌體小戲”,演唱語言主要以地方方言為主,內蒙古中西部、冀北、晉北、陜北等地區方言接近,因此二人臺主要活躍于此。二人臺藝人用地方方言演唱當地的故事,自然最能表達人們的生活情操,深受人們喜愛,這就像藝術歌曲必須要用詩歌作為歌詞是一樣的。內蒙古二人臺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第五代傳承人郭威道出,當時流行了一句順口溜:“不吃油糕喝稀粥,也要看班玉蓮的走西口”。
二人臺在形成過程中,有很多的蒙古族藝人參與其中,蒙漢民歌、絲弦坐腔便是二人臺形成的基礎。劇考究,二人臺音樂是由民歌發展而來的,因此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伴奏樂器由初期的四胡、隨后又加入笛子、梆子、揚琴等,音樂風格也呈現出有遼闊、悠揚、樸實、清新的特點,反映出樂觀、豪放的民族性格。內蒙古二人臺發展至今,傳統劇目約有120個,如“硬碼戲”《走西口》、《探病》,“帶鞭戲”《掛紅燈》、《打金錢》、《拜大年》。
當今社會,在文化藝術的高速發展下,很多的藝術類別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支持,二人臺能發展至今,就證明了具有一定的歷史價值。雖因其藝術性與地域性在建國后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在如今不斷創新、傳播甚遠的時代,二人臺在發展與傳承上遇到了瓶頸。
首先,發展動力不足,也就是文化傳承的問題,應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培養下去發掘、培養人才,保證傳承人的動力。其次,缺乏創新意識,其他藝術形式能長足發展,一定是在不斷的創新突破,否則我們傳承上百年的二人臺,最終都會成為活化石,要回到正確發展軌跡上,這包括要對二人臺的劇本、演唱語言、內容、演出形式上要進行改革創新、與時俱進。再次,也希望政府文化單位給予足夠的重視與支持,讓我們熱愛的內蒙古二人臺再次發揮其價值功能,得到長足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