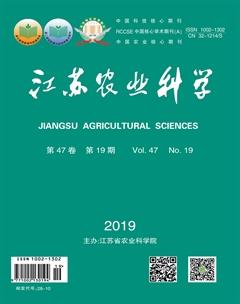低碳視角下烏魯木齊市土地利用結構優化研究
孟梅 崔雪瑩 王志強



摘要:以新疆烏魯木齊市為研究區域,基于碳減排目標建立多目標規劃模型,以土地利用經濟效益、土地利用碳排放和土地利用生態效益為目標函數,得到2020年烏魯木齊市土地利用結構優化方案,并將優化方案與規劃方案進行對比分析。研究結果,優化后的的耕地、園地、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面積有所增加,建設用地面積有所減少;與規劃方案相比,優化方案中碳排放量減少184.57萬t,土地利用生態效益增加6.93億元,雖然土地利用經濟效益較規劃方案減少了,但符合當前中高速增長的經濟發展規律。研究結果表明,以土地利用經濟效益最大化、碳排放最小化和生態效益最大化作為目標的土地利用結構優化方案能在保證經濟平穩增長的同時,有效地實現碳減排,并且有助于土地利用生態效益的提高,對今后烏魯木齊市的土地利用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土地利用結構;碳排放;多目標規劃模型;烏魯木齊市
中圖分類號:F301.2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19)19-0261-04
收稿日期:2018-08-06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編號:71663052)。
作者簡介:孟 梅(1984—),女,新疆烏魯木齊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土地資源管理、公共管理與公共政策。E-mail:785161662@qq.com。
通信作者:崔雪瑩,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土地資源管理。E-mail:495986700@qq.com。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的第四次報告中以堅定的口吻確認了全球變暖與人類活動之間的關系。報告稱人類活動引起大氣中CO2、CH4的濃度增加,導致了全球平均氣溫的升高[1]。溫室效應的加劇,引發了諸多環境問題。因此,有計劃地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是各國解決氣候變暖問題的共同選擇。我國作為溫室氣體排放大國,“低碳發展”正成為制定經濟和能源發展戰略時要考慮的核心因素。土地是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空間載體,土地兼具了碳匯及碳源的雙重作用。但事實上大多數土地利用都導致了碳排放的增加,如建設用地擴張、林地減少、草地開墾等。土地作為陸地生態系統碳循環的自然載體和人類活動碳排放的空間載體,土地利用的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碳排放的結構,隨著土地利用結構的調整,碳排放效應不斷發生改變。因此,在低碳導向下,如何通過調整土地利用結構,優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土地資源,使在降低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同時,實現土地利用整體效益最優化的目標,成為土地利用調控的新課題。
近年來,眾多學者開展了土地利用與碳排放間的相關研究,尤其是如何通過優化調整土地利用結構從而降低碳排放,實現土地利用整體效益最優化的目標,成為土地利用調控的新課題。李國敏提出要將城市、經濟和環境聯系成一個有機整體,從減排和增匯2個方面著手,對土地利用結構優化形成城市土地的低碳利用[2];趙榮欽等對城市土地利用的碳排放效應進行了研究,提出低碳高密度緊湊型的城市土地低碳利用格局[3];毋曉蕾等針對河南省淅川縣實際情況,利用以經濟效益最大化和土地利用總碳排放量最小化為雙重目標的低碳型土地利用結構優化模型獲得優化方案[4]。然而,目前研究層面多以國家或省級為主,對于市域層面的研究還相對較少,尤其對于西北地區,目前還沒有涉及低碳目標下的土地利用結構優化研究。基于此,筆者選取西北部新疆烏魯木齊市作為研究區域,嘗試從經濟效益最大化、碳排放最小化和生態效益最大化3個方面出發,構建多目標線性規劃模型,探尋土地利用結構優化新途徑。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與數據來源
烏魯木齊市是新疆的政治、經濟、文化、信息、科技中心,是我國向西開放的重要門戶,同時也是“一帶一路”絲綢之路核心區。烏魯木齊深處亞歐大陸腹地,遠離海洋,屬于大陸干旱氣候區,降水少,溫差大,年平均降水量為294 mm,年均氣溫為7.3 ℃。烏魯木齊市三面環山,北部平原開闊,平均海拔為800 m。烏魯木齊市現轄七區一縣,面積為1.39萬km2,常住人口351.96萬人。烏魯木齊市有著非常豐富的礦產資源,故被稱為“煤海上的城市”。近年來,隨著國家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中央出臺了一系列針對新疆開發建設的優惠政策,這些政策有力地支持了烏魯木齊的加快發展。2015年,烏魯木齊市實現生產總值(GDP)2 631.64億元,同比增長了 10.5%,人均地區生產總值74 340元,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014年,烏魯木齊市成功申報成為第三批國家節能減排財政政策綜合示范城市,國家給予節能減排典型示范項目大力支持,這對烏魯木齊市既是機遇也是挑戰,烏魯木齊市必須更加重視節能減排建設,優化能源供需結構,實現生態保護與經濟建設的同步發展。
本研究構建的多目標線性規劃模型中,所用土地利用結構數據主要來源于《烏魯木齊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2006—2020年)》《新疆國土資源綜合統計資料冊》和烏魯木齊市土地利用變更調查資料;參考的能源消耗數據和社會經濟數據主要來源于烏魯木齊市歷年統計年鑒和IPCC提供的數據。
1.2 研究方法
在低碳導向下的土地利用結構優化研究中,目標函數需要綜合考慮碳排放、生態和經濟等多方面影響,簡單的線性規劃模型難以處理多個目標函數間的相互沖突,而多目標線性規劃模型具有較強地處理多個目標函數問題的能力且具有較強的適用性、靈活性,能夠彌補簡單線性規劃模型的不足。因此,針對烏魯木齊市的土地利用結構特點,采用多目標線性規劃模型對土地利用結構進行低碳優化。其基本表達式如下:
opti:max(min)f(x)=C·X;
s.t.:A·X≤B;
X>0。
式中:f(x)為模型目標函數,根據優化目的,取最大或最小解作為最優量;C=[c1,c2,…,cm]為系數;X=[x1,x2,…,xm]T為各種類型土地面積;A為約束系數矩陣;B=[b1,b2,…,bn]T為約束常數值。
2 土地利用結構低碳優化模型構建
2.1 模型變量設置
模型變量的設置對于優化模型的構建來說非常重要,針對不同優化目標和對象,設置的變量都是不同的。本研究中變量的選取不僅要以《全國土地分類》為參考,還應遵循烏魯木齊市土地利用規劃的規定和未來的發展趨向。此外,還要考慮到烏魯木齊市土地利用的現實情況和相關數據的可獲取性。綜合以上要求,共設置7個變量,分別為耕地(x1)、園地(x2)、林地(x3)、草地(x4)、建設用地(x5)、水域(x6)、未利用地(x7)。
2.2 目標函數
土地利用的過程不僅會產生經濟效益,還會影響生態安全和環境保護,因此,土地利用結構優化要兼顧土地利用的各方面效益。本研究以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碳排放最小化和生態效益最大化作為調整土地利用構成的目標函數。
2.2.1 土地利用經濟效益目標
本研究中各土地利用經濟效益用各類型的經濟產出率乘以用地面積來計算。其中,耕地和園地產值對應農業產值,根據烏魯木齊市歷年數據,相應地可以計算出2001—2015年耕地和園地的經濟產出率,用GM(1,1)模型測得2020年耕地和園地的經濟總產出率近 49 084元/hm2;林地產值對應林業產值,測得2020年林地的經濟產出率近5 425元/hm2;草地產值對應畜牧業產值,預測得到2020年草地的經濟產出率為4 545元/hm2;建設用地產值則對應第二、三產業產值,預測得到2020年建設用地的經濟產出率近2 893 836元/hm2。其中,由于水域和未利用地基本沒有經濟產出,設定其他土地系數為1。根據相應的經濟產出率,確定土地利用經濟效益目標函數為
F1(x)=49 084(x1+x2)+5 425x3+4 545x4+2 893 836x5+x6+x7→max。
2.2.2 土地利用碳排放目標
土地利用碳排放目標是調整土地利用結構使烏魯木齊市凈碳排放量達到最小化。由于耕地、園地、林地、草地、水域的特性,在一段時期內,碳排放和碳吸收率的變化較小,因此設定研究期內其數值是定值,直接使用各類型的碳排放和碳吸收系數。其中,耕地的碳排放系數參考Cai的研究,取值為0.504[5];碳吸收系數參考何勇的研究,取值-0.007[6]。關于園地的碳吸收系數的研究較少,借鑒IPCC(2015)的園地碳吸收系數取值為-0.21[7]。林地的碳吸收系數參考吳慶標等的研究,其中新疆1990—2000年的森林固碳量為2.19~4.84 Tg C/年,同一時間新疆森林的面積約為67.6×104 hm2,則林地碳吸收系數為 -0.520[8]。基于任繼周等的研究可知,新疆草地碳匯量為 24.1 Tg C/年,而同一時間草地面積為84.26×106 hm2,則新疆草地碳排放系數為-0.029[9]。參考段曉男等的研究,新疆水域固碳量約為596.13 Tg C/年,同期水域面積為1.97×106 hm2,可得新疆水域碳排放系數為-0.303[10]。
土地利用過程中各種化石能源的消耗量是動態變化的,則建設用地平均碳排放也一定會發生變化。因此,需要進行烏魯木齊市2020年的建設用地地均碳排放預測。根據2001—2015年的變化情況,采用GM(1,1)模型最終得到烏魯木齊市2020年建設用地的地均碳排放預測值為 206.06 t/hm2。最終確定碳排放目標函數為
F2(x)=0.497x1-0.21x2-0.250x3-0.029x4+206.06x5-0.303x6→min。
2.2.3 土地利用生態效益目標
運用土地利用生態服務價值評估來構建土地利用生態效益函數。根據謝高地等對各類土地利用的單位生態服務價值的研究,確定土地利用類型的生態效益系數(表1)[11]。
將用地類型與各陸地生態系統的利用類型相對應,耕地、園地、林地、草地、水域、未利用地分別對應農田、園地、森林、草地、水域以及難利用地,建設用地生態系數為0,得出土地利用生態效益目標函數為
F3(x)=6 114.3x1+7 607x2+19 334x3+6 406.5x4+40 676.4x6+371.4x7→max。
2.3 約束條件
綜合考慮烏魯木齊市的有關政策和規劃,并結合實際土地總面積、各用地類型面積、碳減排等作為約束條件,共計9個約束條件。
2.3.1 土地總面積約束
烏魯木齊市2020年規劃面積為 1 378 310 hm2,且各土地利用類型面積非負,可建立約束條件為
∑7j=1xj=1 378 310,xj>0。
2.3.2 耕地面積約束
耕地具有保障糧食安全和保護生態系統良好運轉的雙重功能,因此必須嚴格執行耕地保護政策,嚴守耕地紅線。根據烏魯木齊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要切實保護耕地和基本農田,嚴格實施“占補平衡”政策,保證補充的耕地數量不減少、質量有增加,到目標年(2020年),確保耕地保有量68 957 hm2。此外,考慮到城鎮化的持續推進,耕地面積的減少趨勢在短時間內難以逆轉,將2015年的耕地面積設為上限。即耕地面積約束條件為
68 957≤x1≤76 175。
2.3.3 園地面積約束
根據2009—2015年各年的園地現狀數據顯示,全市園地面積逐漸減少,但園地屬于經濟林類型,能產生較高的經濟效益,又具有一定的碳吸收能力,于是,將規劃中2020年園地面積設為下限,可建立園地面積約束條件:
x2≥6 033。
2.3.4 林地面積約束
森林作為最大的有機碳庫,林地是增加碳吸收的主要源頭。根據烏魯木齊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烏魯木齊市未來要強化綠洲生態保護屏障,加強綠色空間建設,在對天然林進行保護的同時,對荒漠化林地進行封育。因此,圍繞綠化建設目標,應加強林地管理,以規劃中2020年林地預期面積設為下限,可建立林地面積約束條件為
x3≥72 861。
2.3.5 草地面積約束
草地具有良好的水土保持作用,要保證草地面積的基本穩定,保護和合理利用草場資源。根據規劃,至2020年,烏魯木齊市草地預期面積為880 272 hm2,因此,草地面積約束為
x4≥880 272。
2.3.6 建設用地面積約束
建設用地是各項經濟活動的主要載體,是最主要的經濟增長源,但與此同時建設用地也是最主要碳源地,帶來了巨大的碳排放,建設用地快速擴張,不僅帶來糧食安全問題,給生態也帶來壓力。因此,按照規劃要求,至2020年,烏魯木齊市建設用地面積應控制在 128 851 hm2。并且城市化快速發展,建設用地的轉變一般不具有可逆性,至2020年時建設面積不會低于現狀值,由此,建設用地面積約束為
105 106≤x5≤128 851。
2.3.7 水域
根據規劃目標,至2020年,水域面積預計為11 394 hm2,但水域具有較高的生態服務價值,要加強水域地保護,確保居民用水安全,則結合2015年現狀,確定水域面積約束為
x6≥28 046。
2.3.8 未利用地
隨著發展對土地需求的不斷增加,以及科學技術的逐漸提高,未來烏魯木齊市的未利用地將有很大一部分被開發,面積將逐步減少,據規劃預測2020年其面積約為209 942 hm2,確定未利用地面積約束為
x7≤209 942。
2.3.9 重要生態功能用地
為了更好地保護生態環境,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耕地、園地、林地、草地、水域以及未利用地等具有重要生態功能的土地應占全市總面積的75%以上,則:
x1+x2+x3+x4+x6+x7≥1 033 732.62。
3 優化結果與分析
3.1 模型求解
多目標線性規劃模型求最優解的方法有理想點法、線性加權法、遺傳算法、匿名函數法等。其中,運用線性加權法求解多目標線性規劃模型的思想較為廣泛,但由于本模型中3個目標函數的取值方向和數值單位都有所不同,且數量級差異較大。因此,綜合考慮下,本研究利用匿名函數來求解此優化目標。
根據優化目標的要求,土地利用經濟效益目標和生態效益目標求最大值、碳排放目標求最小值,先統一目標函數取值方向,將土地利用經濟效益目標和生態效益目標取負值求最小值,然后將函數和約束條件輸入Matlab 2014軟件的編輯器中,求解出低碳視角下的烏魯木齊市土地利用結構優化模型(圖1)。
最終優化結果見表2。
3.2 優化方案分析
將優化的結果與目標規劃年的各類型土地利用面積進行對比,并結合2015年現狀土地利用狀況進行分析。從表3可以看出,基于低碳視角的土地利用結構優化方案中,所有土地
利用類型的面積均有不同程度的變化。
其中,優化后的耕地面積相比2015年減少了約 6 912 hm2,但與2020年規劃的面積相比有所增加,增加了306.18 hm2,在耕地逐年減少的現實趨勢下,應盡可能充分地保證烏魯木齊市的糧食安全。園地方面,優化面積與規劃面積相比有所增加,由于園地同時具有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面積的增長有助于烏魯木齊市土地利用綜合效益的提高。優化后的林地、牧草地占土地總面積的比重與規劃相比也都有所增加,分別增加了0.02、0.06百分點,表明林地、牧草地在基于低碳目標的優化過程中碳匯效應和生態效益得到了體現,因此要加大植樹造林力度,對未利用地進行綠化,通過植樹種草提高碳匯。水域的優化面積較現狀有所減少但較規劃面積有大幅度增加,由于水域具有較高的生態效益,且為了確保居民用水安全,必須要加強水域的保護,因此較現狀的小幅降低符合現實需求。此外,未利用地較規劃有所減少,減少了約 9 268 hm2,較現狀減少了約 120 001 hm2,由于未利用地的生態服務價值較低,且隨著科學技術的提高,沙漠變綠洲已經成為可能,因此加大對未利用地的開發利用,將未利用地轉變為草地、林地能夠大大提高生態服務價值,并且建設用地開發優先占用未利用地,可以大大控制耕地的減少。優化后的建設用地面積有所減少,比規劃面積減少了8 919.41 hm2,表明雖然建設用地能帶來較大的經濟效益,但同時也造成了巨大的碳排放,為了綜合效益的最優,要控制建設用地過快增長,轉而加強建設用地的內涵式挖潛,符合土地集約節約利用的政策要求。并且烏魯木齊市目前也開始在進行舊城區改造,拆違拆舊,優先利用閑置土地,建設用地增加速率有減小趨勢。
可以計算出規劃方案和優化方案的土地利用經濟效益、土地利用碳排放和土地利用生態效益(表4)。
從表4可以看出,2020年土地利用規劃目標下的土地利用碳排放量達到2 651.98萬t,而優化后的土地利用碳排放量為2 467.41萬t,減少了184.57萬t,并且土地利用生態效益也從80.57億元增加到87.50億元,增加了6.93億元,說明優化實現了碳排放的減少,同時也提升了生態效益。但優化后的土地利用經濟效益為3 551.61億元,較規劃目標的經濟效益減少了257.9億元。這是由于建設用地是主要碳源地,為了實現碳減排目標,要通過控制建設用地面積和增加草地、林地等碳匯地面積來實現,這勢必會對土地利用的經濟效益產生影響。但十九大報告提出了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要求,綠色GDP核算體系在逐漸推行,即在計算GDP時將經濟活動帶來的資源損耗和環境降級成本從GDP中扣除,因此現在不再是一味地追求GDP快速增長,而是要經濟增長與自然環境和諧統一,要經濟增長對環境的負面效應盡可能小,表現了優化方案實施的可行性。
綜上所述,基于低碳視角下對土地利用結構的優化調整,能在保證經濟平穩增長的同時,有效地實現碳減排,并且兼顧土地利用生態效益的提高,基本能夠滿足烏魯木齊市土地利用綜合效益最優的要求。
4 結論
基于碳減排目標構建多目標規劃模型,以經濟效益、碳排放和生態效益為目標函數,并設立約束條件,運用Matlab 2014軟件對模型進行求解,求得2020年烏魯木齊市土地利用結構優化方案。將優化方案與規劃方案對比,耕地、園地、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面積有所增加,體現了基于低碳目標的優化過程中碳匯效應和生態效益的作用。優化后的建設用地面積有所減少,表明雖然建設用地能帶來較大的經濟效益,但同時也造成了巨大的碳排放,為了綜合效益的最優,要管控建設用地過快增長,加強建設用地的內涵式挖潛。
將規劃中和優化后的各土地利用類型的經濟效益、碳排放和生態效益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優化方案中碳排放降低了184.57萬t,土地利用生態效益也增加6.93億元,雖然土地利用經濟效益較規劃方案減少了,但符合當前中高速增長的經濟發展規律,進而表現了優化方案實施的可能性。
研究表明,以土地利用經濟效益最大化、碳排放最小化和生態效益最大化作為目標函數,構建多目標線性規劃模型對土地利用結構的優化,能在保證經濟平穩增長的同時,有效地實現碳減排,并且有助于土地利用生態效益的提高,對今后烏魯木齊市的土地利用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由于一些數據難以獲取,模型中僅選取了經濟效益、碳排放和生態效益作為目標函數,沒有加入社會效益,可能約束條件也不夠充分。今后對于土地利用社會效益的量化途徑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并補充約束條件,構建更為精確的土地利用結構優化模型。
參考文獻:
[1]曲福田,盧 娜,馮淑怡. 土地利用變化對碳排放的影響[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1,11(10):76-83.
[2]李國敏. 城市土地低碳利用模式的變革及路徑[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0(20):62-66.[HJ1.5mm]
[3]趙榮欽,劉 英,郝仕龍,等. 低碳土地利用模式研究[J]. 水土保持研究,2010,17(5):190-194.
[4]毋曉蕾,王 婧,汪應宏,等. 淅川縣土地利用結構低碳優化研究[J]. 地域研究與開發,2013,32(2).160-164.
[5]Cai Z C. Estimate of CH4 emissions from year-round flooded rice fields during rice growing season in China[J]. Pedosphere,2005,15(1):66-71.
[6]何 勇. 中國氣候、陸地生態系統碳循環研究[M]. 北京:氣象出版社,2006:141-152.
[7]IPCC.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Ⅱ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45-52.
[8]吳慶標,王效科,段曉男,等. 中國森林生態系統植被固碳現狀和潛力[J]. 生態學報,2008,28(2):0517-0524.
[9]任繼周,梁天剛,林慧龍. 草地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響應及其碳匯潛勢研究[J]. 草業學報,2011,20(2):21-22.
[10]段曉男,王效科,逯 非,等. 中國濕地生態系統固碳現狀和潛力[J]. 生態學報,2008,28(2):463-469.
[11]謝高地,甄 霖,魯春霞,等. 一個基于專家知識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化方法[J]. 自然資源學報,2008,23(5):911-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