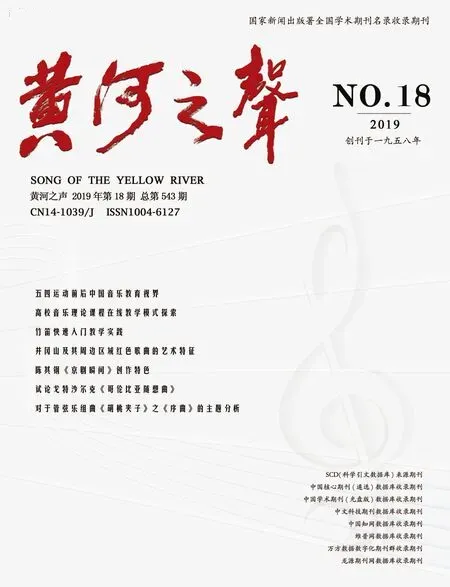五四運動前后中國音樂教育視界
陳雅丹
(浙江師范大學,浙江 金華 321004)
通過對《中國近現代音樂教育文選》第一部“音樂教育概論”近二十篇文獻的閱讀,可以發現有關中國近現代音樂教育發展的討論不外乎于對音樂的定義、古今音樂之關系、中西音樂關系、音樂的價值功能以及音樂與其他藝術的關系等問題。這些豐富、珍貴的資料,是研究近現代音樂教育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藝術中最一般的,最純粹的,最深刻的,就要數音樂了。無論古今中外,音樂常被認為有著重要的價值。
一、有關“音樂”、“音樂教育”的概念界定
世界萬物皆有定義,知道它是什么東西才能知道它的作用,知道它的作用才能知道它存在的意義。既然音樂被認為是一門科學,那就必須要知道它的定義是什么。曾志忞對音樂下了一個簡明的定義即“音樂者,以器為本,以音為用,音器相和,是為神樂”。人生來就有追求美的情操,視覺如此,聽覺亦是如此。音樂就是聽覺藝術。音樂與詩歌、雕刻及其他美術相比,有一種靈妙的魔力,能感動人的心靈。因此,我生在《樂歌之價值》一文中對音樂作出定義,即“音樂者,籍樂音以發表美的感情,即悉耳之美術也”。而在《中國音樂改良說》中,匪石將音樂定義為中國的古代音樂,“即在當日,亦僅作之郊廟,歌之朝堂,奴臣婢妾,以蹈以舞”。古代音樂是詩、樂、舞三者相結合的,運用于郊廟、朝堂、賓客等場所。賈新風在《音樂教育通論》(節錄)中提到中國將來的音樂“當于西洋音樂之理論與技巧中,發揮中華民族的國民性,以完成中華民族的世界音樂。”
音樂對人心的要求,勢力甚強,音樂的感化力能被視為音樂的生命力。音樂在人們的心中有著偉大之勢力,因此有人利用音樂陶冶心身,涵養德性,成為善美之人,因此我生將這一方法稱為教育音樂。賈新風在《音樂教育通論》中認為,音樂教育分為廣義和狹義兩個范圍。廣義的音樂教育即“音樂化的全般教育”,狹義的音樂教育即則是屬于全般教育中的一科。音樂在眾多藝術門類中,可以算得上是全藝術的藝術了。有人認為今日的文明將由眼的文明,移到耳的文明上了。因為音樂給人情感的移入,比其它的藝術有力量的多,并且音樂的特性,是最為抽象的感情表現,所以有極難把握的抽象性。因此賈新風將音樂教育定義為“乃專事研究音樂知識,及培養愛好音樂的感情,及鑒別音樂的能力,而使音樂能充分發揮其德性,以達藝術治人之目的也。”
二、音樂的功能價值作用
關于音樂的功能價值,在中國近代知識界中有了一定的認識,不少學者對音樂的作用有著不同的看法,這不僅有從事音樂事業的學者,也有從事其它教育領域的學者。但是在從這些文章中不難發現,學者大都是從音樂的實用功能出發的,通過音樂教育改造國民品質,喚醒人們的意識,培養愛國的情感需要音樂,挽救中華民族是每一位知識分子共同的奮斗目的。音樂可以振奮人的精神,激發人的斗志,使人們為實現崇高的目標而積極進取。
知識分子們認識到音樂對育人救國有著景是離不開的。清朝末年,中國民族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國已經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清政府還只把音樂課作為隨意科目來看待,在實際的音樂課堂教育中,當時的政府教育主管部門還沒有把音樂放在重要位置,而只是視作“隨意科目”而已。這時許多學者都在思考改進中國音樂教育,1904年曾志忞在《音樂教育論》撰文強調音樂的重要性。在學校教授唱歌,可以使學生得到“發音之正確,涵養之習練,思想之優美,團結之一致”的收獲。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也指出“蓋欲改造國民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劍虹在《音樂于教育界之功用》一文中,還著重對音樂在學校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探討。劍虹指出,音樂是世界各國的教育家公認的一門重要的學科,在幼稚園和小學校中,“幾有舍音樂不能成立之勢”,就是到了中學,每周仍“授業一二時或二三時”。
人生來就有追求美的情操,視覺是這樣,聽覺亦是這樣。音樂就是聽覺藝術。欣賞美術需要智識,但音樂不盡然。音樂的感化力可視為音樂的生命,將此用于軍事、政治上,可以鼓舞士氣、振作精神,忘掉利益與生死。用于恍惚靡定、窮困潦倒或脾氣暴戾的人,能感化他們的心靈,讓其心有所依。音樂對人心有著如此大的作用,于是可以將音樂用于陶冶心身,涵養德性,成為善美之人,將這一過程可稱為教育音樂。學校開設唱歌科,源自于古代希臘的教育法,我國雖然也開設了此科,但大多數都很不注重,是因為沒有明白唱歌真正的價值。音樂能養成美的觀念,使得趣味高尚,精神快活,感受純良高潔的快樂,涵養協和共同之心,擁有圓滿的人格。唱歌還能磨煉聽覺及發聲的機關,調整呼吸作用,旺盛肺之運動,增進肺臟的健康,促進血液的循環,讓身體得以強健。矯正粗俗的歌謠,振作國民的元氣,是移風俗的利器。音樂的學習能補其他科目,任何學科都是以兒童心意的教養為目的,音樂能使這一目的更好的達到。音樂能方便利用,是為教育之一方便利用之者。綜上所述,唱歌的效果,能養成圓滿感情,啟發智能,訓練道德的意志,強健身體,還可完成教育的目的。
三、古今音樂之關系
音樂開幕之期,莫如我國先。古時有伏羲作瑟、作琴,堯作磬,舜作蕭。六代樂舞,黃帝曰《云門大卷》、堯曰《大咸》、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匪石在《中國音樂改良說》中提到“即在當日,亦僅作之郊廟,歌之朝堂,奴臣婢妾,以蹈以舞。”雖然有所保留古樂中的一二,但是不能發揮國民之精神,尚足以代表寡人之性質及行為也。孔子曾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又曰“詩,可以興,可以群,可以觀,可以怨。”但直至今日,古樂的性質已經完全被磨滅了。
周朝任命樂師做官吏,把音樂列入六藝之一,作為必修科目,每逢大合樂的時候,周王必定領著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自到場聆聽。周朝的音樂雖偏重于貴族方面,但是同時“禮”與“樂”一樣重視,習樂者必須習禮,必須知禮,必須守禮。“禮”就是維持社會安寧的一定的秩序,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道德的制裁。音樂生活是從感情和心靈發出的,禮是以理智為立場規定一切的,禮樂互相節制互相調和。因此孔子說“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唐朝設立教坊,羅致全國樂工,又設宜春院、云韶院,蓄養一班女樂,唐明皇并且有時還會在梨園親自指揮奏樂,梨園弟子因此還有“皇帝弟子”的稱號。教坊、宜春院及云韶院的男女樂工,專為皇帝娛樂而演奏音樂,他們只需有一技之長就可以被選進去,他們的常識如何,品性如何,概不過問。宋朝的教坊子弟也是如此,宋朝之后的戲子更是如此。他們既沒有受過普通教育,又缺乏理智的節制,因此常有逾閑失檢的舉動,結果引起當時士大夫的蔑視,于是與優伶并稱,甚至優、倡、奴、隸四種人并在一起,音樂的地位于是一落千丈。
四、中西音樂之關系
為何要學習西樂?因為我國的古樂今樂都存在弊端。匪石在《中國音樂改良說》中,通過批判古樂今樂存在的弊端,宣揚我國的音樂急需變革,應引進西樂造中國之音樂。在否定古樂今樂后,中國音樂該如何改良?“西樂哉,西樂哉!”。西樂具有的進取思想,是現存音樂所沒有的。但是匪石也不提倡將中國傳統音樂,全盤西化,而是廣泛吸取古今中外音樂中優秀的部分,中西結合。此外他還舉出日本的音樂改革,說明引進西樂并不會影響民族性,只是讓音樂往更完善的方向發展。
歐美、日本等國,只要是重視教育的學者,沒有不重視音樂的。甚至將小學的歌唱一科,與國語并重。曾志忞1903年發表的《樂理大意》,從時間上看,這是中國音樂史上第一個由中國人發表傳播西方基本樂理的文章。更為重要的是,曾志忞對樂理重要性的強調,即他認為,歐美、日本等國將唱歌與國語放在同等的位置,它們經由教育家、理論家近百年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音樂成果。同時學者們也十分清醒的認識到,西樂的引進不是全盤接受,而是吸收一些對中國音樂發展有益的東西,不能丟失自己本土的文化。
蔡元培將中西音樂發展現狀作了一個比較,歐洲各國在培養音樂人才以外,音樂更是豐富人們生活的必備工具,無論是公園或是咖啡廳,不論是小城鎮還是大都市音樂無處不在。但是中國的音樂在秦朝以前頗為發達,到如今卻是不斷退化,就算是喜愛音樂的人,也是對著以前的舊譜子依式演奏,沒有創新。要明白音樂是促進文化發展的利器,要采西樂之長,補中樂之短,讓我國的音樂以時進步。
五、音樂與其它藝術之關系
現在的文明,將由眼睛能看到的文明轉移到耳朵能聽見的文明中。因為音樂給人情感的移入,比起其它的藝術而言,有力量得多,并且音樂的特性,是因為最抽象的感情的表現,所以有極難把握的抽象性。它有極難把握的抽象性,所以有極為詳盡的精密性。因為音樂具有這些特性,所以賈新風認為“音樂能凌駕其諸姊妹藝術之上。”
梁啟超強調詩與樂相結合的重要性。國人沒有尚武精神,有一端就是因為音樂靡曼,而詩歌的結合能產生強烈的振奮人心的力量。想要改良國民的品質,詩歌音樂是十分重要的,這就得讓詩歌與音樂相結合,并在大眾中普及和推廣,讓詩歌中的精神文化通過詩歌傳達到每一位民眾的內心深處。詩歌音樂的結合,能便于吟唱和普及,達到“樂教”的目的。梁啟超十分重視音樂與教育、詩歌的聯系,我國古代詩經十分豐富,能按不同內容編排出不同的詩歌,表達不一樣的情感,用這些古詩詞來譜寫歌曲,何須擔心屬于我國自己的歌會缺乏?在學校教育選歌方面,也要注意歌曲是否適合兒童諷誦。詩歌與音樂的結合是十分具有積極進步意義的,體現了作者強調音樂教育的德育功能。這也是由于當時的社會背景,維新變法后,梁啟超來到了日本,在日本廣泛了解西方的思想。新的思想給梁啟超帶來了很大的影響,認識到自己本國文化急需變革,應該要打破原本那種沉悶的氣氛。而變革首先就應從教育開始,開啟民智,鼓動改良運動。梁啟超認為音樂對人有調節作用,音樂可作為精神要素改造國民的品質,國民品質的改變能影響國家整體政治變革。而音樂的實用功能,正是梁啟超所需要的,因此他十分推崇詩歌合一。
曾志忞強調歌曲的創作既要對詩歌有艷艷,也要對作曲有研究。要拋棄我國以前固有的作曲思想,學習西方作曲技術,結合我國詩詞,做到“曲與歌不可離,歌與曲不可背”。
六、結語
綜合這一部分的文獻,發現每一位作者都很注重音樂教育的功能,也有涉及音樂的其他作用如音樂在社會、外交、軍事等方面。其中好幾位學者都曾遠赴日本學習接觸新的思想,盡管剛開始接觸的并不是音樂,如曾志忞剛赴日本時學習的是法律,而梁啟超更是一位政治變革者。但是由于時代的需要,一批具有進步思想的青年為中國的變革發出了吶喊。他們看到要想變革成功,就要先從教育出發,用音樂感染人心,鼓舞士氣。但是他們所主張的內容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梁啟超,他雖然重視到了音樂的實用功能,以此用作發展音樂的動力,沒有看到音樂的藝術功能。而曾志忞認為“中國之物,無物可改良也,非大破壞不可,非大破壞而先大創造亦不可”。這未免有些太過度貶低本民族之物,會影響民眾對民族的信心,對本民族文化產生消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