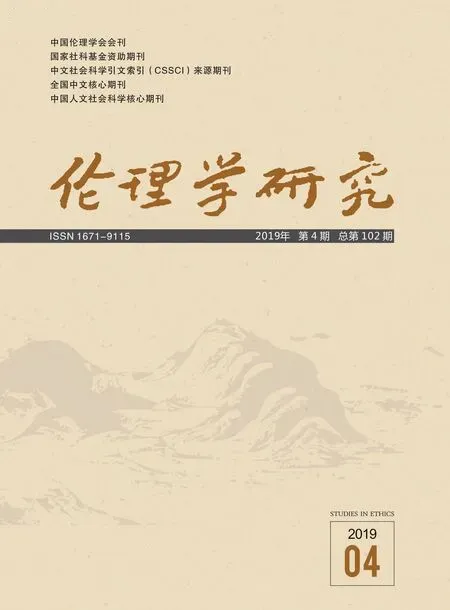論慈善活動中的個人偏好
聶文軍
一、什么是個人偏好
個人偏好或個體偏好(individual preferences)是個體在其社會實踐活動中呈顯出來的、對某些事物或某種活動的喜愛或喜好。“穿衣戴帽各有所好、羅卜白菜所有所愛”,由此可見個人偏好在人類社會的各個階段或時代都或隱或現地存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物質資源越來越豐裕,消費者的各種非經濟偏好如審美偏好、情感偏好、道德偏好等就會越強烈。”[1]進入現當代社會之后,個人偏好不僅在其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中和社會經濟生活中(消費偏好、投資偏好、風險偏好等)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而且在個體參與的政治生活中也得到了較明顯的體現(被稱為政治偏好、選舉偏好、政策偏好等);在文化、體育、娛樂和休閑生活中更是呈現出了不同個人對不同事物的各自偏好。
個人偏好是個體差異性——由個體認識與情感喜好等諸多因素共同決定——的一種表現。在社會結構穩定、社會變化和發展緩慢以及社會流動性缺乏的歷史條件下,個體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活簡單、內容貧乏,人們只能在極其有限的選擇范圍內作出選擇,從而使得個人之間的偏好的多樣性與差異性不是十分明顯。進入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的近現代社會以來,社會生產的不斷發展日益突破傳統社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限制,使得人們的日常社會生活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極大的擴展或加深。人們進行選擇的時間范圍和空間范圍以及做出選擇的對象范圍都大大拓展,在個人主義及自由理念的驅動下,不同個人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中的個人偏好得以極大地凸顯。
從法學的觀點看,社會組織是擬人的。具有與法律上個人同等的法律地位。因此,本文關于“慈善活動中的個人偏好”的觀點也適用于法人、專業慈善組織和其他組織的慈善活動。
二、慈善活動中的個人偏好
什么是慈善活動?簡言之,慈善活動即做慈善;寬泛地說,就是指人們在道德上做好事或善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對“慈善活動”則有著嚴謹的界定,慈善活動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以捐贈財產或者提供服務等方式,自愿開展的下列公益活動:(1)扶貧、濟困;(2)扶老、救孤、恤病、助殘、優撫;(3)救助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和公共衛生事件等突發事件造成的損害;(4)促進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等事業的發展;(5)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6)符合本法規定的其他公益活動。”可以說,慈善活動廣泛全面地囊括了個人與不同社會組織各種具有善的性質的行為。
個人偏好的廣泛性和多樣性不僅體現在個體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十分自然地體現在其道德生活實踐中;甚至有學者把道德視為個人偏好的表達,“所有的道德判斷,就其具有道德的或評價性的特征而言,都無非是偏好的表達、態度或情感的表達。”[2](P14)作為道德認識的判斷都具有作為偏好呈現的特征,人們在其道德認知或道德理念指導下(指引下)的道德活動或行為自然也具有相應的偏好特點。只要稍加注意,我們就會看到在現當代社會的道德生活領域中存在著豐富多樣的個人偏好現象。
所謂慈善活動中的個人偏好即個人在道德上的偏好,是指個人在慈善活動中——個體做好人好事的行善中——呈現出來的對某些善行善事的偏愛、喜愛或愛好。雖然慈善組織、企業家或慈善家、普通民眾在面對突然的、重大的自然災害事件時,都會表現出“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共同道德情懷和道德支援;但在其日常的道德實踐或慈善活動中,他們卻呈現出顯著的各自不同的個人偏好。
慈善活動中的個人偏好正如人們在日常社會生活中的個人偏好一樣也是普遍存在的。有人喜歡救助孤寡老人,有人喜歡照顧兒童;有人喜歡動物保護,有人喜歡自然環境的保護;有人喜歡捐資助學,有人喜歡捐助體育;有人喜歡錦上添花,有人喜歡雪中送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實際上,慈善活動中的偏好特征不僅在作為自然人的個體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而且在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慈善活動中得到了體現。不同性質的法人和不同的專業慈善組織在其各自的慈善活動中都表現出了各自對不同慈善活動的專注與側重,也就是說,它們的慈善活動具有各自不同的偏好。例如,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不對個人而是研究機構和社會團體,通過它們的活動來促進人類的健康;國際紅十字會主要著眼于戰傷救護(先發展為廣泛的自然災害救助和醫療救護等);卡耐基基金會把圖書館和學會的建設作為其慈善活動的最佳選擇;世界自然基金會(原名“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專注于全球瀕危物種的保護;“無國界醫生”組織救助世界各地需要醫療救助的民眾;比爾·蓋茨和梅琳達基金會旨在促進全球衛生和教育領域的平等,如此等等。因為只要個人在道德上呈現出各自的個人偏好,由個人或不同個人共同創建的法人、慈善組織等等自然也會受到創建者的價值傾向、情感因素等個人因素的影響而呈現出在慈善活動中的偏好特征。
三、如何看待慈善活動中的個人偏好
隨著中國社會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發展,慈善活動逐漸進入我國社會生活和人們的視野。一方面,眾多社會人士的慈善活動受到人們的高度贊揚,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特別是著名企業家、社會名流等——的一些慈善活動受到人們的質疑。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的當天,由著名企業家王石執掌的萬科企業捐款200萬元人民幣就被很多人指責捐款太少;2014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曾在耶魯大學讀書一年的張磊事業有成后向耶魯大學捐款888萬美元,因未向母校中國人民大學捐款而被指“忘恩負義”;2014年7月,潘石屹向哈佛大學捐款1億美元也受到不少人的質疑;如此等等。為什么做好事善事的人不僅沒有受到人們的贊揚反而受到人們的指責或責難呢?網絡時代的道德輿論場人人可以發聲,我們究竟應當如何看待普通人和企業家們(慈善家)作為個人偏好的慈善活動呢?
1.尊重和肯定慈善活動中的個性化選擇
任何道德判斷或道德評價都必須立足于該道德事件所處的時代,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重要原則,也是我們進行道德評價的基本依據。
從人類社會形態的歷史演變來觀察,西方社會經歷了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演變,中國社會則經歷了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演變,應當說都大致經歷了從自然經濟的農業社會到工業經濟的近現代社會的演變;伴隨著科學技術的巨大發展,信息時代和網絡時代更是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人類當代社會顯著的突出的共同特征。以工業經濟為基礎的現當代社會采用了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這使得生活在現當代社會中的人們普遍接受和踐行自由、平等的價值理念和行為方式。人們在經濟、政治、文化、體育、娛樂休閑等等社會生活中均表現出各具個性、各具特色的言論與行為。同樣,人們在道德生活中也是如此。任何人、每一個人只要不違背社會的道德底線或底線倫理,只要不去傷害或損害他人和社會的利益,都可以按照他們各自的價值判定和情感偏好去做慈善,去做好事善事。這是由現當代社會的基礎性價值的自由理念——當然也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核心理念——所決定的。
人們的道德生活的觀念與行為方式是由其所處時代的社會生活條件決定的。商品經濟的生產、競爭、貿易、擇業等等方面的自由要求必然滲透和擴展到整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必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核心的和基本的價值理念。人們在道德領域的慈善活動也像在其他領域中的活動一樣,成為人們可以依據個性作出自己選擇的權利,而不再是前資本主義的傳統社會條件下每一個人都必須履行的義務。
生活在現當代社會中的人們,在遵守法律和社會底線倫理——不損害他人和社會——的條件下擁有廣泛的和全面的自由。道德自由無疑也是人們自由的重要內容,所謂道德自由即行善的自由,是做好事、善事,做慈善活動的自由,一個人做怎樣的好事善事、做怎樣的慈善活動、做多少好事善事、做多少慈善活動、做多大的好事善事、做多大的慈善活動,都是每一個道德行為主體——包括各類慈善機構或慈善組織——的個人權利,我們不能通過法律的手段或社會輿論的手段去逼迫、強迫或強制任何一個人去做好事或慈善活動。在現當代社會里,不同個體在慈善活動中呈現出十分顯著的個性化選擇,是由各個個人的家庭出身、經濟條件、教育程度、道德理性能力、情感偏好、風俗習慣等等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充分尊重和肯定每一個體在道德實踐領域中的個體性、多樣性、獨特性的選擇,這是人類社會發展到當今時代的各種客觀條件使然。
人們的道德態度與道德判斷必須與社會、時代的發展需要相一致。當我們對他人的慈善活動——如捐款數量、捐款次數、捐款對象等等——感到不滿,甚至予以指責或責難時,這實際上侵犯、干涉了他人的道德自由,侵犯了他人做慈善、做好事善事的自由。這是與現當代社會的基本價值理念和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核心價值之一——自由——相違背的。因此,一個人只要作出了慈善活動,我們就不能以自己的認識或社會的要求等等為由予以干涉或指責。從正面的積極的視角來看,不同個人在慈善活動中的不同偏好,雖然各自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們確實各自滿足了他人與社會的不同的道德需要,因而理應得到社會的肯定與尊重。正如孔子所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3](P61)。一個人對特定道德事物或道德活動的偏愛或喜愛,既對他人和社會有益,也對道德實踐者有益,如果道德實踐者以此為樂,無疑會大大激發其道德積極性。在現當代社會,任何一個個體只要是實實在在、確確實實在做慈善活動,在做好事善事,每一個人以及社會輿論就不能只是按照該社會的最高價值標準、最崇高的道德境界去整齊劃一地要求具有現實道德水平差異的每一個人,而是要立足于每一個人當下所做的慈善活動、好事善事來予以必要的肯定和贊揚,這既體現了對個體道德自由的肯定與尊重,又有助于個體道德積極性的更進一步發揮。
2.慈善活動中的個人偏好不能妨礙或損害他人的合法權利
在當代社會極其多樣復雜的條件下常常會出現諸多矛盾。道德生活領域中的個人偏好因其強烈的認知因素、價值因素、情感性等等因素也會使得慈善活動與他人的社會正常活動產生沖突。因慈善活動的個人偏好引發的問題引人深思,我國2011年的“攔車救狗”事件最為典型。
2011年4月15日,一些特別愛狗的人士和動物保護志愿者在京哈高速公路張家灣收費站“攔車救狗”。當天中午約12點,在京哈高速張家灣收費站附近,一輛從河南出發開往吉林的載有520只待屠宰狗的卡車被愛狗人士攔下;當時經警方和動物衛生監督部門調查,該車持有真實有效的檢疫運載證明,運狗車證照、手續齊全,屬于合法運輸和經營,任何人都沒有理由扣車。但愛狗者卻拒絕放行。不少志愿者和公益組織獲知消息后前往事發地點;現場有50余名志愿者和中國小動物保護協會等10余個公益組織。毫無疑問,這一事件鮮明地呈現了那些動物保護志愿者在慈善活動中的個人偏好,但他們的活動卻造成了較為嚴重的社會不和諧。
一些人對狗有特別的偏好、有特別的喜愛,這是他個體偏好的表現,愛狗、收留照看流浪狗也無疑是愛心之舉。但個人偏好的慈善行為無論如何不能逾越法律的約束,不能妨礙、妨害他人和社會組織正常合法的商業活動與社會生活。
2011年的“攔車救狗”事件之后類似事件仍時有發生,2014年廣西玉林狗肉節期間發生了愛狗人士與餐飲店經營者以及消費者的爭執與沖突;我們也看到不少成長中的少年就時常因各自所好的影視偶像各異而相互爭吵甚至嚴重沖突。從理論層面來看,很多個人往往會因自己一般日常生活中的所好與道德生活中的所好而蔑視、指斥甚至阻礙或禁止他人之所好。這些事件都啟發和警示我們:我們每個人都希望他人理解與尊重我們之所好,我們也理應理解與尊重他人之所好;我們決不能因為自己在慈善活動中的個人偏好而妨礙、妨害其他個人(社會組織)在日常社會生活與道德生活中的正當合理的活動和法律上的合法行為。不同個人在慈善活動中的不同偏好,可以并行而不悖,共同有益于整個社會的道德。任何個人都沒有權利因為自己對某一慈善活動的喜愛或偏好而要求或強迫他人也喜愛或偏愛這一慈善活動。任何個人在慈善活動中的個人偏好都不能妨礙或妨礙其他人(社會組織)在道德上和法律上展開其合法活動的正當權利。
3.慈善活動中的個人偏好應予以引領和提升
從觀念的字義的層面和從現實的層面辯證地考察,我們都可以發現,慈善活動中的個人偏好是利弊并存的。從字面看,慈善活動中的個人偏好(piān hào),對道德事物有所“好(hào)”當然對社會有益,是“好(hǎo)”的;“偏”又意味著有所選擇,有所為(只做個人感興趣的道德之事)有所不為(個人對其不喜歡、不感興趣的道德之事則予以不顧),這當然在道德上是有不足、有缺陷的。孔子多次慨嘆“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3](P92)孔子所期望或希冀的不是對個別的、局部的、有限的道德事物或慈善活動的喜愛或偏好,而是人們對整個道德或道德本身的喜愛或熱愛,是“見善如不及”的全面的道德行為。從現實層面來看,一方面,慈善活動中的個人偏好呈現出強烈的和豐富的個體差異性,這固然體現了千千萬萬不同個人在道德上的自由并造就了整個社會道德生活的豐富多彩,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與積極性,有益于他人與社會;另一方面,慈善活動中的個人偏好又會因個體強烈的自我意識、道德認識的局限性、情感的執著等等因素而在某些方面存在道德上的不作為以及和他人的個人偏好相沖突,從而有損于他人和社會。從我國《慈善法》所列慈善活動的種類可見慈善活動所包括的范圍之廣泛與全面,社會與他人在道德上有待他人援手的道德之需是十分多樣的。因此,慈善活動中的個人偏好需要通過社會的道德教育予以引領和提升。
慈善活動中的個人偏好需要得到引領和提升,還可以通過深入到社會的內部予以考察來得到闡明。任何一個社會都是由生活其中的千千萬萬個人組成的。從共時性(橫向)視角來看,構成任何一個社會的眾多個人——從一歲的嬰幼兒直到百歲及以上的耄耋老人——無疑存在著個體的代際維度(三代、四代、五代不等),這些處于不同代際的個人共同生活于同一社會之中,他們的道德態度、傾向與實踐方式自然會呈現出不同代際的個人偏好差異。廖小平教授認為,道德價值觀的代溝與溝通問題是代際倫理的主要問題之一。“現代社會的顯著特征之一,就是現代與傳統、國內與國外等各種道德價值觀被濃縮到同一個時空并在同一個平臺上相互激蕩,它們的相互作用不僅表現在同代的各共同體之間,而且越來越表現在代與代之間。因此,必須分析產生代與代之間道德價值觀差異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原因,創造道德價值觀代際溝通的條件,建立道德價值觀代際溝通的機制,探尋道德價值觀代際溝通的規律。”[4]處于不同代際的個人偏好不僅體現在諸多日常活動中,而且也體現在他們的道德活動中。“上一代通過道德示范和灌輸等實現對下一代的道德教育,而下一代也通過文化‘反哺’等形式對上一代產生影響。”[4]不同代的個體之間通過代際倫理的相互作用來促進和實現各自的道德變化、發展和提升。從歷時性(縱向)視角來看,根據美國當代著名道德心理學家勞倫斯·科爾伯格(Lawrence Kohlberg,1927—1987)道德發展心理學理論所得出的實證結論,每一個體的道德狀況在其一生中會呈現出明顯的發展階段性,每一個體的道德狀況由其道德判斷能力(道德思維能力)所支配和主導,隨著其年齡、心理、認知能力、情感等等因素的變化而變化發展,科爾伯格為此把每一個體的道德成長發展歷程概括為“三水平六階段”[5]。構成社會的千千萬萬個人的道德既具有共同性又呈現出差異性。因此,我們既需要尊重不同個人的道德差異與個人偏好,又需要引領和提升不同個體的道德水平和道境界。如果眾多個人不能得到有效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引領,其個人的道德發展就可能出現停滯甚至倒退,個人之間就會產生諸多道德上的對立或沖突。
用什么來引領和提升一個社會中千千萬萬不同個人在慈善活動中的個人偏好呢?當然是以“為人民服務”為根本的社會主義道德原則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引領和提升作為個體的廣大社會成員。我國社會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立足于我國社會的實際,我們需要把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與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有機結合起來;為人民服務是社會主義道德的核心和根本原則。本來,“為人民服務”本身就是先進性與廣泛性的有機統一,但在計劃經濟時期左傾錯誤和教條主義的影響下,我們錯誤地把“為人民服務”和集體主義看作高高在上、普通人遙不可及、無法踐行的東西。“在今天,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無私奉獻是為人民服務,顧全大局、先公后私、愛崗敬業、辦事公道是為人民服務,同志間、師生間同學間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是為人民服務,熱心公益、助人為樂、見義勇為、扶貧幫困、扶殘助殘也是為人民服務,遵紀守法、誠實勞動并獲取正當的個人利益同樣也是為人民服務。”[6](P108)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和思想觀念的革新與進步,“為人民服務”的先進性與廣泛性、崇高性與通俗性、層次性與發展性的辯證統一已經成為我國學術界與教育界在理解和宣傳上的普遍共識。黨的十八大以來,積極培育和踐行“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已經成為我黨和全社會的共識。可以這么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為人民服務這一根本宗旨在國家層面、社會層面與個人層面的全方位體現,是為人民服務在多領域的價值目標和價值規范(價值準則)的具體化和具體體現。普通個人既有充分的道德自由以踐行其在慈善活動中的個人偏好,又能在以“為人民服務”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宗旨(中心)、價值目標和價值規范的教育與影響下,不斷擴大其道德活動、慈善活動的廣度與深度,不斷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和道德境界。
誰來引領和提升千千萬萬普通個人的道德呢?使普通個人在慈善活動中的個人偏好在范圍上不斷擴展或擴大,從而在整個道德水平道德境界上不斷提升呢?當然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黨員和干部。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全心全系為人民服務。憂人民之所憂,樂人民之所樂。榜樣的力量是巨大的,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在廣大黨員干部的率先垂范下,在弘揚正能量的社會輿論熏陶下和抑惡揚善的相關制度保障下,包括每一個人在內的整個社會的道德生活實踐一定會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
總的來說,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新時代,我們既要充分尊重和肯定千千萬萬個人在慈善活動中的個人偏好,又要求各個個人不能因此而妨礙或損害他人的合法權利與合法利益;既尊重自己和他人在慈善活動中之所好,不以己之所好強加于他人。我們追求共同的美,也追求各自的美;我們追求共同的善,也追求各自的善。我們既要允許人們、“各善其善”“各美其美”,彰顯其美的生活與道德生活中的個性和多樣性,又能“善善與共”“美美與共”,共同構建社會的道德和諧與整個社會的和諧,走向人類社會的美好生活。我們既要看到慈善活動中個人偏好的正當性與積極性,也要看到其蘊含的消極性與局限性,希冀和引領每一個體從慈善活動的個別的、局部的“所好(hào)”走向孔子所向往的整體的全面的“好(hào)德”、“好(hào)善”,積極接受以“為人民服務”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宗旨和中心的價值引領,在愈益完善的制度建設保障下不斷提升每一個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境界。這樣,我們的社會就會真正成為一個既尊重個人意志自由,又有為人民服務的根本道德原則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既有個人心情舒暢,又讓個人有所依歸的和諧美好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