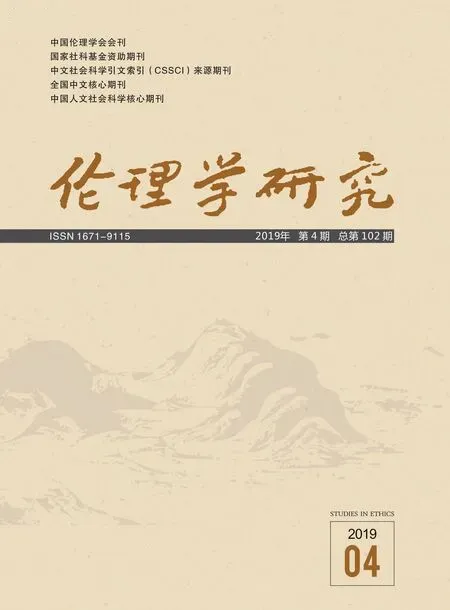論何殷震的女性倫理思想及其西學特色
常恒暢
何殷震(1886-?),原名何班,又名何震,字志劍,江蘇儀征人,是近代著名學者劉師培的夫人,也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有名的女權主義者。學界對于何殷震思想的研究多側重挖掘其女權主義、女性意識、無政府主義思想等方面的內容①,本文擬就其女性倫理思想的形成背景、主體內容以及產生根源進行初步探討。女性倫理是中國倫理文化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指的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女性,以其性別角色面臨人生中各種情況而產生的道德規范的總和,它既包括女性自身的道德選擇,也包括社會對女性的道德要求。”②何殷震的女性倫理思想是在清末民初西學東漸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中國知識階層尤其是中國知識女性自主思考和探索的產物。研究這一女性倫理思想不僅有利于我們理解在中西文化沖突背景下中國女性的應對與突圍,而且對于我們更加全面深入了解中國近代女性倫理思想的嬗變過程亦不無裨益。
一、背景與基礎:何殷震女性倫理思想的資源
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晚清的女性倫理觀念與思想已經發生巨大變化,并且出現了與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系統相背離的諸多因素。由這些因素構成的新思想逐漸影響了近代以來人們對于中國女性的固有認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女性社會狀況的改變,從而慢慢形成了對于女性道德要求的革新方向和嶄新認知。
首先,西方傳教士開啟的“男女平等”命題討論極大地沖擊了中國傳統倫理系統中“男尊女卑”的舊觀念,給國人帶來認知上的強烈刺激。《自西徂東》《佐治芻言》《泰西新史攬要》等著述通過向國人介紹西方文化,傳遞男女平等的思想。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在《險語對》中闡述:“夫男,人也;女,亦人也。”直接表明女性應該享有與男性平等的人權。他提出應以“己所欲者,必施諸人”的“西教”之“恕道”取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者之恕道”[1],呼吁中國向西方學習。
其次,受到西學影響的維新派與革命派持續關注男女平等、女權思想等相關問題。康有為在《實理公法全書》中倡導“人類平等是幾何公理”,中國傳統的“男為女綱,婦受制于其夫”[2](P36-40),不合公理,理當廢除。譚嗣同也提出“男女同為天地之菁英,同有無量之盛德大業,平等相均”,理應“變不平等教為平等”,以破“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不平等之法”,這也是儒、佛、耶三教共通之義[3](P333-337)。梁啟超在1897年發表的《變法通議》中也援據其師康有為“孔教平等義”,痛斥男女不平等的起源,為女學張目[4]。革命派則以馬君武為典型代表,他直接將西方的女權學說譯介到中國,使國人直接閱讀西方女權理論的文本成為可能。1903年4月,馬君武譯介了《彌勒約翰之學說》一文,其中第二節“女權說”,專門介紹彌勒的《女人壓制論》與社會黨人的《女權宣言書》[5]。可以說,馬君武的譯著乃晚清女權理論之源頭[6](P78)。
第三,來自女性群體的自我覺醒。1903年,金天翮在《女界鐘》一書中,以“女權革命”為中心,考察和參照歐美女權運動的歷史與現狀,認為中國的“女權革命”應區分為“人身自由權”和“參政權”“公民權”階段,從而完成與男性共建“新政府”的歷史使命。她認為最重要的是通過新式教育,把女性培育為“新國民”[7](P6-43)。1904年,呂碧城在《大公報》發表《論提倡女學之宗旨》,呼吁女性“以復自主之權利,完成天賦之原理而后已”[7](P51)。同年10月,秋瑾在《白話》雜志撰文,對中國傳統女性普遍悲慘的人生際遇進行了描述,號召女性起而抗爭。秋瑾呼吁婦女解放,并將女性的自我拯救與救國聯系起來[8](P4-6)。
概而言之,這些來自不同時期、不同群體的聲音代表了由“男女平等”向“女權”逐步過渡的時代訴求,為何殷震提供了思想資源,對其女性倫理思想的形成起到重要的啟發作用。
二、批判與重構:以“絕對平等”為核心的女性倫理思想
何殷震女性倫理思想既受到前代思想資源的啟發,也構成西學東漸背景下中國女性倫理嬗變過程中的重要一環。這一思想建立在對于傳統倫理制度批判的基礎之上,其理論核心是強調男女關系的“絕對平等”。
1.抨擊封建家族倫理制度,呼吁“解放婦女”
首先,對儒家倫理話語進行批判,何殷震把歷朝被統治階級奉為經典的儒家學術稱為“殺人之學術”,因其“以重男輕女標其宗”[9](P57)。在《女子復仇論》一文中,她對《禮記》《左傳》《詩經》《白虎通義》等儒家經典中關于“男尊女卑”話語進行了整理清算:“蓋以男為陽、以女為陰,又以惡之屬盡為陰、善之屬盡為陽,(《春秋繁露》)。由是,天下之最賤者,莫若女子;而天下最惡之名,亦畢集于女子之一身”[9](P66)。對于要求女子忠貞節烈的傳統婦女觀,何殷震抨擊道:“以貞女之空名,迫女子以死亡之禍,然后知前儒所言之禮,不啻殘死女子之具矣。”[9](P62)基于對于“男尊女卑”的深刻認識,何殷震提出要把女性從家庭、閨閣中解放出來,還給女子人身自由,讓女子與男子一樣擔負家庭責任,以實現“婦人者人人同享解放之樂”[9](P142)。
其次,何殷震以女性視角為出發點關照婦女群體命運,激勵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從而實現真正的獨立。她曾對班昭所作《女誡》進行了極具針對性地批判:
及于東漢,班昭之學,冠絕古今,而所倡之說,尤為荒謬。觀其所作《女誡》,首崇卑弱,謂女子主于下人,當謙讓恭敬,先人后己,含詬忍辱,常若危懼。又謂:“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又謂:“陰以柔為用,女以弱為美。”以侮夫為大戒,以貞靜為德容。嗚呼!此說一昌,而為女子者,遂以受制于男為定分。名為禮教,實則羞辱而已;名為義理,實則無恥而已。此非所謂“妾婦之道”耶?[9](P67)
何殷震認為這一文本是首次提倡和崇尚女子卑弱的文化,將女子地位置于男人的權威之下,讓女子經常處于一種慣性的弱勢,并輔以義理、禮教等崇高名義,將儒家禮法粉飾一番,而實際則是促成了女性自我意識缺位的“妾婦之道”的產生。何殷震對于班昭抱有某種程度的痛恨,同時也有一份同情的理解。她并未認定“以夫為天”的傳統話語里班昭的罪責,而是深刻地認識到班昭同樣也是儒家知識系統中的受害人和犧牲品,“而班賊之為此言,又由于篤守儒書,以先入之言為主,則班賊之罪,又儒家有以啟之也”[9](P68)。何殷震不僅關切同情婦女的命運,更看重女性自我意識的培養。
2.批判中西婚姻制度,革新婚姻制度
中國封建婚姻制度與家族制度是緊密相連的,前者是后者的產物,后者是前者的基礎。因此,何殷震對中國封建婚姻制度也進行了批判,并倡導一種“絕對平等”意義上的婚姻制度。
一方面,何殷震認為男女在嫁娶上的不平等是導致女性婚姻不幸的重要原因。中國封建社會實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度,“古代之時,位愈尊者妻愈眾。如殷代之制,天子娶十二女,諸侯娶九女,大夫三女,士二女……而后世之嬪妃,則更無限制。顯貴之家,蓄妾尤眾”[9](P41)。何殷震要求女子自身須有明確的意識,時刻警醒女性在這種男女不平等的婚姻制度中的悲劇性以及這種“男尊女卑”婚姻觀的可恥。“納采、納徵之禮,一遵古制,而婦家對于夫家,或以衣物服御之微,競相爭執,則賣女之風至今尚在……名曰下嫁,實則以俘囚、仆隸自居。于此而不知自恥,是必女子非人類而后可矣。”[9](P55)另一方面,在考察男女婚姻的現實生活問題上,何殷震對儒家創始人孔子、孟子發難。“孔丘者,儒家之鼻祖也,而其人即以出妻聞。傳之暨孫,均有出妻之行。蓋以暴行施之于妻,莫孔門若。孟軻者,儒家之大師也,因入室而妻失迎,遂謀出妻,其專制室人為何如”[9](P57)。何殷震將儒家創始人塑造成了專制的“出妻”者形象,將在封建休妻制度下的女性婚姻的不幸展露無遺。
在批判了傳統的婚姻觀之后,何殷震表達了自己革新舊有婚姻制度的愿望。首先,她倡導的是“忠貞”至上的一夫一妻制,禁止男性納妾,一旦有所違背,則將受到重罰,甚至有性命之虞。“如男子不僅一妻,或私蓄妾御,性好冶游者,則妻可制以至嚴之律,使之身死女子之中。”同時,也嚴禁女子婚內出軌,“其有既嫁之后,甘事多妻之夫者,則女界共起而誅之。若男子僅一妻而妻轉有外遇,無論男界、女界,亦必共起而誅之。”[9](420)其次,她認為女子出嫁后不應該隨夫姓,而應該父母姓并重,以保持女性在婚姻中的獨立性。為了實踐這一主張,她還掀起了關于“雙姓”問題的討論。她提倡女性應該承繼父姓與母姓雙姓,“自號其姓名曰何殷震”。隨后又提出了改良的辦法,“男子從其父姓,女子從其母姓”,以保障父族延續的同時母族的延續。再后來,何殷震提出“廢姓論”以取代“雙姓論”,在《天義》中作者的署名,例如“申叔”“震述”“震選”“志達”“公權”等,直接就沒有姓氏。第三,主張如果婚姻不幸福,也是可以離婚的。“如夫婦既昏而不諧,則告分離。惟未告分離之前,男不得再娶,女不得再嫁。否則,犯第一條之禁。”這條規定是與“一夫一妻”制配合實施的。第四,講求男女在婚姻中的絕對平等。“以初昏之男,配初昏之女。男子于妻死后,亦可再娶,惟必娶再昏之婦。女子于夫死之后,亦可再嫁,惟必嫁再昏之夫。如有以未昏之女嫁再昏之男者,女界共起而誅之。”[9](P43)這種希望男女在婚姻結合過程中認定婚姻身份的絕對等同體現了一種對于男女關系“絕對平等”追求的偏執。最后,反對欲望婚姻。何殷震不僅對中國封建婚姻制度進行了鞭笞,而且在研究了外國的婚姻制度之后也表達了對其虛偽性的批評。“據甄氏之說,足證近世結昏之禮,仍沿古代劫掠之風”[9](P54),她認為資本主義婚禮制度“一縛于權力,再縛于道德,三縛于法律”,“均由肉欲及財欲結合而成者也”,“實與蠻族之財昏無異”[9](P135)。在她看來,古今中外婚姻的本質都充滿了身體與物質的欲望,不同時期與不同國度的倫理制度、政府權力、道德法律則是維系這種欲望的強大機器,而這個機器是必須打破的。
3.解構中國傳統倫理話語體系,主張男女“絕對平等”
無論是家族倫理制度,還是婚姻制度,都是生產“男女不平等”的中國傳統倫理話語體系的組成部分,何殷震深刻認識到了正是因為這樣一整套知識生產體系與話語裝置的持續運轉,壓迫女性的知識與學術被源源不斷的生產出來,導致男女之間沒有真正意義上平等可言的一絲可能性。她力圖從根本上解構傳統倫理話語體系,主張男女之間應該處于“絕對平等”的關系之中。
何殷震睿智地發現了關于“女性”的“天性”與“傳統”皆由知識話語權力系統所建構,要實現“男女絕對之平等”則必須從最初的權力話語體系中找到突破口。首先,她考索歷史,將“男為主而女為奴”和“男為人而女為物”作為男女不平等產生的根源,而男女不平等的表現又可分為嫁娶不平等、名分不平等、職務不平等、禮制不平等四個方面[9](P41)。她分析了中國傳統社會中各種壓迫機制,例如文字、禮制、學術等。她全面而細致地清理了儒教對婦女的各種限制和壓迫,揭露了歷代儒家“學術”知識生產機制的特點:“黠者援飾其說以自便,愚者迷信其說而不疑,而吾女子之死于其中者,遂不知凡幾。”更是發出了“儒家之學術,均殺人之學術也”[9](P57)這樣振聾發聵的呼喊。何殷震冷峻地發現并指出,這些系統都對男女性別序列階層作了隱形地設置,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透過知識系統的不斷更新迭代,持續不斷生產著男女不平等。對何殷震來說,分別“男女”的機制是至關重要的邏輯起點,性別化的知識生產從男性主導世界的那一刻就開始了政治、文化與倫理等方面的權力設置,并進一步建構著知識系統中主體的普遍經驗。
其次,何氏主張通過向男子“復仇”以建立男女平等的起點。在《女子復仇論》一文中,何殷震則提出“男子者,女子之大敵”的極端口號,號召女子對男子進行“復仇”。她指出:“今男子之于女子也,既無一而非虐,則女子之于男子也,亦無一而非仇。”堅決主張要“革盡天下壓制婦女之男子”,同時“革盡天下甘受壓制之女子”,對女子“甘事多妻之夫”者,要“共起而誅之”[9](P49)。何殷震從不相信現實中“天性”或“傳統”的女性存在,她在《女子宣布書》中論述:“……男女同為人類,凡所謂男性、女性者,均習慣使然,教育使然。若不于男女生異視之心,鞠養相同,教育相同,則男女所盡之物亦可以相同,而“男性”“女性”之名詞,直可廢滅。此誠所謂男女平等也。”[9](P43)她也承認“男”與“女”的內部也有宰制關系,也有男子提倡男女平等現實情況的存在。所以,她也告誡女子:“蓋女子之所爭,僅以至公為止境,不必念往昔男子之仇,而使男子受治于女子下也。”[9](P50)
第三,她將復仇的目標指向了婦女受壓迫的經濟根源,以建立男女平等的經濟基礎。“惟土地、財產均為公有,使男女無貧富之差,則男子不至飽暖而思淫,女子不至辱身而求食,此亦均平天下之道也。依此法而行,在眾生固復其平等之權,在女子亦遂其復仇之愿。”[9](P50)。學者宋少鵬評述:“何殷震認為女子的解放和真正的男女平等只能存在于實行公產制的社會中。”[9](P77)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勞動婦女的悲慘境遇讓何殷震感同身受,也成為她激進女權主義批判的出發②。何殷震把財產關系作為社會生活的關鍵,她認為私有財產制度是不平等的根源:“現今女子之陷于困阨者……則有同一之原因。原因惟何?即生計問題是也,即財產分配不平均是也。”[9](P115)何殷震通過對中國蓄婢制度的歷史考察,認為該制度的產生,不是因為階級制度,而是因為“生計問題”。在論及西方國家的現狀時她說:“自十九世紀以來,富者挾其資本,以從事于生財,然財非一己所能生也,必役使他人以為己用。被以一言,即以平民之勞力,供富民之生財而已。”[9](P112)
在何殷震看來,勞動應該是人類的普遍活動,是勞動者生命本身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不應該包含私人占有他人勞動所得的權力。她賦予了勞動一種純粹的本體性,提出了一種完全不同于經濟學范疇的勞動概念。這樣的勞動是一種女性自主的勞動,而不是被奴役的商品化形式的勞動。因此,勞動作為最后的思考落腳點,關系到女性的生計問題與財產分配問題,關系到男女平等的實現。可以說,由自主的勞動出發,只有當女性重塑她們從事勞動的身體乃是人類勞動的本體,整個人類社會才可能從財富和權力建構的工具化勞動狀態中解放出來,男女之間的平等才能夠真正實現。
第四,消滅政府,實行無政府主義,以建立對“男女絕對之平等”的制度保障。何殷震指出:“女子私有制度之起源與奴隸制度之起源同一時代。”[9](P198)她認為,國家是私有制度的保護者,而“生計”上的保障,是不能依靠國家的。真正的“解放”和“生計”在于消滅一切經濟政治依附性的社會生活形式。何殷震抨擊國家制度,認為只有在一個徹底重構的社會文化體系中才能實現“男女絕對之平等”。她說:“如欲實行女界革命,必自經濟革命始。何為經濟革命?即顛覆財產私有制度,代以共產,而并廢一切之錢幣是也。”[9](P204)這種徹底地廢除財產私有制度的立場,使何殷震與中國的革命派和改良派區別開來,使她關于男女關系的理論具有了超越時代的深刻的思辨性與徹底的革命性。
三、淵源與超越:何氏女性倫理思想的西學特色
何殷震以“絕對平等”為核心的女性倫理思想并不是憑空想象的,而是具有深厚的理論淵源的。尤其是西方學術思想的滋養,使何氏女性倫理思想呈現出鮮明的西學特色。
首先,達爾文的進化論奠定了何殷震女性倫理思想的西學理論基礎。西方的進化論,特別是赫胥黎的《進化與倫理》經過嚴復的翻譯,作為一種全新的世界觀已經為當時國人所接納。嚴復在譯著《天演論》中將進化論的核心概括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何殷震在《天義》中則在比照的基礎上重新闡釋解讀了生存競爭的含義:
物類互助之說,始于達爾文。達氏雖以生存競存為物類進化之公例,然達氏所著《種源》,已言生存競存之意,不宜偏小一方面觀之,當從寬大處解釋。生存競存,即眾生之互助關系。又,所著《物種由來》,亦謂:“動物進化,當代競爭以協合。及競爭易為結合,斯其種益遷于良。所謂良種,非必賴其強與巧也。其所尚,惟在扶持結合。故凡公共團體,凡彼此相遇愈殷摯者,其團體亦愈發達。”達氏之言如此。而赫胥黎誤解其義,以為動物之中,惟強狡者乃生存。[9](P258)
在嚴復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中,適者即為強者,其論述的本質上一種生存競爭關系。《天義》的理解則更接近達爾文的本意,認為無論多么強壯的生物都不能獨活,競爭與協作相互依存,而協作是競爭的基礎,也是推動生物進化發展的根本動力。因此,生存競爭的含義其實是互助結合。
事實上,作為《天義》主編之一的何殷震能有如此卓識則是因為對于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接納和吸收。在赴日本之前,何殷震與其夫劉師培等人已經通過日本無政府主義者的著作間接了解到克魯泡特特金的學術思想。到日本后,則直接研習了克氏的《訴青年》《無政府主義哲學》《互助》《自由合意》等著作。因此,無政府主義構成了何氏女性倫理思想的又一個理論來源。何殷震推崇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本質上是推崇一種平等、自由、互助的倫理原則,而落實到其女性倫理思想上,則確立了對于“男女平等”核心思想的絕對肯定。
除此之外,盧梭的天賦人權學說也對何氏建構其女性倫理思想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中國傳統倫理核心是“三綱五常”,何殷震在批判“三綱五常”方面深受其夫劉師培的影響。劉師培借用盧梭的天賦人權學說對“三綱五常”這一傳統倫理核心曾提出過激烈批評。劉氏認為:“自三綱之說興而為君者,為父者,為夫者只有權利無義務,為臣者,為子者,為婦者有義務而無權利,所謂論勢不論理也。有權勢者能論理,無權勢者即不能論理。”[11](P48)正是由于“三綱五常”所規制的權利與義務的極端不對等,導致了上尊下卑的極端不平等現狀。而且,在他看來,這種歪理邪說“鉗制民心,束縛才智”,也是中國國民精神萎靡不振,無意積極進取,而“厭世樂天”之心日生的原因。因此,劉師培主張以“平等”為核心重構中國倫理,“以振勵國民之精神,使之奮發興起”[12](P37)。劉師培參照法國思想家盧梭的民約論來觀照倫理的起源,“蓋倫理之生,由于人與人相接。其始也,由一族而合數族;其繼也,由一群而合他群。其所以結合之方,皆由于人民之契約。”[12](P147)在盧梭的契約論思想中,契約之真諦在于平等,因此平等成為了倫理的精神內核。劉師培進一步闡釋中國“恕道”與西方的“平等”最接近,提出要以“恕道”為主線構建中國倫理。他說:
與人相接,以我之所欲所惡推之于彼,彼亦以所欲所惡推之于我,各行其恕,自相讓而不相爭,相愛而不相害,平天下所以在 矩之道也。此言甚確。蓋恕道于平等最近,故儒家之君臣父子也,祗言報施。報施者,即西人所謂權利義務之關系也。故恕道行,則三綱之說廢。[12](P50)
何殷震基本接受和吸納了劉師培的這一思想,通過以盧梭的天賦人權學說為參照,在理論源頭上建立了以“男女平等”為核心的思想與西方學術思想的內在邏輯聯系,不僅達到了對于中國傳統倫理文化批判的目的,而且為中國近代女性倫理思想發展指出了新方向。
事實上,一方面,達爾文的進化論、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和盧梭的天賦人權學說影響了何殷震女性倫理思想的建構,從而奠定了何氏思想西學資源多元化的特色,而另一方面,何殷震女性倫理思想又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對于西學理論的超越。
首先,這種超越性反映在對于“平等”和“自由”之間關系的理解上。何殷震十分重要的一個觀點就是將“平等”置于“自由”之上。《續社會主義講習會第一次開會記事》中劉師培極具代表性的發言就坦言了其所主張的與當時任何一派無政府主義均有不同:
無政府主義雖為吾等所確認,然與個人無政府主義不同,于共產、社會二主義,均有所采。惟彼等所言無政府,在于恢復人類完全之自由;而吾人之言無政府,則兼重實行人類完全之平等。蓋人人均平等,則人人均自由。[13]何殷震的持論與劉師培的主張幾無二致,她亦認為“平等”比“自由”更為重要。在日本拜訪無政府主義領袖幸德秋水、堺利焉,并與他們探討是否應對初婚、再婚男女的婚配做嚴格限制時,何殷震這樣理解與表述她和日本革命家的分歧:
蓋幸德君及堺君之意,在于實行人類完全之自由,而震意則在實行人類完全之平等。立說之點,稍有不同。[9](P347)
幸德秋水曾寫信與何殷震討論婚姻問題:“夫夫婦關系之第一要件,在于男女相戀相愛之情。縱令初婚之夫婦,心中無相戀相愛之情,則固有妨于夫婦之道。又令再婚之男,與初婚之女,真克愛戀和諧,何害其為夫婦乎?”[9](P347)在幸德秋水看來,愛情是婚姻的唯一基礎,甚至愛情遠在婚姻之上。何殷震卻從掃蕩“舊道德”的角度出發,要求一種近乎極致的“貞潔”至上的男女“絕對平等”婚配觀。
其次,受無政府主義影響,何殷震在尋求女性解放之道上表現得異常徹底,這與同時代受到西學影響的其他知識分子形成了鮮明比照。如前所述,何殷震將廢除政府作為尋求兩性絕對平等的根本保障。何殷震在《女子復仇論》種宣示:
以女子受制于男,固屬非公;以女子受制于女,亦屬失平。故吾人之目的,必廢除政府而后已。政府既廢,則男與男平權,女與女均勢,而男女之間,亦互相平等,豈非世界真公之理乎?[9](P50)
由此可知,何殷震已將“無政府”作為實現男女真正平等平權的絕對且唯一必要的前提。與何殷震同一時期的其他激進知識分子也都以提倡“女權革命”為己任,但諸人所說均以女權革命與民權革命相聯系。比如丁祖蔭在闡釋“女子家庭革命說”便直言:
政治之革命,以爭國民全體之自由;家庭之革命,以爭國民個人之自由:其目的同。政治之革命,由君主法律直接之壓制而起;女子家庭之革命,由君主法律間接壓制而起:其原因同。[14]
諸人之呼吁倡導“女界革命”,仍是出于政治革命或種族革命的考慮,他們將“女界革命”的進程設計為:“愛自由,尊平權,男女共和,以制造新國民為起點,以組織新政府為終局。”[7](P4-43)金一斷言“二十世紀之世界,為女權革命之時代”,柳亞子之謂“二十世紀其女權時代乎”,丁祖蔭之稱“二十世紀,為女權革命世界”,都表明了一種以西方婦女運動為楷模倡導建立一個新型的現代國家與政府的訴求。反觀何殷震的女性倫理思想,她以“男女平等”為終局,誓言消滅一切政府。并且,出于對任何權力的警惕,何殷震甚至對于“女權”一詞的使用也十分謹慎。在這種思路主導下,她又提出“發展女性”的新說,即實現女性身體與精神人格的雙重自由與健全。何氏的這些觀念和思想極大地超越了西學理論以及其影響的范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釋放出一種偏執的氣息,但是在清末民初的具體語境中,其獨立思辨的超越價值應該還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四、余 論
何氏女性倫理思想內涵豐富,充滿革命性,閃爍著思辨光芒,這使其與同時代其他女性倫理思想區別開來,成為中國近代女性倫理嬗變過程中重要的一環。
值得注意的是,何氏能夠迅速吸納西學觀點并進行創發,根源還是在于其本身對中國文化傳統在一定層面的認同與充分利用。尤其是當時無政府主義的主張與中國社會早已形成的文化興趣具有很大的契合度,這為何氏融合中西思想奠定了文化基礎。比如反對財產私有制,主張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歸公用的單一共產制與儒家的財富“均平”的思想相契,而無政府主義的“平等互助”等倫理原則在一定程度上與傳統文化中“天下為公”“至公”“仁政”與“德治”等理念相合。何殷震有時進行中西思想的互參與比附,“中國儒家謂之仁,歐人康德謂之博愛,若魯巴金則謂之互助扶助之感情”[15](P117)。在很大程度上,這種刻意串聯中西思想內在理路相通的典型手法不僅構筑了何氏女性倫理思想的肌理,而且也促進了中西倫理文化的交融與中國女性倫理思想的嬗變發展。
除此之外,何殷震在思想表達和論述過程中也不斷在傳統知識系統中尋找文化根源。例如通過把女媧繪制成身著和服的女性形象,并例數女媧功績,盛贊女媧“與軒羲并隆”[9](P3),有意抬高女性地位,以宣傳其婦女解放思想;又如在認知領域,接受歷史傳統中的異端思想的感召和啟示,受到李贄“不以圣人之是非為是非”觀念的影響而形成自己“所謂是非者,強者所定之是非也”的論述[9](P273)。而她關于儒家學術乃“殺人之學術”的論斷應該是受到了清代理學家戴震所指出的“以理殺人”的啟發[9](P230)。
何殷震曾坦言:“吾于一切學術,均甚懷疑,惟迷信無政府主義。故創辦《天義報》,一面言男女平等,一面言無政府。”[9](P307)基于無政府主義理論和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的雙重滋養,何殷震所追求的“男女絕對之平等”具有強烈的理論思辨色彩。在金天翮、呂碧城的論說中大力提倡的女子新式教育,在她看來也是“奴隸之教育”,因為政府與權力仍然存在,而這將必然帶來不平等。“蓋人治一日不廢,權力所在之地,即壓制所生之地也”[9](P140)。她開辟了一個原創性的理論空間,從不不糾纏于細枝末節,直接將女性解放的根本之道歸結為“盡覆人治”,施行無政府主義。盡管這種理論有一定程度上的偏執,卻也彰顯了其在思辨層面上的深刻。
最終,在如何解決男女關系的“絕對平等”這一核心問題上,何殷震給出的是無政府主義革命的方案:即廢除政府與家庭,施行“共產無政府主義”。然而,這已經完全背離了生產力發展的基本規律,忽視了經濟基礎的決定性作用,不符合當時的歷史情況。這種試圖畢其功于一役的思路,在實踐層面反而阻斷了社會革命的可能路徑,從而使她的女性倫理思想鍍上了一層空想社會主義的烏托邦色彩,成為清末民初多重思想世界中一種別樣的景觀。王汎森曾評價劉師培等一批知識分子的思想具有“反西化的西方主義與反傳統的傳統主義”的雙重特質[16](P244),這一評價同樣適用于劉師培的夫人何殷震。何氏的女性倫理思想反映的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兩難心態——既批判傳統,又依附傳統;既痛恨西化,又自我西化。可以說,這一矛盾心態從后來的“五四”時期直至21世紀的今天,也仍然是我們必須面對和檢視的。
[注 釋]
①劉慧英.從女權主義到無政府主義——何震的隱現與《天義》的變遷[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2);夏曉虹.何震的無政府主義“女界革命”論[J].中華文史論叢,2006(83);夏曉虹.晚清女報中的國族論述與女性意識[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4);須藤瑞代著,姚毅譯.中國“女權”概念的變遷——清末民初的人權和社會性別[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彼得·扎羅.何殷震與中國無政府女權主義[J].黃淮學刊,1989(4);劉人鵬.《天義》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視野與何殷震的“女子解放”[J].婦女研究論叢,2017(2);另有劉禾、瑞貝卡·卡爾、高彥碩著,陳燕谷所譯《一個現代思想的先聲:論何殷震對跨國女權主義理論的貢獻》,本文為英文版《中國女權主義的誕生》一書導言,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5期.該文章認為何殷震對于勞動婦女和農村經濟困境等問題的批判基本上是單槍匹馬進行的,且極具開創性的理論價值和意義。
②李桂梅,黃愛英.辛亥革命時期中國女性倫理的嬗變[J].倫理學研究,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