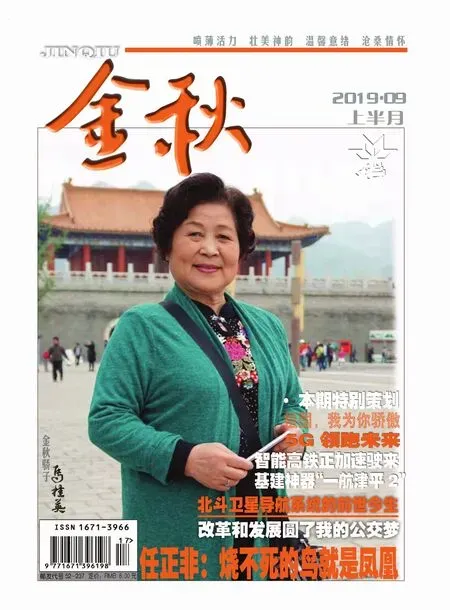別讓老師等得太久了
文/重慶·李曉

已經81歲的老爸時常感嘆說,人這一輩子啊,總要遇到貴人,對這些貴人,應該不相忘,放心頭。所以每年農歷八月十九,我爸就要吩咐我媽做點好吃的飯菜,等我媽把飯菜端上桌,我爸就會顛著痛風的腳,去把房門和窗戶一一打開,然后到桌子上擺上碗筷,嘴里喃喃呼喚著:“朱先生,您來吃吃飯……”住在我爸心里的這個朱先生,是早年他在鄉下發蒙時讀私塾的老師,農歷八月十九是朱先生的生日。朱老師對我爸這個忠厚誠懇的學生很是喜歡,寄托著殷殷期望。后來,我爸成為村里第一個師范專科大學生。考上的那一年,朱先生已經離世,我爸跪在朱先生的墳頭,擺上祭祀的酒菜,把喜訊傳遞給了老師。
在前不久的一次中學同學會上,由于同學之間有親疏遠近,還有厚此薄彼,所以一個當老板的同學對我說,你看啊,這次請的那幾個高中老師都白發蒼蒼了,只有他們,無論是對事業有成的學生,還是對普普通通過著日子的學生,都一視同仁,那慈祥的表情,像老爸老媽一樣,充滿了關切與愛憐。所以我們應該趁老師們還健在,多去看望一下他們,我聽后非常認同他的看法和建議。
于是,在去年9月,我和幾個小學同窗去看望班主任楊老師。楊老師當年是村里小學的民辦老師,而今已年過八旬。一個同學驅車帶我們去楊老師所在的村莊,雜草已淹沒了村里的土路,只有棄車步行。在山梁上看見一個佝僂老人,正遠遠迎接我們。
見了楊老師,同學們一一和他擁抱。等到我和楊老師擁抱時,他瘦骨嶙峋的身體貼在我胸膛上,讓我感覺是緊貼著山岡上一棵滄桑的老樹。
楊老師走在前面,帶我們去看他種的莊稼、喂的牛羊、養的雞鴨。楊老師這么大年紀了,還在鄉下種地,拒絕了兩個兒子讓他到城里去住的請求。有一次,楊老師還對大兒子發了脾氣,揮舞著鋤頭大聲說:“我這一輩子,就是種地的命!”兒子還嘴說:“你不是還說過,你一輩子,就是教書的命嗎?”其實,在楊老師的心里是不舍得離開那所學校的原址。楊老師49歲那年,告別了那所由破廟改建成的小學。在那所小學,楊老師執教了24年。18年前,那所小學已合并到了鎮上。聽師母說,楊老師還一個人偶爾走到學校原址去,默默念叨起當年那些學生的名字。
那天中午,白發如雪的師母,做了一大桌子豐盛的鄉下土菜款待我們。楊老師抱出一個酒壇子說,這是他泡的老藥酒,大家都喝點吧。那天我們幾個同學喝得都有些高了,后來竟然都哭了。也不明白到底是為什么,是看到楊老師老了,還是懷念我們那遠逝的童年時光?下午,我們難舍難分地告別了楊老師,看到他在松林包上朝我們一直揮舞著手,依稀浮現起當年他在黑板上用粉筆吱吱吱地寫下生字的情景,還讓我想起磨牙的聲音。
又一年的初秋時,我去看望高中教歷史的宋老師。85歲的宋老師住在一所養老院里,已掉光了頭發,老眼昏花。宋老師見了我,抱住我激動得直哆嗦,渾濁的老眼里淚花涌動。
后來,我們這些有“別讓老師等得太久”想法和同感的同學們在QQ、微信上聯系,彼此囑托:多去看望一下老師噢,哪怕去不成,也常常打個電話過去問候一下吧。還有一個同學說,他前不久組織了一次同學會,輾轉請了當年任教的老師們,卻有幾個老師已去世了;一個當年英姿勃勃的老師,牙齒都掉光了,吞咽食物都很艱難。同學們在會后互相感慨地說:“多去看望老師們吧,他們像自己的父母一樣,在倚門凝望中正一天天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