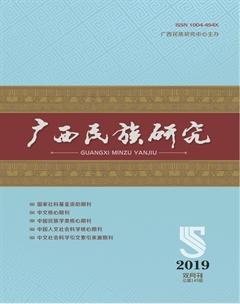花山巖畫與螞??節:南疆邊地壯族社會整合的儀式
【摘 要】螞節和花山巖畫中的核心角色“土司”“大人”都是壯民族社會依生關系的體現,在這兩種儀式活動中凝聚了壯族人民共同的信仰、文化象征和社會治理目的,包蘊了多重文化符號、凝聚了族群多重力量。壯族人民在這樣的全民聚會狂歡活動中獲得精神的歸屬、心理的安慰、生活的勇氣和信心,實現情感的抒發和宣泄,社會治理者借助儀式象征獲得了族群的認同與統治的合法性、促進了社會治理的實現,在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穩固及南疆邊地民族社會的建構、民族性的加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邊地;社會整合;儀式;螞節;花山巖畫
【作 者】何永艷,云南大學少數民族藝術專業在讀博士研究生。云南昆明,650091。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9)05-0145-009
紅水河流域壯族“螞節”與左江流域花山巖畫是聯系緊密的壯民族文化事象,二者都位于以壯族為主體的祖國南疆地域。“邊疆有時是帝國的政治邊界,更經常處于政治體制內的社會、經濟或文化罅隙之中。”[1]邊疆既是地理上的邊疆也是文化上的邊疆,其在政治、語言、宗教信仰、習俗等多方面都與漢文化中心具有一定疏離,因此,文化軟實力尤其是宗教信仰、習俗、儀式在社會治理過程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成為南疆邊地壯民族家園聚落內邊地治理中社會建構、社會整合、民族凝聚的重要力量。
一、螞節是那地土司時期社會整合的儀式
廣西壯族自治區河池市南丹縣與西南云貴高原余脈相連,隸屬于廣西壯族自治區河池市,崇寧(1106年)吾隘設那、地二州,1368年那、地二州合并,土司羅氏世襲土官,治所即在吾隘鎮那地村,該地區的土司管轄歷史一直到民國初年改土歸流時期才結束,土司歷史長達900余年,對當地文化影響較深,有石碑為證:“那地,地處南丹縣的西南面,1927年尚稱為那地土州,1928年成為河池縣十一區,管四哨十八石,地處交通要沖,是天峨、東蘭、南丹等縣沿紅水河兩岸的政治、經濟中心。”1
(一)那地螞節與土司淵源深厚
“螞節”是紅水河流域諸多節日中節慶時間最長、儀式最復雜、最隆重的一個,是該區域稻作節日的典范。
首先,那地螞節的確立、流傳與土司政治有淵源。
從廣西東蘭、鳳山、巴馬一帶的《螞歌》可知壯族螞節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姆六甲母系氏族社會。民國《河池縣志》中就有記載:“是月(即正月,筆者注),各哨村民皆埋螞,眾鐃鼓送之,墳上遍插色旗,至除夕發現蟆骨色以卜來歲祥祲。”[2]316現如今舉辦“螞節”的村鎮有紅水河流域的天峨縣、東蘭縣、南丹縣的部分村莊,世居民族皆為壯族,與銅鼓分布區域重合, “據當地文化部門調查,20世紀60年代以前,僅東蘭、南丹、天峨三縣壯族民間舉行螞節活動的村屯或修建的螞墳就有300處以上”[3]16。巴馬、鳳山壯族民間螞節逐漸消失,天峨、南丹、東蘭三縣的螞節傳承至今,南丹縣以那地村為中心周圍數十個村屯現今依然流行螞節活動,2018年2月25—26日兩天那地村集中舉辦螞節活動 。
筆者在節目冊上看到了本地關于“螞節”的螞傳說1,傳說中講道:夜郎國時代,那地州連年鬧“蝗兵”災,夜郎王下令誰能帶兵征剿“蝗兵”便封為大將并招之為駙馬,那地名叫駱吉的青年披上螞皮衣討伐“蝗兵”取得勝利,駱吉不愿當駙馬,皇帝令人燒了他的螞衣,駱吉不久便死去,當地人認為他是天上螞星轉世,要想消滅蝗蟲就必須每年農歷正月選個吉日為螞節,安葬螞,開棺材觀看螞遺骨,男女老少跳螞舞、唱螞歌、吃螞飯,以祈風調雨順,五谷豐登。
那地村的螞傳說具有夜郎國的歷史背景。英雄駱吉奉旨作為大將消滅“蝗兵”,立功后被招為駙馬不從被皇帝害死,這樣的情節表述隱約可見政治權力的影子。駱吉是借助了螞的力量取得了戰爭的勝利,下令討伐“蝗兵”、燒螞衣害死駱吉的人是皇帝,他是螞節誕生的官方強制力量。
田野調查中,筆者發現在祭螞的環節中師公戴啟初在拐卜得了吉卦之后開始為螞召魂,他一邊跳師公舞一邊念誦蟾祖祭詞,筆者發現那地村《蟾祖祭詞》系統完整地介紹了那地“螞節”與當地土司文化的深厚淵源以及它對壯族人民的意義,這份祭詞的日期和署名為“咸豐九年孟春 騰皋夜撰”2,表明這份蟾祖祭詞是由那地清朝土司羅騰皋于1859年一個孟春之夜所“撰”。這則祭詞是羅騰皋原創還是記錄、改寫、保存已經難以考證,但它的確為那地螞節找到了最為權威、久遠的來源,將那地螞節與壯族先民的原始起點及歷史進程相聯系,制定了當地螞節最為高端的規則與基調。那地土司重視通過文化管理和意識形態凝聚來鞏固地方統治,“螞節”民俗活動中有幾個文化項目都是土司組織進行并世代流傳下來的,加之這里交通閉塞、文化封閉,“螞節”也因此傳承不斷。2018年那地村“螞節”主要舉行場地那地小學即為原那地州土司衙府所在地,螞亭是土司衙府的一部分,至今還保留著那地土司照壁、羅氏祖祠碑等文化遺跡。
以上事實讓我們看到螞節民俗文化表征背后的權力因素,很明顯,那地村的“螞節”具有獨特的土司文化背景,讓其與當地歷史政治具有了緊密的深層關聯。
(二)土司時期螞節成為社會整合的儀式
首先,土司曾是那地村螞節活動的主要角色。
筆者田野調查點那地村是紅水河流域壯族螞節活動最活躍、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村落。據南丹縣非遺中心主任譚安強和銅鼓專家梁富林所言,那地土司在當地“螞節”的傳承中曾經起到過重要作用,是土司治理時期“螞節”活動的主要角色,是這一活動的發起者、主持者,可以說是集軍事、政治和宗教祭祀大權于一身的大祭司。
從組織成員來看,那地“螞節”程序復雜、分工細密,顯現出族群、地緣和家族傳承的結合,土司時期的核心領導者是土司,還有民間組織“螞社”專門負責螞活動的協調,“在節日中人們還要遵守一定的禁忌和規約,以習慣的方式調整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保證節日的正常進行”[4]48。
其次,通過螞節的祭螞、葬螞、吃螞飯、螞歌會、禁忌習俗、游藝活動等儀式內容,土司權力地位得到鞏固,族群認同與構建得以提升。
螞節是那地村全民參與的盛會,從吃螞飯這一特殊的儀式環節即可對其社會協調與整合意義模式窺見一斑。首先,螞飯對于當地壯族群眾來說是非常神圣的大事,具有吃螞飯資格的必須是已經成年的族人,因此這一活動就具有了成人儀式的作用,是對族人的身份、地位責任、義務和權利的一種標識和認同。其次,在吃螞飯的過程中,壯族民間傳統的村老頭人制發揮著重要作用,村老在其中扮演著顧問的重要角色,參與重大事情的決策和定奪,村與村之間的關系、各家庭之間的矛盾糾紛等都會在吃螞飯的過程中由村老出面協調解決。再次,在吃螞飯的過程中,人人動手、分工協作、共同籌辦,以神圣嚴肅、平靜認真、有禮有節的姿態來享用這一頓祈神求福的神圣之餐,以求獲得螞之靈氣與保佑。
從螞節螞歌會的熱鬧場面和多重社會意義功能也可以看到螞節的社會功能實現模式。現在人們舉行螞節活動,已不單純是祭祀螞,螞節發展成為一種集祭祀、娛樂、對歌、交友、聚會為一體的傳統節日。在螞歌會中,“各村都相互通報,盛情邀請,四方賓客歡聚一起,互相宴請,相互交流,盡情歌唱”[5],“能增進相互間的了解,加深彼此的感情,促進民族團結,增強民族凝聚力”[6]。通過節日活動,向青年人進行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的教育傳播、生產知識交流、對唱山歌技巧,對增強全村的團結,培育和振奮民族精神,弘揚民族優良文化,培養青年人熱愛家鄉、建設家鄉的熱情,增進與鄰村的友好感情,都具有積極而明顯的作用。
除了螞節組織者具有規范秩序外,在螞節上還有一些約定俗成的禁忌習俗,具有一定的社會功能。如在螞歌會中有不允許血親對歌、男女有嚴格的對歌距離、不允許調戲婦女等規矩,如有犯者,“螞頭”和村老有權處置。在東蘭巴英鬧螞時會有七位特殊的面具人物和二十一位手持木棍的彩相維持秩序。在螞節上用攔客桿攔客吃飯的習俗也具有一定的社會性。在螞節上還會有一些游藝活動,如那地村的地牯牛競賽,納洞村的老虎攆豬、螞跳塘、扳腰、大水翻壩、搭人山、虎擒羊等活動,這些習俗雖然不具有政治色彩,但在維護社會穩定、加強民間交流、化解矛盾、規范秩序、增強民族凝聚力、活躍民族情感等方面發揮了一定的社會功能。
總之,土司時期,土司在螞節儀式的確立、傳承和展演方面曾擔任核心角色,在“螞節”儀式活動中,全體族群共同宣示對青蛙的崇拜觀念,全民聚會、歌舞歡騰,族群的凝聚力、認同感得以提升,“螞節”是“堅定信心、整合智慧、交流經驗、促成共識的一次盛會,是民族文化展示、傳承的現場會,是壯族民間宗教信仰的隆重祭典,是青年男女以歌會友、依歌傳情、倚歌擇偶的交際會”[3]149。那地村“螞節”與土司文化的緊密關聯使得這一民俗節日具有了促進族群認同和歸屬感、增強集體凝聚力和維護社會穩定的社會功能,在土司治理時期,“螞節”超越了文化節日的功能,不僅僅是一個意義模式,也是一種社會互動形式,具有了構建和塑造社會結構的社會功能。
二、花山巖畫曾是駱越先民社會整合的儀式
花山巖畫是左江流域壯族那文化的結晶,其生業基礎是稻作農業,壯族先民生存環境、社會環境的相對多變性和一定程度的不穩定性,是刺激他們以花山巖畫的繪制這一文化適應行為來引起生產力發展和社會變革的重要因素。
(一)花山巖畫的誕生無法脫離社會環境
人是社會的動物,巖畫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表征必定脫離不了其創作者身處其中的社會結構,花山巖畫的產生必然以一定的生業經濟模式和社會環境為依托。
首先,花山巖畫的創作者為壯族先民甌駱族群,花山巖畫必定脫胎于這一族群的社會結構之中。
周秦和漢代活動于今廣西地區的人們,被稱為駱越或西甌,有時則西甌、駱越并稱,早在周代就有歷史記載。《史記·貨殖列傳》記載了楚越地區以稻作農耕為主要生計的“飯稻羹魚”的社會經濟形態,《交州外域記》記載了駱越地區以駱田為食的社會經濟形態和以駱王、駱侯、駱將為領導機構,以駱民為主體的社會形態:“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駱民。設駱王,駱侯、主諸郡縣,縣多為駱將,駱將銅印青綬。”[7]642從歷史記載中我們可以窺見駱越地區在花山巖畫繪制時期以稻作農耕為經濟主導,在此基礎上的社會傳統形態,已有階級社會的萌芽,人們依然是在各種傳統思想的主導下生活著,飯稻羹魚、自給自足、民風淳樸、少私寡欲、生死豁達,有世外桃源之景象。
百越“各有種姓”、雜居共處,駱越是“百越”中的一支,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語言、穩定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生成了具有獨特性的斷發文身、錯臂左衽、性習于水、喜居干欄、鑄造銅鼓等民族風俗。秦統一嶺南以前,壯族先民處于自主發展的由原始氏族、部落社會向階級社會的過渡階段。舊石器時代晚期壯族先民處于母系氏族社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壯族先民在新石器時代晚期5000年前進入了父系氏族社會,畜牧農耕代替了漁獵采集,“石祖”“陶祖”作為男性崇拜的象征開始出現。2500 多年前的春秋時期,壯族先民進入銅器時代,開始制作銅鉞、銅鐘、銅劍等器具,原始社會逐步解體,階級意識悄然出現,出現領袖與平民的等級差別。商以后壯族地區氏族社會瓦解,進入奴隸社會,形成了奴隸主、君、王、侯、將、都老等級體制。后來,西甌部落與秦軍戰斗數年,以秦始皇統一嶺南為分界線,壯族地區被納入中央政府統一管轄。
其次,花山巖畫的繪制處于駱越方國發展強盛時期,當時的社會結構具備組織大型巖畫繪制和儀式活動的制度力量。
大多數專家學者認為左江花山巖畫時間斷代為戰國至東漢的近700年的時間,這一時間段正好處于駱越方國強盛時期。梁庭望教授在其新作《駱越方國研究》中結合大量考古發現和歷史推斷認為在秦統一嶺南前,公元前1300年左右的商代后期,壯族先民已建立駱越方國,并進入階級矛盾相對緩和的東方奴隸制社會,“花山巖畫為壯族先民駱越人遺留下來的珍貴歷史遺跡”[8]。這一論點得到了各個學科的證實。可見,花山巖畫具有深厚的族群歷史背景,是百越族群甌駱部落中的駱越族群的智慧結晶,而宋明時期形成的壯族就是西甌、駱越的后裔民族之一。“駱越方國范圍大體是:北界至紅水河一線,西界至句町國,東界玉林、海南島,南界至北部灣沿海的北海、欽州、防城港和越南北部紅河流域一帶……駱越族群及其方國的政治中心和古都,有可能在中國廣西左江流域和邕江流域一帶的某地”[9],左江流域花山巖畫帶正好處于駱越方國的核心地帶。可見,稱花山巖畫的作者為壯族先民駱越人在時空上都是吻合的,花山巖畫是駱越方國的文化典范。可見,當時的社會結構已經具備組織大型族群儀式活動的制度力量,花山巖畫的制作、祭祀儀式等對于左江流域或更大范圍內的社會結構的建構、族群意識的認同、族群文化的穩固發展以及民族凝聚力的提升發揮了強大的社會功能。
(二)花山巖畫曾是駱越先民社會整合的儀式
左江花山巖畫曾是古駱越人的圣地,對壯族先民來說,花山巖畫的選點、繪制、祭祀等在他們的社會生活里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堪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巖畫群。
首先,規模龐大、規制統一的花山巖畫是壯族先民在統一的社會表征、規范和精神信仰之下集體意志的結晶。
左江花山巖畫對于生活在遙遠時代的駱越人,絕對不是單純為藝術的個人行為,一方面,巖畫的繪制對于生活在險惡環境中、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古代的駱越人來說重要性超過我們的想象,巖畫信仰在當時一定是全民參與的集體活動、社會行為,承載著整個族群生死存亡期待和希望的大事;另一方面,花山巖畫作畫難度巨大,接近作畫巖石、獲得作畫顏料、作畫工具、工匠培養、傳承等在生產力低下的情況下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況且要完成如此大規模的巖畫繪制,還要維持700年左右的時間,可能需要一批專門的作畫工匠、作畫培訓的老師,甚至還可能有巖畫傳習的場所、機構以及專門的領導負責,經年累月在洞窟中懸崖上繪制巖畫,需要大量的財力、物力人力和精神的支持,若是沒有駱越方國社會制度、體制保障、信仰的支持是不可能實現的。左江流域花山巖畫的繪制一定是當時駱越社會重要歷史事件,通過巖畫繪制的行為、借助巖畫圖像媒介,駱越先民的社會治理能力得以提升、集體意識得以整合、民族凝聚力得以加強,整個社會由此具有了統一的社會標準、規范和精神動力。
其次,在花山巖畫的繪制和儀式展演過程中,壯族先民的集體信念、集體情感、集體趣味結晶為完整、統一、成熟的文化模式,促進了壯族先民形成高度統一的社會組織的形成和穩固,反之,逐漸統一、成熟的社會組織又保障了巖畫繪制統一模式的穩固和龐大規模的形成,保障了巖畫繪制的綿延和傳承。二者協作共生、耦合并進、相輔相成。
花山巖畫是駱越根祖,包孕著古駱越族群的物質和精神文化信仰觀念、原始圖騰,從漁獵到農耕經濟的生產生活、“天—地—人”的宇宙觀;大小相對、正側排列、上下相分、繁簡布局等辯證思維模式和高度統一龐大的社會組織形態,以及崇尚紅色、強調程式化、集體情感的藝術審美情趣。整個左江巖畫群幅員廣闊,創作年代集中、主體集中、主題統一、風格雷同、手法一致,并且為單一族群所作,說明花山巖畫的創作、傳承是在聚力強大的集體意志下完成的,花山巖畫的繪制整合了族群多重的社會力量、促進了族群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提升,促進了統治階層合法權威的確立及等級、秩序、法令的形成,逐漸形成和穩固了高度統一的社會組織,這一社會組織包括了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信仰和習俗、教育的統一凝聚,最重要的是在社會、精神文化的凝聚之上形成了完整、統一、成熟的文化模式。花山巖畫核心原型就是當時的駱越先民從這一文化模式中提煉出的最能代表當時的文化精神的核心因素,這一模式加以創作發揮,作為駱越先民進行社會整合與建構的儀式,在逐漸型構的社會力量下星火燎原、逐漸完善,在長達700年的時間中形成左江巖畫長廊。
總之,規格統一、規模龐大的花山巖畫群誕生脫胎于駱越先民向階級社會過渡的駱越方國社會結構之中,存活、延續于各具體的壯族家園聚落之中,花山巖畫就是壯族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變革相適應的文化產物,巖畫的繪制整合了族群多重的社會力量、促進了族群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提升,促進了統治階層合法權威的確立及等級、秩序、法令的形成,與社會建構系統關聯、耦合并進巖畫與壯族社會自然、社會和精神生態形成了共生之美。
三、南疆邊地壯族社會整合的儀式
正如蘇聯學者烏格里諾維奇在《藝術與宗教》一書中所言:儀式是一種能夠履行多種社會職能、同時滿足多種社會需要的、與宗教相互滲透的繁復的混融性結構,因為儀式活動本身就是直接由勞動活動產生的,只不過是在對實際勞動的模擬中加入了信念和象征的成分。在儀式被不斷重復演出之后,人們開始相信這一活動具有巫術的力量,滿足人們在幻想、求知、教育、抒情和審美諸多方面的需要。
(一)都是社會依生關系的體現
花山巖畫和螞節儀式活動中儀式核心土司與“大人”的身上都體現了多重角色的融合以及政治、軍事、宗教、文化等多重力量的集聚,體現了不同時期壯族人民對自然、社會、權力的多重依生關系。
首先,花山巖畫和螞節都是大河流域壯族稻作文化的表征,共同的蛙崇拜信仰都體現了壯族人民在稻作農業生業基礎上,在生產力水平不夠發達的條件下對自然生態的妥協、附屬和依生關系,這一關系在此文中不再贅述。
其次,作為花山巖畫和螞節儀式軸心的土司和“大人”身上都集合了多重角色,體現了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的社會依生關系。
土司制度在南丹縣那地村發揮過長達900年的歷史作用,土司曾是那地村螞節活動的主要角色,曾在當地螞節活動規范確立、保護與傳承等方面做出重要貢獻,在土司身上匯聚了地方統治者、宗教組織者、執行者、接受者、祭司等多重角色,土司成為政治、軍事、宗教、文化力量的集合體。螞節與土司政治的聯結促進了其社會功能的發揮,通過螞節儀式的重復展演土司權力的合法性得到加強、地方權威得到確立、族群認同獲得提升、社會秩序得以穩定。在這個過程中土司借助螞節儀式活動文化軟實力促進了社會治理的融通和實現,其中體現出多重的社會依生關系。壯族人民作為螞節儀式活動的信仰主體、執行主體、參與主體、傳承主體,積極主動地響應土司的號召、接受其領導,體現了民眾對土司的依生關系,儀式活動中民眾之間的分工協作、凝聚融合又體現了民族內部人與人之間的依生關系以及個體對族群的依生關系。
花山巖畫的圖像包括了人物圖像、動物圖像和器物圖像等幾大類,數量最多的是人物圖像,其次是圓形圖像,有學者認為花山巖畫圖像的中心是圓形圖像所代表的銅鼓,因為人物都是圍繞銅鼓來排列活動的。筆者認為花山巖畫以正、側身人物圖像為主體,其中正身人像是主體中的主體,正身人像中又以魁梧高大的正身人像為中心,因為銅鼓為人使用,銅鼓、刀劍、動物的存在以及人物大小、繁簡都是為了凸顯人的權威。花山巖畫以人為主體的圖像正是壯族先民人性力量覺醒與高揚的標志,正身人像中的最為高大者才是中心與主角,因其酷似甲骨文中的“大”字,巖畫學者李啟軍將其稱為“大人”圖像,并認為花山巖畫“大人”圖像是駱越先民蛙神形象、“理想自我”與“自我理想”、部落首領與部落英雄、祈福除災的巫師、女人孩子可以托付的成熟男人等諸多形象的復指與疊合。花山巖畫綿延250公里、80余個巖畫點、5000多個巖畫圖像,最高的“大人”圖像近三米,每一畫幅內圖像都以酋長式的首領“大人”為中心,輔之以銅鼓來增加與確定其威嚴,配之以環首刀和扁莖短劍來凸顯其地位權力,周圍所有正、側面人皆圍繞其舞蹈、祭祀、膜拜,如此浩大宏偉的工程不可能不與社會結構和社會形態相聯系,“‘大人形象作為群眾仰視的首領或巫師形象、小孩仰視的成人形象、女人仰視的男人形象,體現的是駱越先民社會里人對人的依生關系”[10],巖畫中的“大人”形象必定是駱越現實社會中社會權力集中者的藝術化體現,復歸回現實,在壯族先民的實際生產生活中 “大人”應當是具備組織領導能力的、能被族群大眾所依生的、能帶領族群團結一致、走出生存困境的生產、生活、宗教、戰爭領袖。
(二)都是借助象征促進社會治理的儀式
大衛·科澤在《儀式·政治·權力》一書中認為規范化、穩定化、重復循環的儀式會與強烈的情感聯系在一起,儲備著有力的象征,這種象征被政治力量所征用,由此,社會統治者通過儀式與有力的象征相關聯,借助儀式征用了文化的象征性,象征系統將統治者與超自然力量相結合,進一步取得了社會治理的普遍合法性。
首先,花山巖畫與螞節儀式中都包含了象征意象,具有巫術象征意義,并與政治力量相聯系。
從花山巖畫的社會文化內涵來看其象征力量非常強大,說它是壯族的族徽、方國的門神、保家衛國的兵鎖、壯族先民的綠色家園、綠色搖籃和棲息地、圖像化的燦爛史詩、標志族群生存權的時代工程、民族力量的象征、族群社廟、族群重大事件的紀念碑等都不為過。“螞節”所有物質形態、觀念形態、制度形態意象的象征性都在儀式活動的展演過程中得以展現。壯族先民在“螞節”和花山巖畫圖像所呈現的儀式祭祀、歌曲、舞蹈、競技過程中鍛煉靈敏性和力量,獲得稻作耕種、巖畫繪制的知識技能,手舞足蹈、抒發情感,在制作各種儀式道具和歌舞表演中他們的審美需要也得到滿足,而且在儀式中創造道具、祭祀螞、埋螞、繪制巖畫等藝術過程本身就具有巫術象征意義。“‘螞節與花山巖畫最確鑿的核心關聯是‘蛙,它是‘螞節的主要祭祀對象,也是花山巖畫核心圖式‘蛙人的原型。‘蛙是這兩大文化事象共同的、核心的意象,是壯族稻作文明制度性、物質性、觀念性文化層面的核心載體、精神內核和動力表征。”[11]螞節的儀式活動、花山巖畫上所呈現的舞蹈、祭祀、銅鼓等儀式活動內容都在規范化、穩定化、重復循環的儀式中承載了強烈的民族情感、宗教情感以及功利愿望,包含了以蛙為核心的象征意象,必然與社會結構、政治力量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成為以土司和“大人”為軸心的社會整合的儀式。
其次,統治階層通過將花山巖畫和螞節儀式活動中文化的象征轉化為等級、秩序、法令、權力的象征來促進社會治理目的的實現。
面對著凝固在花山上的圖畫場景,我們可以想象出壯族先民在祭典活動前在部落首領統一指揮部署之下全民為儀式準備的情景,在儀式中除了涂繪在畫面上的集體祭祀蛙神、歌舞歡騰的高潮場景,花山巖畫其實包孕著祭祀儀式活動之前、之后、之中完整的動態過程。通過與“螞節”的類比參照,花山巖畫儀式活動全程在想象中得以還原,與“螞節”相比,花山巖畫圖像中的社會功能折射其實更加突出,最為明顯的莫過于巖畫中呈現出了等級之分,通過一次次的儀式活動的呈現與強化,花山巖畫和螞節中的文化象征悄然轉化成為等級、秩序、法律、權力的象征,規定了各個階層人與人的位置,首領的責任,也劃定了邊國的界限,彰顯了本族的權威,其中每幅畫面中還出現了與大多數蛙人圖像不同的“大人”形象,如同氏族部落首領的徽記、方國國王的玉璽一般使得花山巖畫保障邊防安全、社會穩定、人民安全的社會功能得到凸顯。螞節中土司角色的強化固定以及祭螞、葬螞等儀式流程和螞亭、螞墳、螞棺等儀式道具以及故事、歌謠、舞蹈等儀式文化的象征意味通過年復一年的儀式展演滲透進入民族文化并悄然轉化成為土司社會治理合法權威的象征。
花山巖畫圖像中所代表的這些“大人”應當具有與“螞節”土司同樣甚至更大的政治權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都是具有了一定社會型構功能的集政治、軍事、經濟、宗教、教育為一體的社會整合的儀式活動的再現,成為某一特定時代、特定族群社會統籌、社會治理的方式之一。沃勒斯指出:“使用各式各樣的樂器、歌曲、贊美詩和舞蹈,不僅能起到召集神靈的作用,而且還起到把人們整合起來的作用。”[12]489依據花山巖畫綿延范圍的廣闊和持續時間的長度、活動的盛大程度,其舞蹈排列、蛙人圖像的整齊劃一,以及參與人數的眾多與嚴謹有序、等級分明,以及螞節從母系社會淵源流傳至今的生生不息、螞節儀式程序的穩定傳承與活動的豐富有序,可以做出這樣合理的推測:花山巖畫與螞節都具有一定的社會型構功能,花山巖畫的社會組織性可能比土司組織的螞節活動更為嚴謹,其畫面反映的儀式活動的社會功能可能更加強大,其社會力量的整合效果對于整個族群的凝聚力、統治力可能更加強大。
(三)都是多重社會力量和功能的凝聚
首先,花山巖畫和“螞節”儀式都是社會秩序建構的一種形式,也是對現實制度的一種模擬。
綜合“螞節”中土司的重要角色地位和“螞節”傳說故事、歌謠習俗以及“螞節”儀式活動中的組織分工、習俗禁忌、儀式道具、吃螞飯、唱螞歌等內容來看,“螞節”給予“螞”人的葬禮的禮儀,具有祖先崇拜的內涵。同時,在具有社廟意味的“螞亭”進行的螞祭祀具有社祭內涵,在壯族宇宙觀中雷神是專司雨水的天神,螞與雷神具有超自然關系作為中介向雷神傳達人間的需求,在螞節儀式中對人與蛙神、雷神關系的建構也是對社會秩序的建構,是對現實制度的一種模擬。
在花山巖畫和螞節儀式中祖先崇拜、神靈崇拜、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社廟社祭融為一爐,巖畫儀式中人蛙的合一、正身人與側身人的分型、不同體積和大小的人的分型、繁簡的區分,蛙形人與圓形圖像、動物圖像、船形圖像、刀劍器物等的組合以及巖畫人物布局、排列、空間的建構,程式化雷同一致的風格主題,顏料、手法統一整齊的標準選擇,在精神層面都是駱越先民集體意識、民族整體愿望的整合。在社會層面實際執行者、統合這一切的人應當就是集族群首領、巫師祭司、巖畫專家、教育家等身份于一身的“大人”,他本身就是族群的一員是族群精神結晶的承載者,花山巖畫的繪制即是對社會秩序的建構,也是對現實制度的一種模擬。
其次,花山巖畫和螞節儀式活動都承載了多重的文化符號,協調和凝聚了族群多重力量,整合強化了族群的向心力、凝聚力,在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穩固及民族社會的建構和民族性的增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土司權力經過一年一度的儀式活動其社會治理合法性不斷強化,族群個體的民族認同感、依附感不斷加強,利于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以“螞”為核心要素的“螞節”在被土司固定規范化后儼然具有了政治權力的意味,以土司為祭司的“螞節”在年復一年的儀式展演內化進入族群視野,一次次地顯示了土司的權力和地位合法性,族群認同不斷構建提升,“我們”意識不斷增強。“螞”作為該地區全民崇拜的文化意象,螞亭具有了社亭的功能,祭司同時具有了統治者的職能,土司對于在文化上的整合強化了族群的向心力,使得“螞節”承擔了保障全民生產生存和美好生活順利進行的重要職責。
壯族先民創作花山巖畫的儀式活動過程與那地村“螞節”一樣在當地的社會建構、族群文化建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大人”通過花山巖畫祭祀儀式、巖畫繪制儀式確立自己社會治理的合法性地位,以“蹲踞式蛙形人”為原型圖式的巖畫圖像在被統治階層固定規范化后儼然具有了政治權力的意味,以“大人”為核心的巖畫內容將“大人”的等級、權威力量在一次次的膜拜中內化入族群大眾的集體觀念之中,以“大人”為統領的巖畫繪制在長達700年的歷史時間中銅鼓年復一年的儀式展演過程,一次次地顯示了首領的權力和地位合法性,壯族先民的族群認同不斷構建提升,“我們”意識不斷增強。“青蛙”成為該地區全民崇拜的文化意象,巖畫繪制地點成為天、地、神、人溝通的族群圣殿,同時又具有了社亭社祭的功能,巖畫繪制成為社會整合的儀式。
總之,花山巖畫和螞節儀式都在文化上整合強化了族群的向心力,承擔了保障全民生產生存和美好生活順利進行、整合社會力量、增強族群凝聚力、傳遞知識信息、協調社會關系、祈求生產豐收、族群繁衍生殖、表達宗教信仰和宇宙觀念、媚神娛人等多重復合職能,承載了多重的文化符號,在族群的生產生活中發揮了重要社會作用,在紅水河與左江流域壯民族家園聚落共同地域內為共同經濟生活、語言、文化基礎上穩定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民族社會的建構發揮了重要作用,是中國南疆邊地壯族社會整合的儀式。
結 語
總之,在土司治理時期,“土司”在那地村螞節的確立、傳承中曾扮演著重要角色。通過祭螞、葬螞、吃螞飯、螞歌會、禁忌習俗、游藝活動等儀式內容,土司權力地位得到鞏固,族群力量得到整合、認同與構建得以提升。規模龐大、規制統一的花山巖畫是壯族先民在統一的社會表征、規范和精神信仰之下集體意志的結晶,花山巖畫的繪制和儀式展演過程與駱越先民高度統一的社會組織的形成過程耦合并進,成為駱越先民進行社會整合的儀式。螞節中的“土司”、花山巖畫的“大人”都是壯民族家園聚落共同地域內社會依生關系的體現,包蘊了多重文化符號,凝聚了族群多重力量,這兩種儀式活動均凝聚了壯族人民共同的信仰、文化象征和社會治理目的;族群大眾在這樣的全民聚會狂歡活動均獲得精神的歸屬、心理的安慰、生活的勇氣和信心,實現情感的抒發和宣泄;社會治理者借助儀式象征獲得了族群的認同與統治的合法性、促進了社會治理的實現,在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穩固及南疆邊地民族社會的建構和民族性的加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共同彰顯了壯族人民借助青蛙崇拜表達的對生命永恒、種群繁衍、稻作豐收的追求,體現了壯族人民順應自然、尊重自然、熱愛自然、保護自然、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態智慧,對于現代社會治理以及生態環境保護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新時期,隨著生產力的進步,生產關系、社會結構發生變化,花山巖畫與螞節作為權力的文化符號象征、發揮社會建構的功能作用逐漸被削弱分化,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在新的時代語境下將呈現出壯族文化生生不息的勃勃生機與嶄新活力。
參考文獻:
[1] 趙樹岡.邊地、邊民與邊界的型構:從清代湖南苗疆到民國湘西苗族[J].民族研究,2018(1).
[2] 黎德宣.民國八年河池縣志·卷二“輿地志·風俗”[M].河池:河池市地方志,2000.
[3] 覃彩鑾.壯族螞節[M].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
[4] 廖明君,楊丹妮.壯族螞節:漢英對照[M].龔楚穎,譯.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
[5] 覃義生.廣西東蘭壯族螞節的調查與研究 [J].廣西民族研究,1999(2).
[6] 邵志忠,袁麗紅,吳偉鑌.壯族傳統節日文化傳承與鄉村社會發展——以廣西南丹縣那地村壯族蛙婆節為例[J].廣西民族研究,2006(2).
[7] 陳橋驛.水經注校釋[M].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
[8] 梁庭望,厲聲.駱越方國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
[9] 趙明龍.試論駱越族群及其在東南亞的后裔[J].百色學院學報,2016(5).
[10] 李啟軍.左江崖畫中“大人”形象的生態審美解讀:下[J].美與時代(上半月),2010(9).
[11] 何永艷.花山巖畫與螞節:大河流域壯族稻作文化的表征——花山巖畫與“螞節”比較研究論文之一[J].廣西民族研究,2018(4).
[12] [美]C·恩伯·M·恩伯.文化的變異——現代文化人類學通論[M].杜杉杉,譯;劉欽,審校.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HUASHAN ROCK PAINTING AND MAGUAI FESTIVAL:CEREMONY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ZHUANG IN THE SOUTHERN BORDER AREAS:
The Second Paper o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Huashan
Rock Paintinghs and The Maguai Festival
He Yongyan
Abstract:"Chieftain" and "Huge portrait",the core characters of Huashan Rock Painting and Maguai Festival? are all the embodiment of social dependence of the Zhuang. The common beliefs,cultural symbols and social governance purposes of the Zhuang are condensed in the two ritual activities. The Zhuang gain spiritual affiliation,psychological comfort,courage confidence of lif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emotional bursts and catharsis in such a national gathering and carnival. The social administrators use the ritual symbol to obtain the legitimacy of ethnic identity and domination,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stability of th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society in the southern border areas.
Key Words:border areas;social integration;ceremony;Huashan rock painting;Maguai Festival
〔責任編輯:陳家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