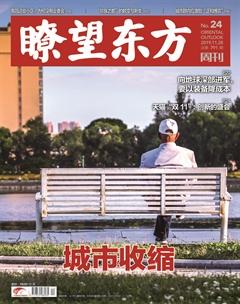收縮型城市:現狀與未來
劉佳璇 尹希寧 李維

黑龍江雞西市恒山國家礦山公園
2019年4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提出收縮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強體,轉變慣性的增量規劃思維,嚴控增量、盤活存量,引導人口和公共資源向城區集中。
這是官方文件首次提及“收縮型中小城市”概念, 意味著城市收縮現象已經從學術討論和媒體關注層面進入了國家政策視野。
“人口流失”“老齡化”“少子化”“減量規劃”……這些在我國城鎮化與區域發展進程中備受關注的現象,與城市收縮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當下,網絡上也流傳著不同版本的“收縮城市名單”。
當絕大多數人感受著城市擴張帶來的變化時,城市收縮現象是否正在悄然蔓延?城市收縮,是如何發生的?“收縮型中小城市”,開始“瘦身強體”了嗎?
“老家的人越來越少了”
25歲的在讀博士李然不愿意畢業后回到黑龍江的老家,雖然那座城市有著廣袤的林海,礦產資源也非常豐富。
“老家的人越來越少了。”李然對《瞭望東方周刊》說。他的50個高中同班同學中,只有15人留在了家鄉,離鄉的同學里,最近的扎根哈爾濱,更遠的走到了沈陽、北京、上海……
黑龍江省統計局數月前發布了那座城市的人口發展歷程報告,將當地人口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爆發增長期、緩慢增長期和遞進減少期。
報告中提到,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那座城市的林業資源逐漸減少甚至枯竭,由于缺少接續替代產業,資源型城市沒有如期實現轉型,加之改革開放形勢又相對滯后,出現了人口外流現象。90年代后期,戶籍總人口和勞動年齡人口進入下行通道,形成逐年遞減的局面。
資源枯竭與產業轉型不力導致的人口收縮,較為接近城市收縮的本質,如黑龍江省“四大煤城”出現的情況。
首都經貿大學副教授吳康發現,2007年到2016年,我國663個建制市中,有80個城市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人口收縮,占比12.1%,其中地級市24個,縣級市56個。大部分城市人口收縮幅度不大,僅有9個城市的收縮幅度超過5%。發生人口收縮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東北、東南沿海及沿邊地區。
第一表征
2016年5月,中國收縮城市研究網絡 (SCRNC) 發起了中國收縮城市學術研討會。至今,這個研討會已經舉辦了四屆。
第四屆的舉辦地點是哈爾濱,來自全國多個高校的相關研究團隊在會上交流了過去一年的研究成果。本刊記者在會上發現,關于收縮城市在我國該如何界定和識別,仍是一個熱門的研究課題。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德國政府便開始關注老工業區的人口流失問題。進入21世紀后,城市收縮現象得到了更加廣泛的關注。
吳康向本刊記者介紹,國際上普遍認同的是,城市收縮或城市局部收縮通常有三個表征:人口減少、經濟衰退、城市空間衰敗或品質下降。不過,這只是基于城市收縮表現出的特征所作的歸納,但它的內涵并不止于此。
事實上,各國城市發展情況各異,對于如何嚴格界定收縮城市這一概念并識別收縮城市,學術界并沒有形成共識。
比如,人口負增長的城市是否就是收縮城市?有人認為,如果一個城市連續多年常住或戶籍人口負增長,就可視為收縮城市;也有人認為,人口減少、經濟衰退和空間衰敗三個表征同時出現,才能視為收縮城市。
目前,將人口狀況作為城市收縮現象的第一表征已是共識,然而,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2000年)和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2010年)的數據已比較陳舊,統計時指標又有差別,很難通過這些數據來反映真實狀況。
另外,由于行政概念上的城市邊界會有變動,人口數據并不容易進行比對。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研究員、北京城市實驗室創始人龍瀛在研究中發現,與2010年相比,2014年全國已有100多個城市的市轄區邊界發生了變化,包括縣改區、縣改市等。
“有些地方可能市轄區人口下降了, 但中心城區人口還是增加的,這也成了定性的難題。”龍瀛說。
收縮的本質
按照發生機制,龍瀛將我國城市人口收縮現象分為五類:資源枯竭導致的人口收縮;大都市周邊中小城市出現的人口收縮;偏遠欠發達城市出現的人口收縮;產業轉型不成功導致的人口收縮;因行政區劃改變或統計數據調整等因素導致的人口數據下降。
上述五個類型中,資源枯竭與產業轉型不力導致的人口收縮,較為接近城市收縮的本質,如黑龍江省“四大煤城”出現的情況。
黑龍江省城市規劃勘測設計研究院院長助理、規劃研究所所長張遠景告訴本刊記者,黑龍江省城市收縮的原因可歸結為人、地、物、策四個方面。
“黑龍江省大部分人口是闖關東進來的,不少城市是移民城市,居民歸屬感可能不是那么強,一旦出現資源枯竭、產業不振、就業崗位減少,人自然就會往別的城市走。同時,高寒的氣候也使得人們更愿意往相對溫暖的地區轉移。”張遠景說,“我國優質的公共資源、公共服務設施,都集中在‘金字塔尖的城市里面,黑龍江省相對來說比較薄弱,年輕人更向往公共服務比較完善的城市。”
離開了家鄉、從東北到成都經商的吳文浩對本刊記者說:“感覺去大城市發展是個趨勢,很多年輕人一旦出來了,再想回去基本是不可能的。”
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人口收縮也發生在東南沿海的一些工貿城市,如東莞、義烏等。
在義烏調研期間,吳康發現義烏存在外來人口減少的情況。在全球生產要素進行重新配置的背景下,義烏的勞動密集型小商品加工業失去了原材料和人力成本優勢,電商的發展也在沖擊過去的小商品批發貿易,導致一些企業倒閉或外遷,外來人口隨之減少。
也有研究者發現,在江蘇、浙江等沿海發達地區,因低端制造業外流,局部出現了工業用地的人口收縮。
城市化的另一面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認同城市收縮是城市化的另一面。
2018年,我國城鎮化率已接近60%,開始進入城鎮化的“下半場”,剩余的城鎮化率增長空間約為10至15個百分點,這對單個城市的人口增長形成了約束。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宋迎昌認為,當前城鎮化主要靠城市群和大城市驅動,城市群和大城市以外的中小城市將來可能出現大批收縮。
比如,在人才爭奪戰中,特大城市、大城市的規模優勢愈發突出,這些處于常住人口增長前列的城市,所吸引的部分人口正來源于中小城市。尤其是在戶籍制度大改革的背景下,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障礙將逐步消失,中小城市的人口流失可能進一步加劇。
一些城市正處于收縮或局部收縮的階段,規劃里卻寫滿了增長的預期,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人口收縮、空間擴張的悖論。
“人口的空間再配置,或者說人口的自然流動,是一種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現象。”基于種種背景,龍瀛認為,部分省市人口的流失與城市收縮的現象會繼續存在,這將成為我國未來空間規劃與空間治理需要正視和解決的新命題。
尋找新出路
20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指出,做好城市工作,要堅持集約發展,框定總量、限定容量、盤活存量、做優增量、提高質量。此后,“存量規劃”在我國城市規劃業界成為“熱詞”,業內還提出了“減量規劃”的概念。
但是龍瀛也發現,一些城市正處于收縮或局部收縮的階段,規劃里卻寫滿了增長的預期,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人口收縮、空間擴張的悖論。
廈門大學教授、中國生態城市研究院總規劃師趙燕菁回憶,在剛進入規劃行業時,幾乎所有的城市都是擴張型增長,“城市規劃的方法都是圍繞此類城市而設計的, 規劃要回答的無非是增長多少、增長快慢的問題” 。如今,面對城市收縮現象,“迫切需要一個能解釋‘非增長型城市的理論并提出相應的規劃方法”。
吳康認為,處于收縮階段的中小城市要轉變“為增長而規劃”的執念,城市收縮也可以視作一種轉型發展的機遇。
事實上,出現收縮現象的中小城市,有的已在轉型,尋找新出路。
本世紀初,甘肅玉門為應對資源枯竭,將生活基地和辦公機關整體搬遷至酒泉,同時,將玉門市政府駐地遷至玉門鎮,在老城建設開發風能、太陽能產業集聚區,并利用大量的閑置資源開發旅游文化功能。
伊春近年來在加緊改革國有林區的同時,大力發展旅游產業,并于2019年7月正式調整行政區劃,將原有15個區整合縮減為8個區縣,將撤并的原區址建成生態特色小鎮組團,進而優化了城市空間布局和生產力要素布局。

東莞某企業智能制造生產線
因存在大量低價房而受到輿論關注的黑龍江“四大煤城”之一鶴崗,在2019年3月至7月間舉辦了“收縮城市規劃設計工作坊”活動——由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城市規劃新技術應用學術委員會、鶴崗市人民政府、黑龍江省城市規劃協會和清華大學建筑學院聯合主辦,邀請城鄉規劃專業知名高校的師生參加,探索應對收縮的途徑。
參與活動的年輕學子,很可能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第四屆中國收縮城市學術研討會上,他們展示了自己的設計方案。這次研討會的主題,正是“精明收縮·品質發展”。
多位受訪者對本刊記者說,面對城市收縮現象,不能簡單地將其視為城市“消亡”的先兆,或急于為發生收縮現象的城市“唱挽歌”,而應系統客觀地分析現狀,認清潛在風險,在規劃與治理上有所準備。
不同城市出現人口收縮的原因并不一致,全球范圍內公認的收縮城市,在表現形態上亦有細微差別,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很多城市通過自身要素的再分配、再調整,實現了城市的健康運行乃至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