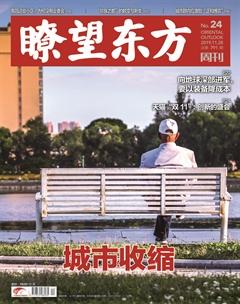收縮之中,也有機遇
尹希寧 劉佳璇

甘肅玉門昌馬風電場的風電機組(連振祥/ 攝)
城市收縮帶來的問題與挑戰,極易在輿論中形成熱點,因此,不少存在人口流失現象的城市,唯恐被扣上“收縮城市”的帽子。其實,與國外城鎮化高度發達后部分城市走向衰敗不同,在中國,城鎮化進程還在持續,某一時段內的人口流失對于部分城市來說還不是那么緊迫的問題,但是,收縮可能導致的發展停滯的潛在風險仍不能忽視。
上海財經大學長三角與長江經濟帶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張學良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專訪時表示,收縮不等于衰敗,不應只看到收縮給城市帶來的挑戰,而要理解收縮發生的機制,并看到收縮之中提升城市品質的機遇。
收縮不等于衰敗
《瞭望東方周刊》:城市收縮現象已經受到廣泛關注,應該如何認識這一現象?
張學良:城市收縮是個中性詞,它并不可怕。城市收縮雖然可能意味著遲緩的經濟增長,但同時也包含著空間置換、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的機遇。
《瞭望東方周刊》:城市收縮與城市衰敗之間不能畫等號?
張學良:城市收縮不等于城市衰敗。需要特別指出,中國的城市收縮有廣義和狹義之分。
廣義的城市收縮,指的是城市整體層面的人口下降。出現這類收縮的部分城市,可能整體上人口下降了,但中心城區的人口反而在上升,這類城市的活力還是在增強的。
狹義的城市收縮則需引起重視——城市整體人口數量下降的同時,中心城區和CBD的人口也在下降,這就需要進一步考察城市收縮的原因,如產業發展的情況、就業機會的多少、城市公共服務的水平、教育資源的分配等,并據此給出有針對性對策。
向“適應人口減少”轉型
《瞭望東方周刊》:《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提出,收縮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強體,轉變慣性的增量規劃思維,嚴控增量、盤活存量,引導人口和公共資源向城區集中。你認為相關城市在落實中應注意哪些問題?
張學良:收縮城市的規劃,要改變傳統的以增長為主題的擴張型規劃模式,向“適應人口減少”的方向轉型,由規模擴張轉向質量提升。
收縮城市發展的模式有很多種,可以借鑒“精明收縮”的理念——“更少的人、更少的建筑、更少的土地利用”。與其將重點放在存量人口的增長和持續擴張的土地利用上,不如通過提供更為宜居的環境、塑造更為精致的城市旅游文化、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來吸引流動人口和企業入駐,提升城市活力。
《瞭望東方周刊》:在政策應對上,國外有沒有可以借鑒的案例?
張學良:國外城市收縮主要是由去工業化、郊區化、人口結構變動以及政治變革等因素導致的,中國以人口流失為表征的城市收縮,則是城鎮化、工業化進程中出現的客觀現象。
想找到一模一樣的案例進行參考是不現實的,西方城市的一些做法我們只能部分地加以借鑒。
與其將重點放在存量人口的增長和持續擴張的土地利用上,不如通過提供更為宜居的環境、塑造更為精致的城市旅游文化、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來吸引流動人口和企業入駐,提升城市活力。
國外的案例中,城市轉型與重新定位被認為是重新振興城市的一個有效方法,英國曼徹斯特、利物浦、謝菲爾德等城市的案例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經驗。此外,不同于政府主導的轉型模式,西方部分城市還實施了公眾廣泛參與的“精明收縮”計劃,部分城市則實施了彈性城市規劃。
協同創造機遇
《瞭望東方周刊》:如果將城市收縮現象視為人口流動的一個結果,那么,跳出對單個城市的觀察,從都市圈的層面來看城市收縮現象,有哪些發現值得注意?
張學良:今年2月國家發改委發布了《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我認為都市圈也是研究城市收縮的重要空間尺度。我和我的團隊在一項以全國33個都市圈為觀察樣本的研究中發現,2000年至2015年間,都市圈中心城市常住人口增加超過1億,外圍區域常住人口增加3500萬左右。只有重慶都市圈的人口是持續下降的,其他都市圈的人口都沒有下降。這說明,如果將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看成一個整體的話,城市收縮現象并不是特別明顯。
《瞭望東方周刊》:在發展勢頭強勁的區域中心城市周邊,不少中小城市出現了收縮現象,成了“燈下黑”,如何解釋這一現象?
張學良:這種城市收縮是由中心城市的“虹吸效應”產生的。經濟學規律告訴我們,“虹吸效應”導致的城市收縮大致表現為人口等要素由農村向城市集中,由周邊城市向區域中心城市集中。中心城市通過發揮集聚效應,形成了空間增長極,又以較高的工資水平、優質的社會公共服務進一步吸引了勞動力等資源的流入,導致外圍城市的人口呈現下降趨勢,表現為收縮現象。
《瞭望東方周刊》:被中心城市“吸走”人口的中小城市,應該如何應對收縮?
張學良:中心城市周邊的小城市,應注重與中心城市形成區域協同,此外,應注重錯位發展,打造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品質。具體來說,有以下四點建議:
利用毗鄰區域中心城市的優勢,主動與中心城市形成產業配套,通過合理的分工合作,享受中心城市的溢出效應;
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注重錯位發展,因地制宜地推動特色產業的發展;
要注重在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環境治理等方面與中心城市銜接;
在制度建設上,外圍城市要積極推動與中心城市的跨區域合作,弱化行政壁壘,致力于形成多種層次、多種形式的行政協調機制,以優化營商環境,增強城市的生產活力與消費活力。
《瞭望東方周刊》:在這個過程中,中心城市需要做什么?
張學良:中心城市要發揮龍頭帶動作用,主動加強與周邊城市的互動。我們認為,中心城市綜合承載能力的提升,需要突破單個城市的行政邊界來進行思考。同時,部分中心城市“虹吸”了周邊城市的人口與其他生產要素,那么在公共服務配套方面也要考慮周邊城市的訴求,從都市圈的整體視角進行統籌規劃。